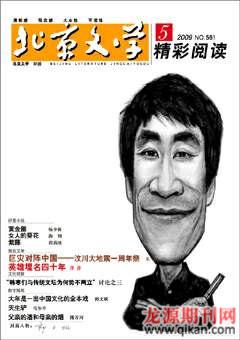紫藤
谭理中学是一所乡中学,又一学期开学,学生流失很多,陶敏去家访,劝回两个学生:胡锦章和吴来贵。胡锦章不好好读书,不好好劳动,还说女教师张馨的坏话。张馨气不过,打了胡锦章一巴掌。这一巴掌,引来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
谭理中学是一所乡里的中学,离县城十五里,离市区十八里,两头不着边。谭理中学在地理位置上跟市里的中学没多少距离,待遇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相差十万八千里。城里的老师带一节晚自习十块钱,而在谭理中学只有一块钱。这些都是直观可比较的,更不要说那些隐形部分。怪不得人说,市里重点学校的一个班主任抵一个正县,校长就是一个正厅,牛得很。
陶敏是谭理中学八年级一班的班主任,教语文。语文是谈不上专业的基础学科,因此陶敏老是自嘲,他是电话号码中的三三三,靠边站。不像英语老师,是天上的月亮,吃香得很。
谭理中学之所以星期四、星期五报名,也是无奈之举。这主要是农村学校针对学生报名情况,然后利用周六、周日上门做工作。乡里的中学,一般情况是七升八的时候,学生流失最多,稍微重视一点的家长,都会想尽办法把孩子转到县里或是市里的中学,留下的基本是靠天收。陶敏班上在七升八的时候就走了8个学生。今年是八年级的中间阶段,班上又有6个学生没来报到,有4个转学,2个没见影,全班50个学生,占到了11%,这么一算,这个数字就厉害了,这也是那些老师不太吼学生的一个原因,一吼一吼,学生就更不来了。现在还怪事,学生不来,家长不讲什么,倒是校长跟在屁股后面问你要人,没得搞!早在开学前的预备会上,胡校长就特别提到了失学问题。陶敏知道,虽然胡校长只是在会上提了提山里的深桥中学,说深桥中学初一三个班,初二两个班,初三一个班,但毕竟作为一个事来说,就要当个事来做。胡校长要求各班班主任还有任课教师辛苦点,到一些学生家里跑跑走走,尽可能地多了解一下学生的实际情况。家庭实在困难的学生,学校也将酌情预以减免一些费用,做到仁至义尽。老师被分成几条线,全都出去跑,全民总动员,同眼下的全民招商差不多。
老师都说学校这是在撒网,能网多少是多少。
陶敏先到胡锦章家。胡锦章是陶敏班上的学生。胡锦章一个儿子种,在家也是宝贝得不得了。
胡锦章的父母每天起早贪黑地赶到县医院门口摆水果摊。但今天他俩都没出去而是在家接亲戚。农村里有句老话,清明认祖,春节认亲,正月,城里水果是旺季,胡家忙着做生意,亲戚一家没接,过了十五再接,这也是比较少见的。
一进胡家门,陶敏几个还以为走错了,进了麻将场。
胡家客厅里竟然摆了三桌麻将,老头老太一桌,老爸一桌,小孩一桌。里面乌烟瘴气,闹哄哄的,还有好多凑热闹的。陶敏扫了一眼,没看到胡锦章,也不知道这小鬼摸到哪儿去了。老头老太们望了望,说了句是学堂里的老师,就继续打牌。因为以前来过,基本上都认得他们。小孩子那一桌,个个也不过十来岁,都还是小学生,也闷在那里打麻将,桌上还放着过年得的红包。有个小男孩看上去挺清秀灵光的,抓牌时,反扣着牌,中指一摸,就知道那是八万。摸得出白板没什么稀奇的,摸得出八万是个老杆子。
一个妇人家,走上前问:“得么事?”那语气硬邦邦的。陶敏说:“我们是谭理中学的老师,来看看,胡锦章为怎么不去上学。”用的是当地土话,很有点套近乎的味道,陶敏自己都觉得自己掉价。
胡锦章的老子看到老师来了,说了句:“老师来了,这把打好就来,”然后大声地对着厨房里叫道:“锦章个母,老师来了,冲杯茶。”自己却在麻将桌上继续。
“叫,叫,叫个死人头,我忙都忙死了,自己不晓得冲啊!就知道在那里充大老爷。”胡锦章的妈妈扯开嗓门在厨房里顶着。那声音又老又辣,如同毛草上的倒齿,刺利利的,从厨房刮过客厅,滑过来,刮人。不用看就知道是个厉害的婆娘。
陶敏赶忙说了句:“没事,打好这把我们再谈。”
客厅里根本就没凳子啦,几位老师识相得很,自己找地方站。
陶敏没想到这些家长这么无所顾忌,把老师这么不当回事,识趣地走到门口站着。门上贴着对联:“土生百宝,瑞雪兆丰年。地出万金,春光无限好。”横批:招财进宝。
胡锦章的父亲下了场,准备泡茶,陶敏赶忙说:“不用忙,我们一下就走。”然后把此行的目的跟胡锦章的父亲说了。
这时,胡锦章哼着吉祥三宝,悠哉悠哉地走了进来,原来他去买烟了。
胡锦章看到几个老师在他家,想开溜,陶敏眼尖,看到他逮了个正着。胡锦章一看溜不掉,就低着头,磨磨蹭蹭地磨进来。
陶敏直截了当地问:“怎么不到学校去?”
胡锦章低着头,不作声,闷了一大歇,才说了句:“念不下去。”
“念不下去,准备干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就到学校里去,等知道了,再不读也不迟。”
过了好大一会儿,胡锦章仰起了头,笑着对陶敏说:“我明天就到学校里去。”脸上虽挂着稚嫩的笑,但是眼光一扫的一瞬还是流露出一点诡,这一点诡没能躲过陶敏的眼睛,陶敏明明知道,但他无可奈何。
吴来贵的妈妈看到陶敏老师来了,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热情地招呼着,一个劲地叫老师“坐、坐、坐”。那种热情使几个老师从寒冬直接跨入到盛夏,倍感温暖。倒是吴来贵看到老师,一句话也不哼,到灶台边一个人闷坐着。吴来贵的妈妈把陶敏硬是拉到上板头。嘴里还数着:我们家来贵就亏你啦!就亏你啦!
吴妈妈一直在热情地招呼着老师,脸也笑开了花,一听儿子没到学校报到,脸一下子就白了,那白是大而醒目的,一点也不掩饰,也掩饰不住,一朵春雨中的白玉兰,含泪的白玉兰。
陶敏看到吴妈妈哭了,一句话也不哼,走到灶台边。问来贵:“为什么不上学?”
没得声音。吴来贵拿着根棍子在灶台边画来画去。
“是不是有什么事?有事告诉老师,老师帮着解决。”
还是没得声音。
这时吴妈妈从客厅里冲过来,对着吴来贵叫起来:“你是个死人啦,一点声音都没有,老师都上门啦,你还有什么话说?”
陶敏看吴来贵不想讲话。若是吴妈妈硬来,适得其反倒不好。就说:“不想讲,就不讲,但学还是要上的,有困难,就跟老师说,老师一定帮你,也希望你相信老师。你那个小房间,我已经给你扫好啦。”然后走过去,用手摸摸吴来贵的头,很有爱意(这动作被同事们戏称为陶敏的王牌动作———舒式招安)。
月儿很圆,月色很美,大地被月光照得一片清亮,泛着广漠的辉韵。
陶敏到外面走走,人影在月光的照射下,越来越大,立在那儿不动时,如同一个大黑熊似的,黑黑乎乎的一大团,那团黑映在地上,也印在了他的心里。
陶敏看到张馨时,他愣了一下,他没想到,这么冷的天,张馨也会在外面逛。张馨一抬头,看到陶敏时,她也愣了下,她同样没想到,这么冷的天,陶敏也在外面。目光相触的一瞬,彼此都有些尴尬,这尴尬不知从何说起。
陶敏和张馨是高中同学,后来张馨考取师专,陶敏考取安农师范学院,没想到两人分到一个学校,多少有些亲近感。本来两人也很自然,但是学校里的一些前辈们,老是善意地撮合他们,倒把他俩的关系给撮合生分了。他俩像是想撇清什么似的,总是隔得远远的,越是如此,旁人越是觉得他们之间有事。
陶敏看到张馨,愣了一下,但还是先打招呼:“你怎么也没睡?这个天这么冷,多穿点,不然容易冻到。”平平常常的一句话,不难听出温柔的内存。
“有点烦,出来转转。”
“烦什么?烦还不是要过日子?”这话说得像禅透了生活的老夫老妻,白白的,一点味都没有。男女之间,明明知道,而不点破,才有味,什么事都说到看透的份上,就扫了兴致。可惜,陶敏年轻,还不懂这些。
“教室里吵哄哄的,学生不学,自己讲给自己听。”
“只要有一个人听,都值。”陶敏安慰着。
第二天一早,东方刚刚吐白,地上还是一层白露。陶敏还没走出校门,就看到吴妈妈押着吴来贵来了。吴妈妈背着两个蛇皮袋,一前一后地挎在肩上。虽说很冷,但是吴妈妈的头上已蒙上了一层珠。看到陶敏,就跟看到救星似的。
吴妈妈把吴来贵的床铺好后,含着眼泪走了。吴妈妈走后,陶敏看看吴来贵,摸摸他的头,说,“可怜天下父母心,你要是想让你妈妈不流泪,就好好读书,知道吗?”
“读书出来也不一定有好工作。”吴来贵还是坚持着自己的观点。
“读书出来不一定有好工作,但是不读书肯定没有好工作。”
“我是怕妈妈伤心才来的。”
陶敏苦笑了一下,不作声,心想,要是吴来贵能体谅到父母的苦心,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市教委的公告,醒目地贴在校门口,上面写着从一年级到九年级的学费、书本费、杂费、其他收费等。八年级的书本费,学费,杂费,其他,总计326元。贫困生可以减免书本费。
黑板报还是老的,顶头是校训:厚德博学健身怡心。下面是明显的三大板块:左边是先进性专栏。中间是安全问题,不难看出学生的安全问题已成为学校、老师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右边是校务公示,张贴着:根椐县教育基教科2005年第20号文件精神,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免费享受教科书一套。经调查摸底,现将本学期享受免费教科书资助的名单公示,全校有学生780人,其中享受免费教科书的就有220人。黑板报的四周是信手涂鸦的一些所谓的不想长大,天灰,三节棍,月桂女神,SHE等等,乱七八糟的。
陶敏到教室转了转,看到胡锦章也来了。陶敏转身往教研组走去。
上课铃响,张馨跨进初二(1)班。
这时初二(1)班教室里的胡锦章像吃了兴奋剂一样,陶醉地在教室里唱起来:
太阳当空照,老师对我嚎。老子说,烦烦烦,你为什么总是找上我?我去找老大,老大有办法。一发话,一窝上,实在有趣,全部消灭光。
太阳当空照,骷髅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炸药包?我去炸学校,老师不知道。一拉弦,赶快跑,轰隆一声,学校炸没了。
这一唱,那教室里还得了,炸窝了。刚开始不过是两三个人轻轻地附和着,接着是四五个人,五六个人,乃至整个班的人都跟着唱起来。笑声一浪高过一浪,直嚷着好玩、搞笑。
张馨夹着书硬着头皮走向讲台,事实上,这时的教室根本就不是教室,而是歌剧院。张馨皱着眉头说:“唱够了,笑够了,也该静一静,上课了。”但这时的学生已达到兴奋点,根本刹不住车,也不想刹车,还一个劲地在那里唱,而且就数胡锦章唱得最带劲。学生是吃硬不吃软的,看张馨长得小小脊,都不怕她,敢跟她上鼻子上脸的。张馨没办法,走下讲台,走向带头的胡锦章说:“别唱了。”
“又不是我一个人唱,为什么就讲我一个?”胡锦章不服气地顶着。
“是你带头的。”
“什么我带头的?嘴长在他们身上,我有什么办法?”胡锦章毫不示弱。
“你不想上课没关系,不要在这里影响别人,真不想上课,就不要来。”
“我是不想来,是你们上门请我来的。”说到请字时,还故意用重音强调一下,说完还调皮地冲着张馨笑。那调皮得意获得了一片笑声。
“请你来是读书的,不是请你来炸学校的。”
“我又没炸学校,我是在唱歌,我有言论自由。”胡锦章根本不买张馨的账,还为自己在班上的影响力而感到自豪。
张馨生气地用手指着门外说:“要自由到外面去,不上课就给我出去。”
“我为什么要出去,我是交了钱的。”胡锦章满不在乎,松松垮垮地歪着,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在左脚上,那轻飘飘的语气像是逗老师玩。
胡锦章面不改色,倒是张馨面红耳赤,气得直抖。他走下讲台去拽胡锦章,想把胡锦章拖到教室外面去,但胡锦章哪服她拖,就在那里犟,一边拖一边拽,好不热闹。张馨本身个头就小,再加上劲道还没胡锦章的大,被胡锦章一推搡,没站稳,反倒被他反弹出好几步远,差点摔一跤。那些学生看到张馨个子那么小,还跟胡锦章在那里扯,一个个笑得要命,在边上起哄。教室里一片沸腾,一边拽一边扯,一边拖一边犟,像一个屠宰场,只是不知道谁是真正的屠宰者。
张馨的脸真有些挂不住了,学生们笑得更欢了。这歌声、笑声像长了翅膀,飞遍了整个学校,整个学校被这笑声、歌声淹没了,也引起了胡校长的注意。
胡校长来了,那些学生一看校长来了,一个个跟泥鳅一样溜进自己的座位装模作样地坐好,但嘴还抿着,嘴角还挂着笑。校长用眼睛瞪了瞪学生,看学生坐好了,也不说什么,拿眼望了望张馨,想说什么最终还是忍着了,但是那欲言又止的一瞥多少有点埋怨的意思。
张馨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课是怎么上下来的,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扒光了衣服示众的小偷一样,只是偷走的是老师的尊严和对未来的希望。
最后一堂课,全校大扫除。
太阳的余晖照着大地,把操场映得一片金黄,迎着太阳望过去,孩子们的头上形成了一道光影,煞是好看。
全校上下一片热闹,尘土飞扬。
陶敏在自己的责任区看着学生。这时,陶敏的手机响,原来是陶家村的人打来的,说细爷病了,叫陶敏马上回去一趟。
陶敏看着学生,有些放心不下,但想到那些离奇的梦,觉得还是该回去一趟。他走到吴来贵面前,叫吴来贵照应一下,又怕吴来贵压不住,他又托张馨帮他照应一下。陶敏把事交代好后,就往陶家村赶。
也许是兴奋情绪的延续,胡锦章又在操场上大放豪情:头可断,发型不能乱,血可流,皮鞋不能不擦油。这种原创性的改创很有感染力,引起了同学们的关注,胡锦章很有成就感,情绪更饱满,整个操场淹没在原创激情中。此时的操场已是名副其实的激情广场。老天也跟着凑热闹似的,起风了,把梧桐树上的毛球吹得满天飞,很有些金庸武侠里的意境。
张馨远远地在那里看着胡锦章,她装着没这回事,对于这样的事,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心想,只要把地扫好,就行,她不愿意管那么多,吃力不讨好。老师吃力不讨好的事太多了。
激情在操场上燃烧,激情在操场上蔓延。
吴来贵在认真地扫着,把垃圾拢成堆,远远地就看到胡锦章在那里舞,耍得起劲,一会儿“九阴真经”、一会儿“降龙十八掌”。梧桐树的黄毛本身就飞得人心里毛毛的,胡锦章一舞,更是满天飞,把已经拢起堆的垃圾舞得到处飞扬。吴来贵看到自己辛辛苦苦扫好的地又给胡锦章给弄得一塌糊涂,就生气地说:“你干什么呀?”
胡锦章:“我干什么,我在扫地呀!”然后又舞得漫天飞雪。
吴来贵冲上前去,对着胡锦章:“你不扫,你也别在这里害。”
胡锦章:“谁害?再害也害不过你哥哥,你哥哥是抢劫犯,家里都管不好,还来管我?”
吴来贵一听这话,冲上去就要找胡锦章拼命。两人抱成团,头顶着,如同两头斗牛,同学们地也不扫了,就围在那里看热闹。
张馨走到学生中间,拉开两头斗牛,问:“怎么回事?”
胡锦章:“他先动手打人。”
吴来贵不作声。
胡锦章看到吴来贵不作声,更是不得了。“理亏了吧?没得话说了吧?”
吴来贵还是不作声,但脸涨得通红,满脸的委屈和愤怒。
张馨看到胡锦章的嚣张样,也有些看不过眼,就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他怎么不跟别人打架呢?你看看你什么样子?”
胡锦章正在得意,突然被张馨一说,也是一愣,这事要是在平时也没什么,但是胡锦章看到那么多同学看着他,就受不了。他认为张老师是存心出他洋相,不给他面子。
他看了看张馨的红衣服,把头一抬说:“我什么样子?你看看你自己什么样子!倩都倩死了。”说这话的时候,嘴角还歪到一边去,满不在乎。
张馨没想到自己穿件衣服,学生也管闲事,而且当面评头论足,当众羞辱她。她气不打一处来,说:“你再讲句试试!”
胡锦章没想到平常柔柔弱弱的一个女教师也会这么凶,但是他还是很硬地回了一句:“倩都倩死了,怎么了?”后面还带个“怎么了?”根本不把张老师放在眼里。
张馨看着他那嚣张样,只觉得胸口一股火在一点点地集聚,膨胀,爆发。她抬手就是一个巴掌。当她看到胡锦章那吃惊的眼神时,不仅她愣了,胡锦章愣了,所有在场的学生都愣了。大家都没有想到:平时最省事的张老师,居然给了班上最难剃头、最瘌痢头的学生一个巴掌。张馨还没反应过来该怎样收场时,胡锦章先反应过来,他把头抬得更高,眼瞪得像铜铃,几乎爆出来,然后眼皮慢慢下放,下放,成一斜缝,最后竟翻了个全白———死鱼白,非常阴险、非常歹毒对着张馨说:“你给我记好了,我不会就这么放过你的!”说完冲出了学校。
那一道全白,像一道利剑,发着冷冷的寒光,让张馨不寒而栗。
胡锦章恨恨地走了,张馨心里没着没落的,魂好像被人牵走了似的。一想到胡锦章那歹毒的眼神,就有种阴森森、寒飕飕的感觉。张馨一颗心扑通扑通七上八下的。她想找陶敏聊聊,跟他拿个主意,走到门边才想起来,陶敏回家了。
夜渐渐地浓了。黑在一点一点地增加,黑雾从地面一点一点地往上漫,漫过脚,漫过头,漫过树梢,漫过山尖,一直往上升,直把远处那最后的一点亮光弥合,淹上,吞没。天地一片黑色。这黑也漫没了张馨,渗入到张馨的心灵深处。
宿舍里的张馨,就是一个字———慌。张馨思前想后,都觉得不是个事,还是到校长家去一趟,给校长反映一下情况,一是想请校长从外围斡旋一下,替她挡一挡。二是万一真有什么事,校长心里也有数。
张馨觉得两只脚像是在儿童乐园里的“太空漫步”,因为恐高,就是迈不开。好不容易敲了门,是校长夫人开的。张馨一进去,校长夫人就问:“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校长夫人现在特别关心别人的身体。
张馨摇摇头说:“校长在吗?”
“他没回来,有事找他?”张馨心想这不是明知故问。
“没什么事,校长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那我就不清楚了,明天上面领导来检查,他到办公室准备材料去了。”
张馨心里没底,她不知道是在校长家里等,还是到办公室里去找校长。她在那里如坐针毡,校长夫人一看她那样说:“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这里有‘美莉,吃了人会舒服一点,你来点试试?”
张馨一看她那样,知道她是想推销产品,她想了想白天的事,肚子里打了个弯,最终还是说:“拿一盒给我试试吧,我明天再给你钱。”
校长夫人一听,脸上的肉都激活了,表情也一下子星光灿烂起来,忙着给张馨泡茶,尽管张馨说她马上走,不用冲了,但是校长夫人还是一再地坚持给张馨泡了杯茶,好像要通过她的服务,来回报她的顾客。
从校长家出来,张馨手上虽多了盒美莉,但心里还是空空的,她真希望这盒“美莉”能让自己的心情也美丽起来,但她心中不但没有美丽的感觉,还增添了许多无奈。
张馨来到校长办公室,胡校长正忙着准备材料,看到张馨走进来,就问:“有事?”
张馨笑笑说:“有个事想跟你反映一下。”
“什么事?”
“我今天打了我班胡锦章一个耳光。”
“就这事?以后注意方法,我还得准备材料,回头再说吧。”校长忙着准备材料,当时也没细想,就这么轻松地给回了。张馨看校长那样,知道校长没工夫,也不好再说什么,走了。
张馨从校长办公室出来,想到校长讲得那么轻飘飘的,心里也轻松了一点,但是一想到那道死鱼白,想到那毛利利的声音,她的心又寒栗起来。到宿舍,看着那盒“美莉”,心里真不是个滋味。
张馨躺在床上,望着窗前的月亮。月亮起了毛,冷冷地斜挂着,月亮缺了,如同一个没有腌熟的蛋黄,淡而白,渣渣的,有些散,一碰就碎了。张馨的心也是淡而白的,胡思乱想,一碰就碎。
谭理中学已作好了检查的一切外围准备。校门口已经打上了横幅:热烈欢迎市领导来我校督导检查。
胡校长和其他老师一样,都希望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内平安无事,不要有情况,不要出乱子。
张馨走进教室,看到胡锦章的座位是空的,她的心一下子又吊起来。
十点半了,没什么动静,张馨心里默着:今天大概不会有事。她正在想好事,就听到校门口闹哄哄的。张馨的心一下子就紧绷起来。就看到学校大门口两大拖拉机的人在那里大喊大叫。几个老师从窗子上往外一看,就看到胡锦章的父母带着两大拖拉机的人,个个手上都抄着家伙。拖拉机往学校里冲,校门卫上前阻拦,胡锦章的母亲,两手叉着腰,就在那里喊:“你不开,我今天就把学校门给撞掉。”
胡锦章的妈妈左手叉着腰,右手打着拍子,骂一句还拍一次大腿,骂一句又拍一次大腿,很有规律和节奏。那门卫一看那气势汹汹的样,也被吓了一跳,慌里慌张地把大门打开。那两车人直接把拖拉机开到校长室门口。胡妈妈冲到校长面前,也不问什么情况,一上来就用手指着校长的鼻子说:“那个女的在哪里?那个女的在哪里?”简直要把校长吃了。
校长一看那架势,赶忙跑上前去:“别急,别急,有什么事我们坐下来谈。”
胡妈妈根本不吃这一套,她手在校长面前直舞直舞的,恶狠狠地说:“什么?打我儿子?我儿子长这么大,一句赖话都没听过,更别说打了。”没等校长接嘴,胡锦章的妈妈嘴巴像机光枪一样哒哒哒地扫起来:“我儿子在家从来没扫过地,扫地还吃巴掌。你们那是什么老师呀?还是个女的,你们要给我们一个说法。”
陶敏看到这样子,实在不像话,走上前去对着胡锦章的家长说:“这是学校,这是上课时间,有什么事,回头再讲。”那几个家长一路气势汹汹地走来,连校长都客客气气的,突然冒出这么个人,根本没放在眼里。胡妈妈冲到头里对着陶敏叫:“啊哟!我还当是谁呢?不就是陶家村细爷家儿子吗?你逞什么能?别人不知道你是怎么来的,我还不知道你是怎么来的?”
“知道又怎样?这是学校,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有什么事?放学后再谈。”
“你逞什么能,你妈妈不就是一个卖床单的吗?卖床单卖到别人床上去了,少在这里丢人现眼。”陶敏一听,血往上直冲,他冲上前去抓住胡妈妈就要跟她拼命,胡妈妈看他那样,嘴上还说:“讲到你的痛处了吧?”陶敏刚一冲上去,胡家的七大姑八大姨就把他俩围住,就听到那毛草割人声:“老师打人啦!老师打人啦!”等到校长把他们扯开时,吃亏的当然是陶敏,而且是暗亏。校长把陶敏拉到一边说:“你跟这帮老妇女吵,有得吵?到宿舍里去。”陶敏硬是被其他老师生吞活剥地拉走了。胡妈妈得了便宜还卖乖,他看到陶敏被拖走了,还不肯罢休,她索性往地上一坐,哇哇哇地大哭起来,搞得那些学生就跟看什么似的看着这一幕幕。
胡家人没找到张馨,还围在校门口,胡校长觉得这样也不是个事,要是甄局长他们这时来,那不是砸蛋?他权衡了一下利弊,拿起电话,给县里的领导讲了一下情况,并且强调,如果他这里出问题,县里领导的面子也不好看。
凡事牵涉到领导,简单的也变得复杂了,牵涉到领导的事,谁也不敢耽搁。县信访办的一个领导和一位年轻的乡长很快就到了谭理中学,这些人农村经验都很丰富,在路上就把情况了解了。看到胡家人,一眼就看出胡妈妈是最难讲经的,直截了当地对胡妈妈说:“不管昨天是什么情况,但是我保证回头给你一个说法。今天你们先回去。”
胡妈妈哪是那么好讲话的,她在那里叫:“不行,我今天就要说法。”
年轻的乡长把脸一沉说:“跟你好好讲,怎么不听?你天天在县医院门口摆摊,现在有人出高价争你们的摊位,是不是?摊位的事我来协调,今天我们各让一步,否则就是跟我作对。”他干过拆迁,讲话强硬得很,蛮赳赳的。
“这又不关你的事,你管什么闲事?”
“怎么不关我的事,在这个乡里发生的所有的事,都关我的事。”
“她是你老婆啊?你这么帮她讲话。”农村里,才不管那么多,什么怪话都讲。
“哟呵!你怎么这么聪明!她还真是我未过门的老婆,怎么样?你不会跟我作对吧,买个面子,下次有什么事找我。”年轻的乡长厉害得很,顺着话上。
对于张馨是乡长未来老婆,胡妈妈是不相信的,但是从乡长那语气,可以听出,这事他是管定了,以后有什么事撞在他手上,也说不准。另外,医院门口市口好,她也不想失去。这样一想,气焰自然而然地就败下来。
但她嘴巴还是很硬地说:“今天我是看你面子。你讲话算数,回头摊位的事我就找你了。”“一句话。”年轻的乡长会哈得很。
胡锦章一大家很有面子地走了,毕竟县里人和乡里人都出面了。
张馨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
学校要求张馨和陶敏两人都要检讨,理由是两人都是先动手打人。
紫藤花谢了,由紫到白,由白到黄,败落的黄。也就是在紫藤花谢时,张馨揣着那盒“美莉”上门道歉了。陪同她前往的有校长和年轻的乡长。而陶敏觉得自己没错,坚决不肯就范,被扣去两个月奖金附加通报批评。
第二年,紫藤花开时,张馨和那位年轻的乡长谈婚论嫁了。她选乡长很简单,就是因为乡长有可能让她不当老师。年轻的乡长选择她,也很简单,找一个当老师的做老婆,孩子的教育问题不用操心。正应了那句“女教师男乡长,黄金搭档”。
作者简介:
程燕冰,女,1971年1月生,汉族。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黄山市作家协会秘书长、黄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办公室主任。发表散文《月夜情思》《走过冬季》《童心遗落》《灵山灵》《雨中万安》《右龙古树记》《岭南三溪》等文章。第一部中篇小说《无花果》在报刊上连载。《紫藤》是其第二篇小说。
责任编辑 白连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