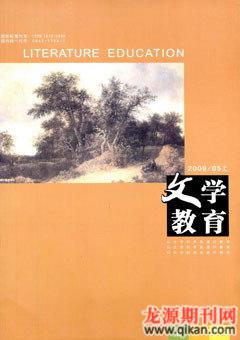跨文化交流下的文化误读
苑海静
由于笔者来自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以来在民族地区的生活和学习,对于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误读问题一直很关注。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沟通与对话是民族发展的必要手段。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不论是国内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还是差异更大的中西文化交流,都存在这个问题。而不论是从文学。还是从文化来说,文化误读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乐黛云老师将误读定义为:指把文化看作文本,在阅读异文化时很难避免误解。人们总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方法。一般来说,他只能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模式去认识这个世界。换句话说,文化的符号系统、价值系统和思维系统在不同民族中是相对固定的、稳定的。由民族中的人们所传承。并作为该民族理解其文化内部和文化内涵的依据。那么一民族文化被另一民族文化理解的过程,即是对该民族文化中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行为方式、艺术内容、审美趣味等多方面的误读。所以文化误读是在交流过程中不可能忽视的问题。
因为交流而产生的误读。尤其是从文学交流上来看,有着其自身的哲学依据。法国理论家皮尔·布狄尼在他的《文化生产场》一书中提出折射理论,对于交流问题提出了一个好的观点。他认为社会现象在文学中的反映不可能直接发生,而是必须通过文学场的折射。文学以它的历史、特点以及约定俗成的默认成规等构成一个文学生产场。场外的社会现象只能通过折射而不能直接在这个场中得到反映。因为它必然因文学场的作用而发生变形。将这一理论运用到文化的接触和对话中,乐黛云老师打了个比方,甲文化与乙文化相接触必然产生这种折射。属于甲文化的群体或个人进入乙文化时,必然带着它自身的文化场——思维方式、默认成规等。而使甲文化在他的研究和陈述中发生折射而变形。瓦尔特·F·法伊特在《误读作为文化间理解的条件》一文中引用了马丁·海德格尔对理解的本体论的分析断言:他人的共同此在之属于共在的展开状态等于说:因为此在之在是共同存在,所以在此在的存在之领悟中已经有对他人的领悟。这样的领会,和一般的领会一样,都不是一种由认识的出的知识,而是一种原始生存论上的存在方式,惟有这种原始的存在方式才使认识和知识成为可能。自我认识以原始地有所领会的共在为基础。作为人类共同存在,理解把握了我们与之同在的他者。瓦尔特·F·法伊特进一步说,与他人的共在主是在人的行为中——对我们而言,尤其是在语言中——显露出来。无论我们做什么,说什么,我们的所行所言都以他人为前提。这个前提非但不避免误解,反而首先尽可能地制造误解。因为理解是透视性的即受制于我过去的成见,当下利益和未来的预期而被理解着。但正是在对他者的误解中,他者才作为不想被我过去的成见,当下的利益和未来的预期。但正是在对他者的误解中,他者才作为不想被误认为一个熟习之存在的他者而被理解。也就是说误解是把他者作为生疏的、非熟悉的新的事物来指认和理解的,带着对异种文化的关注。
从哲学认识论上看,理解基础上的误解在一个存在的循环论中。在认识论上,理解恰恰是异解——或者用通常的说法,首先是误解。区别在于:仅当疏者是作为他者来理解而不是作为习者来误解时,理解才可能发生。在理解基础上的误解,是我们进行交流中无法绕过的一个障碍。
在后现代社会里,解构主义也对文化误解进行了阐释。哈罗德·布鲁姆认为对文本根本不存在绝对的或唯一的正确的理解,对文本的理解,其根本特点是不确定、多元化。他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把对文本的所有理解形式,包括翻译、批评等,一律命名为“误读”。他在对诗歌进行阐释的时候这样说:“诗的传统的形成乃是一代代诗人误读各自的前驱者的结果,而我们对古典诗歌的理解只不过是前人千百次误读的结晶。”解构主义在对误读的描述中不是重视对传统的是非判断,而是强调误读本身的实际意义或功效。但是“后现代时代是差异性和异质性时代,它消解了所有的整体叙事,是西方文化主导地位的减弱,是所有文化和伦理道德差异性齐声并发的时代。”绝对的差异性导致了福柯的“绝对无法与他者的沟通”的论断。如此导致了跨文化交流的一个悖论。
但是文化误解的存在,对于文化本身的自我,及对文化进行的阐释由于受到上文提到的诸多意识形态条件的限制,我们不可否认,由于历史原因,种族优越感已经并仍在人类学和人种学中广为探讨。它被当作了一种误解现象。即:对疏者的误解转而成为对习者的理解,并把自我肯定为正确的、善的和文明的,而把疏者更多地描述成野蛮的、未开化的甚至是邪恶的。例如从少数民族来说,由于地理历史等原因,尤其是地处偏僻,不为人熟知的少数民族,人们一提起就联想到贫穷、落后、未开化、野蛮等。虽然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存在,但在人类共有的文明面前应该没有优劣之分。当然随着改革开放,政府采用各种手段努力做到民族平等采取各种手段来制约这种不平衡的现象。从文学文化这一块来讲,对待文化误读的态度就尤为重要。乐黛云老师从宏观上,更为客观地提出了“和而不同”的原则。第一,事物虽各有不同,但决不可能逃离相互关系而孤立存在。“和”的本义就是要探讨诸多不同因素在不同关系网络中如何共处。二是“和”的主要精神就是要协调“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产生新的事物,这一事物又与其他事物构成新的不同。三是“和”的主要内容是“适度”,“适度”就是“致中和”,即不是“过”,也不是“不及”,而是恰到好处,因适度而达到各方面的和谐。这是一个很普遍的原则。但是我认为作为文化被误解的一方,邹威华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化误读与文化宽容问题》一文中提出的文化宽容观念对于被误解一方具有更好的启发意义。戴纬·钱尼在《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中说:作为社会群体的成员,我们应该理所当然地认为对日常社会问题存在着不同的处理方式,任何形式的社会秩序都是一个实用目的的建构。因此,宽容的核心原则是尊重差异,接受与我们认为正常的东西所不一样的另一套东西。
在解读文化宽容时,宽容首先被视为一种价值;同时宽容被看成是对现代性的构成原则,由此个人或社会对宽容的背离是一种不幸的时代错误,损害了现代进程。文化宽容的缓解和避免因各个民族思维方式习惯、文化模式、价值取向等方面不同而导致文化误读与文化冲突的有效手段和措施。文化误读和文化宽容是辨证统一的。文化宽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宽容或容忍交际者所产生的文化误读。但是文化容忍宽容有个度的问题。对正确理解文化误读和平衡文化宽容度的把握,既要从不同文化本身差异角度去考虑,又要从社会心理、文化认知、读者角度、哲学、语言学、文学和权利等方面去考虑。界定文化误读是否合理的尺度就在于误读的解释能否对文本文化实现超越和升华。文化解读需要有多元开放的心态,不论是正读还是误读,都必须依据文化发展的尺度对包括自身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作“适应性”解读。对文化宽容中的“度”的平衡和把握,应以是否影响交际行为本身和对文本合理性解读和阐释为分水岭。而其界定文化误读是否合理的尺度在于误读的解释能否对文本文化实现超越和升华。在整体文化中形成一个张力,推动文化不断发展和进步。
作为客观存在的实际问题,文化误读从哲学上、人类学上、文学上等各方面都是无法避免的客观存在。但是我们也看到了阐释而带来的另一个视角。而文化误读的尺度把握,在于误读的解释能否对文本实现超越和升华。从古至今,文化处在发展和进步的曲线上,对于误读的存在,我们用文化宽容的态度去对待它,为各民族自身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