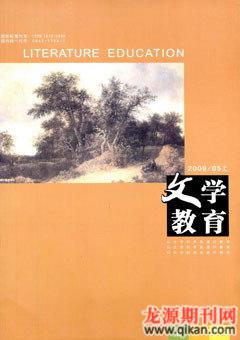《小城三月》的非常态怀乡情结及其悲剧意蕴
覃素安
萧红的《小城三月》是唯一的一篇美化萧红的家及其亲人的作品,在这里,她不再像以往那样寂寞与孤独,家充满着“爱”与“温暖”。这与她生命记忆中的“家”形成极大的反差,所以小说里的怀乡情结是非常态的。“非常态”意味着不同寻常。本文试图探寻的是这种“非常态”的本源,以及把握由此带来的悲剧意蕴。
一、非常态的怀乡情结
众所周知,萧红是一位自传型和情感型的作家,她的作品大多是自己生命活动的诗意再现。在《小城三月》中,非常态怀乡主要表现为人物形象的非常态刻划和家庭氛围的非常态描写。
先是继母形象的刻划。母亲的印象在萧红的心灵是不大深刻的,她九岁就没有了亲生母亲。母亲死时。她还在后花园玩耍,倒比不上祖父死时,在后花园喝酒来得伤痛与悲哀。《小城三月》里的继母给萧红最难以忘怀的是“很客气。不打我。就是骂,也是指着桌子或椅子来骂我”;她是一位充满悲悯之心的妇人。体谅翠姨的寂寞而常把她接到“我”热闹的家,共享天伦之乐;她是一位成人之美的君子,猜着翠姨的心思是在“我”哥哥的身上,而不是那个又小又矮的未婚夫,所以母亲故意派哥哥送礼物给翠姨,让年青人有相会的机遇;翠姨因无爱病死后,母亲还说:“要是翠姨一定不愿意出嫁,那也是可以的,假如他们当我说”;她是一位容易接受新思想的时尚者,她戴流行的长穗的耳坠子,穿时尚的高跟鞋;她还是一位与“我”相处融洽的朋友,“我”去外地读书,家中的事都是母亲讲给“我”听的。这样的继母显然是萧红的诗意构想。
伯父的印象在小说中也变了样。在萧红的记忆深处,伯父尽管也教她读诗诵书,给她榛子吃时也会把她“裹在大氅里”,“抱着”进去,但更多的印记则是他遇事无论大小都喜欢沉着脸,一本正经地说教;和顽固的父亲站在同一战线上,坚持不让萧红上中学。而小说中的伯父。他是一位热情开朗、平易近人、有平等思想的大朋友:晚饭后和晚辈一起玩乐器;正月十五和年青人去看花灯;开翠姨的玩笑叫她“林黛玉”;窘迫了,会喝一些酒来掩饰。这样的伯父是一种艺术的虚构。
还有父亲,虽然在小说中着墨不多。但决非是一个“斜视着你,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m的冷血动物,而是一个“革过命”、“咸与维新”的新潮家长。
《小城三月》不但对人物进行了非常态刻划。家庭氛围的描写也是非常态的。现实中萧红的家是她宁愿流浪街头也不回的!尽管经历了更为长久的漂泊,萧红也还认为这个家是寂寞的、荒凉的。《呼兰河传》写尽了这种况味。后园里的蝴蝶有白的、黄的,大蝴蝶满身的粉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花是红的,草是青的。明媚的背景下,一切都是活的、自由的:有顽皮的小萧红,有终日陪萧红玩的不老的祖父,但这一切正是为了衬托出“我家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花园越是鲜艳家就越是黯淡。院子里的砖头与破坛子,猪槽子与铁犁头。坛子里的似鱼非鱼的生物。大缸下边的潮虫,猪槽子上的蘑菇都配了对,成了双,这些热闹的景象呈现了萧红的寂寞与孤独。还有鲜活的后园到了冬天要封闭,院子里的漏粉人的荒凉的歌声,拉磨人的凄清的梆子声,街上的热闹与家的静悄悄,无不给人寂寞与荒凉之感。这些都是萧红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在《小城三月》里,家是热闹的、温暖的、自由的。“我”和翠姨买了配不着的花边回来会有家人的热烈评论;饭后长辈和晚辈融入音乐会中;男女老少一起逛公园,正月十五看花灯,一天到晚打网球;就连翠姨到我家来也是喜欢它的温暖与热闹。这样的家不是现实中的家,它是漂泊异乡的萧红在寂寞无依的香港时的一个梦,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二、生命深处的无家意识
这就是萧红在《小城三月》里非常态怀乡情结的真实展示。要追根溯源,本文以为,和作者的生命活动联结起来,更为容易探讨。
萧红是一位身心俱受摧残的女性,她的一生“是被家庭、爱情和社会所放逐的一生”。因为无法忍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无法接受无爱的人的婚姻,所以逃离了那个冷酷阴沉的家。这一刻意味着“无家”;父亲宣布开除她的祖籍是“家”的彻底破灭:萧红被家所放逐!流浪的路啊,是一条多么险恶曲折、寂寞凄凉的不归路!先是被无爱的人欺骗,终而遗弃在冷寂的旅馆,这时萧红怀着一个无望的小生命。如果不是萧军悲壮而浪漫的拯救,她肯定会沉沦青楼妓院;而拯救的同时,伤害也接踵而至。“两萧”的爱情历尽了饥饿、寒冷:“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可以吃吗?”“我暖着他冰冷的身子颤抖了。都说情人的身子比火还热,到此时。我不能相信这话了。”这些在没有饥寒交迫的我们读来,也有不可抑制的心酸!但经历了艰难的爱情还是走到了尽头,萧红一句“三郎,我们分手吧”,划了一个极不完满的句号。实际上,萧军是一个侠义但粗枝大叶的男子,而萧红是软弱的,表面的坚强掩盏不了女性的依赖感和强烈的归宿感。在外流连不归家的萧军无法满足萧红的精神需求,更无法给她构建一个温馨的精神家园。至于后来的端木,貌似相合,实则神离。他哪怕连萧军式的爱也无法满足:邻居吵架,只让萧红一人出面挡架,哪里谈得上给她以归宿感!甚至在萧红的生命弥留之际,不知去向,这足以让泉下的萧红遗恨千古!所以无家可归的萧红欲在爱情的伊甸园里营构家园简直是天方夜谭。她被爱情放逐了!爱的破灭是痛苦的,加上永远走不出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社会的压抑:“我最大的悲哀和痛苦便是做了女人”,临终时的话语道尽了性别的艰难与痛苦。萧红不像丁玲,可以在政治的风云里模糊性别而获得男性般的话语权。她游离于政治,忠实于自己的感觉,作为女人的感觉。所以无论在延安还是重庆,她永远是孤独的、无家的。萧红灵魂的深处永远埋藏着无以排解的无家的悲凉。在生命终点的香港,这种无家的凄凉更为深刻。她在《致白朗》一信中道出了此种心声:“这里的一切是多么恬静和幽美,——这一切不都正是我以往所梦想的佳境吗?然而呵,如今我却只感到寂寞!——我将可能在冬天回去。”这里的“回去”实则是渴望回归精神家园,但她无法回家,只能在同样弥漫着战火的香港遥望家,通过对家的诗性想象,构建一个温暖的精神归宿。《小城三月》里非常态地描写家和亲人正是这种心境的流露。
综上所述,萧红的一生是漂泊的一生,既逃离物质意义上的家,又渴求归依精神意义上的家,它的本源就是萧红生命深处的无家意识。《小城三月》里非常态的人物刻划和家庭氛围的描写,实则是再正常不过的怀乡情结。或者说它是一个美丽的梦,是萧红的理想,它让我们窥见了萧红灵魂的更深处。
三、悲剧性的回归
萧红的回归是悲剧性的。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物之源。故乡最玄奥、最美丽之处恰恰在于这种对本源的接近,决非其他”。H在《小城三月》里,萧红是回到了故乡,尤其是回到了“家”,她应是尽了一个作家的“天职”了,也接近了“美丽”的“本源”。但无法回避的是,小说中的家是虚构的,不真实的。有谁比在美梦醒后要面对恶梦般的现实来得更痛苦,更悲凉呢?萧红是深味这种境况的。对家的诗性想象并不能改变漂泊异乡的无依,也不能改变“蜇居”香港的孤苦,更不能改变身染重病而无亲人关爱的彻骨悲凉。梦是暖的,现实是冰冷的。被切开喉管无法发声的萧红的临终遗言充满悲凉与无奈:“我将与蓝天碧海永处,留半部红楼就由别人写了,半生多遭白眼冷遇”。“与蓝天碧海永处”一句透露出萧红还是漂泊的。还是寂寞的。还是无家的,一个没有真正意义上回归精神家园的人才会有如斯感触。
综上所述,《小城三月》的非常态形式的回“家”(怀乡情结)昭示了一个现实:越是美的,越是理想的,就越是悲凉的,这恰是萧红生命深处的体味。所以她的回归充满了悲剧意蕴,令人久久地回味,久久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