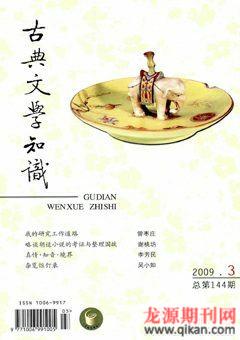嵇康“悔与吕安交”辨析
王洪军
《幽愤诗》是嵇康身陷囹圄,回首自己四十年人生所作,被称为是嵇康的自传,感情真挚,思想恳切。沈德潜在其《古诗源》中如是评价嵇康的《幽愤诗》:“通篇直直叙去,自怨自艾,若隐若晦,好善人,牵引之由也。显明臧否,得祸之由也。至云澡身沧浪,岂云能补,悔恨之词切矣。末托之颐性养寿,正恐未必能然之词。华亭鹤唳,隐然言外。”接着又说,“好善人,悔与吕安交也。”通读嵇康的《幽愤诗》,结合相关的史实,不禁令人质疑:嵇康是否真的后悔与吕安的交往?嵇康之死与吕安交往到底有多大关系?《幽愤诗》到底“悔”在哪里?本文就上述疑点,试辨析之。
一、关于嵇康与吕安的交往
嵇康与吕安的交往,散见于《晋书》及裴松之注《三国志》、《世说新语》等古代典籍中。
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康友而善之。后安为兄所枉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遂复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缧绁,乃作《幽愤诗》。(《晋书》卷四十九)
又共吕安灌园于山阳。(同上)
世语曰:“昭字子展,东平人。长子巽,字长悌,为相国掾,有宠于司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与嵇康善,与康俱被诛。”(《三国志·魏书》十六)
初,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及巽弟安亲善。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三国志·魏书》二十一)
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题门上作“凤”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凤字,凡鸟也。(《世说新语·简傲》)
余与嵇康、吕安居至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向秀《思旧赋序》)
依据这些文献钩索推寻,我们可以看出,嵇康和吕安是真正心意相通的朋友,吕安仰慕嵇康的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而嵇康也愿意为朋友的事情而奔走效劳,“辞相证引”,“义不负心”。嵇康的交友是极其贵乎“心”,贵乎“性情”的,这一点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已经言明:“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也可以从吕安与嵇喜的交往、阮籍和嵇喜的交往中得到反证:嵇喜因为依附于司马氏而为当时名士所不齿,在《世说新语·简傲》中,就有如前所引吕安门上题“凤”讥讽嵇喜之事;也有阮籍“白眼”对嵇喜、“青眼”对嵇康之事;而嵇康临终托嵇绍于山涛,也没有托付于自己的亲哥哥,实则嵇康与嵇喜虽有同胞之情却无同志之谊。刘志伟在《嵇康兄弟之“谜”与兄弟关系》一文中曾说:“嵇喜与嵇康虽为兄弟,实非同志。”同样,在山巨源依附司马氏之后举荐嵇康为官时,“康乃与涛书告绝”,山涛不识其“天性”,与嵇康也不是“真相知”。吕安“心旷而放”,“亦至烈,有济世志力”;阮籍“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本有济世志”;嵇康也“有奇才,远迈不群”、“志远而疏”,所以嵇康和吕安、阮籍之流才是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才有与向秀柳下锻铁之乐,和吕安山阳灌园之趣。
因此,嵇康与吕安的交往应该是志趣相投,心意相通的。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嵇康因吕安事件而死是不存悔意的。
二、关于嵇康之死
要深入分析嵇康与吕安的交往是否存有“悔意”,嵇康之死就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关于嵇康之死,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前人的研究甚详,兹概括如下。
首先,政治之害。
嵇康在司马氏篡权夺位之后,采取了与司马氏不合作的态度,这也是司马氏集团不能容忍的事情。罗宗强先生在其《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的说法颇具代表性:“司马氏是提倡名教的,嵇康却执著于‘越名教而任自然。他处处以己之高洁,显司马氏提倡的名教之虚伪与污浊。在玄风大倡的正始之后,要使名士们臣服,嵇康是非杀不可的。杀嵇康的目的,是借用这位有甚大声望的名士的性命,使桀骜的名士们臣服。”
李泽厚先生在其《中国美学史》中也有类似的看法:“不论如何,嵇康在政治上对司马氏集团采取强烈的不合作态度,又由于他的才学以及他与魏宗室的密切关系在当时有很大影响,这就是嵇康被害死的原因。”对于嵇康因政治原因而死的论断,学者们的看法颇为一致。
其次,性格之悲。
嵇康高蹈独立、任性直道的性格,也是酿成惨祸的一个根源。嵇康素以“性烈”著称,钟嵘《诗品》就曾评为“过为峻切,讦直露才”。孙登之语亦可为证:
登曰:“君性烈才隽,其能免乎?”(《晋书·嵇康传》)
(康)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求乎?”(《晋┦椤ひ逸传》卷九十四)
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三国志·魏书·王粲传》)
登曰:“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世说新语·栖逸》)
即使在《幽愤诗》中,刚烈之概溢于言表:“匪降自天,实由顽疏”、“恃爱肆姐,不训不师”。他的“性烈”使他不能如阮籍那样妥协以全身,更不会像山涛那样折腰事权贵。嵇康性格气质的不羁和绝世独立,也是悲剧的因素之一。
再次,小人构陷。
嵇康之死,其中的关键人物——钟会。《世说新语》和史书均有记载: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秘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世说新语·文学》)
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及是,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晋书》卷四十九)
嵇康等见诛,皆会谋也。(《三国志·魏书》卷二十八)
钟会身出名门,是曹魏大臣,也是大书法家钟繇的儿子。然而嵇康对钟会的《四本论》既没有“非难”也没有“评价”,在崇尚清谈的魏晋时代,对于贵公子豪俊钟会而言,无疑是一件很遗憾很难堪的事情。到了西晋时期,钟会又因征讨毌丘俭、诸葛诞叛乱和阻止曹髦夺权有功,得以成为司马氏的亲信,而嵇康却对钟会的造访不予理会且语带机锋,钟会怀恨在心也属常理。因此,钟会的挑拨、嫉恨和对嵇康的报复,其实早已埋下了祸根。
我们可以看到,嵇康是必死无疑的,是非死不可的。这既有外因——西晋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小人的构陷,也有内因——嵇康刚烈任性的个性。正如李泽厚在其《中国美学史》中所云:“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司马氏集团对嵇康的极大不满,嵇康是因和他的好友吕安的一件纯属个人的私事相牵连而被处死的。这完全是一种小题大做的政治性谋杀。”所以,吕安只是嵇康之死的一个导火线,只是加速了嵇康的死亡罢了,并不是根本的原因。因之,嵇康对于吕安而言,亦是无悔的。
三、关于《幽愤诗》“悔”的解读
第一,《幽愤诗》有无“悔意”。
对于这个问题,沈德潜就认为:“至云澡身沧浪,岂云能补,悔恨之词切矣。”最近的学者也颇有分歧,比如许德楠《嵇康在<幽愤诗>中何曾“忏悔”过?》一文就主张无“悔”。而刘志伟在《崇“友”意识与嵇康的文学创作》一文中却主张有“悔”。本文比较赞同后者的观点。《幽愤诗》作于系狱临终之前,全诗主要回顾了自己一生(四十年)的经历,从幼年失祜,由母兄抚养到自己成年“托好老庄,贱物贵身”思想的形成及其原因,追“悔”自己身遭牢狱之灾是由于自己性格“顽疏”而终遭谤议,抒发自己没有参悟孙登之言,未能实现全真保身、守朴养生的理想和幽愤感慨的心情。从这个层次讲,沈氏所论“至云澡身沧浪,岂云能补,悔恨之词切矣”是中肯的。
第二,对“悔”解读的歧误。
既然有“悔”,那么沈氏所言“悔与吕安交也”是否确实?沈氏的观点在于误解了“好善人”,简单地认为是嵇康“悔与吕安交也”。紧扣《幽愤诗》诗旨,考察相关史实并结合嵇康相关作品分析,这里的“好善人”,并不是针对吕安,而是针对吕巽。通观嵇康的作品,其中仅有两篇绝交书:《与山巨源绝交书》和《与吕长悌绝交书》。《与山巨源绝交书》写于山涛投靠司马氏集团后,举荐嵇康做官,企图将嵇康拉入司马昭的麾下之时,嵇康写信断然和山涛绝交,认为山涛与自己不是“真相知”。《与吕长悌绝交书》,写于嵇康因为吕安事件入狱之时,是写给吕巽的。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载:“初,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及巽弟安亲善。”吕巽与弟弟吕安本来都是嵇康的朋友,吕巽淫亵吕安妻子之后,吕安相信嵇康的劝解调停而没有告发禽兽不如的吕巽,吕巽却恶人先告状,这使嵇康感到极大的愤怒和悔恨,悔恨自己交友不慎,竟然与衣冠禽兽为伍,终致囹圄之灾,所以也断然和吕巽绝交。
对读分析《幽愤诗》和《与吕长悌绝交书》,“好善人”、悔恨之意更加明确。在《幽愤诗》中,嵇康抒发了强烈的愤懑之情,因为“好善人”,错识吕巽,才会内负宿心:“昔惭柳慧,今愧孙登”,既没有实现自己吟啸山林的志向而“事与愿违”,更没有“辞相证引”为吕安洗脱冤屈,自己也因之系狱而“外恧良朋”。所以,也才有《与吕长悌绝交书》中的恨恨之言:“今都(吕安)获罪,吾为负之。吾之负都,由足下之负吾也。怅然失图,复何言哉!若此,无心复与足下交矣。”嵇康叹恨自己“外恧良朋”,感愧“今都(吕安)获罪,吾为负之”。而这一切,都应该归咎于吕巽背信弃义:“吾之负都,由足下之负吾也。”在《与吕长悌绝交书》,嵇康深切表达了对这位相交多年的朋友的愤慨和失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嵇康与吕安的交往应该是志趣相投,心意相通的。嵇康不存在“悔与吕安交”。
第二,嵇康之死是时代政治环境,自身性格因素,小人构陷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吕安事件不是根本原因。
第三,沈德潜评价《幽愤诗》中嵇康“悔与吕安交也”是不确切的,应该是“悔与吕巽交也”。
(作者单位: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