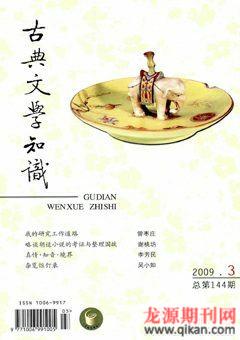我的研究工作道路
曾枣庄
我的研究工作杂而集中。言其杂,在古籍整理方面,我主编过大型断代总集《全宋文》,专题总集《宋代辞赋全编》(与吴洪泽合编);大型类书《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大型丛书《三苏全书》;作过全集注,即苏洵的《嘉祐集笺注》(与金成礼合注);选集注,如《三苏选集》、《苏辛词选》(与吴洪泽合注)、《三苏文艺思想》;作过校点,除校点《全宋文》约500万字外,还校点过苏辙的《栾城集》;作过资料汇编:《苏诗汇评》、《苏词汇评》、《苏文汇评》。研究工作也颇杂,先后出版过《杜甫在四川》、《苏轼评传》、《苏洵评传》、《苏辙评传》、《三苏传》、《论西昆体》、《苏轼研究史》(与中、美、日、韩等国多位朋友合著)、《集部要籍概说》、《宋文通论》。还出版过四本论文集:《三苏研究》、《唐宋文学研究》、《北宋文学家年谱》、《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言其集中,从上述不难看出,主要是集中于古典文学、宋代文学,特别是三苏研究方面。我的研究工作经历了由杂到集中再到杂的过程。
一 从研究乌托邦到研究古典文学
我从初中起就爱好文学,喜欢背诵古典诗词,一心想读中文系,整个高中阶段从未动摇过。但在高考前几天,全部计划都打乱了。那是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于统考前在全国单独招生,老师、同学都怂恿我去报考,我于是抱着“练兵”的目的报了名。那时的中国人民大学没有中文系,而新闻系只招新闻工作者,不招中学生,我没有资格报考。于是,随便报了个历史系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反正考上的希望极小,也没有打算考上。正因为如此,在考《中国历史》时,除答题外,我还花了不少时间去对试题提了一大堆意见。没有料到居然录取了,而且不准再参加统考。我就这样稀里糊涂读了以前连名字都未听说过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
上大学后的第一年,我仍恋恋于文学,曾要求转系,想转到新闻系,未成功。一天偶然读到朱生豪翻译的《罗密欧与朱莉叶》,对莎士比亚戏剧产生了兴趣,于是花了一年的课余时间读完了朱生豪的莎士比亚戏剧的全部译本。青年人的爱好是容易改变的,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是从空想社会主义讲起的,我很快对各式各样的乌托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西方莫尔的《乌托邦》到梅叶的《遗书》,从中国《礼记·礼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凡是我找得到的乌托邦著作,都找来读,并作了详尽的笔记。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教政治学、哲学,还继续研究过一段时间的乌托邦。然而不久,我这位学马列主义、教马列主义的青年教师却成了“反马列主义”,结果在川大“四清”中被批判了大半年。好在我出身贫下中农,最后从轻发落,仅被逐出大学讲坛,先后到中专、中学教语文,没有条件再研究我心爱的乌托邦了。但从此我也得到了解脱,又可以凭兴趣读书了,我于是又回到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上来。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因为读书爱做笔记、爱写文章几乎成了反革命,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在“等待运动后期处理”时,仍继续作读书笔记,继续写文章,没有打算发表,当时我已不可能发表文章,只是为了打发时间而已。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写了《理想与现实》、《真理与谬误》、《杜甫在四川》、《苏轼评传》等。
二 从研究杜甫到研究三苏
我真正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是在1972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出版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的扬李抑杜的鲜明倾向,使我为杜甫大抱不平,于是开始系统研读杜诗。也是边读边作笔记,最后整理成一部《杜甫传》初稿。但当时谁会出版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学语文教师的《杜甫传》呢?于是我只修改出了《杜甫在四川》部分,一是因为杜甫的现存诗有三分之二作于四川,研究杜甫在四川的生活与创作是研究杜甫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二是想以地方特色取胜,争取出版。我把稿子寄给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并附了一封酸溜溜的信,希望他们把稿子看完再决定是否出版。感谢当时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室主任杨莆先生,他硬着头皮读完全稿(他是写新诗的),并约我面谈,问明我的写作意图和写作经过,在同总编李致先生商量后,向我宣判:决定出版。就这样,我的第一部专著《杜甫在四川》于1980年出版了。以上可说是我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三苏研究阶段。我自来喜欢三苏的为人,但研究三苏则是在1975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以后。因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被定为儒家、反动派、顽固派、典型的投机派。骂苏轼为儒家,我无所谓,即使当时正在崇法批儒,但在我心目中,儒家未必不如法家;骂苏轼为反动派,我也无所谓,这是政治问题、立场问题,时过境迁,立场一变,结论也会变;骂苏轼是顽固派,我更无所谓,因为顽固也可说是立场坚定,是“不可夺者,峣然之节”(宋孝宗《苏轼特赠太师制》)的另一种说法。但骂苏轼是“投机派”而且“典型”,我就完全不能接受了,因为这是人品问题。投机者,迎合时势以谋取个人私利是也。在宋神宗、王安石推行新法时,以苏轼的才华,只要稍加附和,进用可必;但他却反对新法,并因此离开朝廷,投进监狱。在高太后、司马光当政时,以他们对他的器重,只要稍加附和,或稍加收敛,不要太锋芒毕露,不难位至宰相;但他却反对尽废新法,并因此而不安于朝,奔波于朝廷和地方上,“坐席未暖,召节已行,精力疲于往来,日月逝于道路”(苏轼《定州谢到任表》)。世间哪有这样不合时宜的“典型投机派”呢?
为回答这些问题,我决心系统研究苏轼。我认为,苏轼一生都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一生也都主张革新,只是具体的革新主张与王安石不同而已。他一生不仅在文学的各个领域颇富革新精神,而且在政治上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丰财”、“强兵”、“择吏”的革新主张,并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做了不少工作。他一生光明磊落,直言敢谏,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正如刘安世所说:“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惟己之是信。在元丰不容于元丰,在元祐则虽与老先生(指司马光)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宋马永卿《元城语录》卷上)他一生几起几落,但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苏轼《登州谢宣诏赴阙表》)。因此,我们不能说苏轼是什么顽固派、保守派、投机派或动摇的中间派,而应该承认他属于革新派,强调改革吏治,强调渐变,反对骤变。他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政治形势,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而他的根本政治主张,可说一生从未“动摇”过。这就是我在1980年前后在《文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的《论苏轼政治主张的一致性》、《苏轼〈与滕达道书〉是忏悔书吗》等系列论文和1981年出版的《苏轼评传》的基本观点。
我在研究苏轼的过程中,发现苏轼同王安石的政见分歧实际上从苏洵就开始了。过去有人说苏洵的《辨奸论》是伪作,但我从苏洵的其他文章以及苏洵同时代人,特别是苏洵的友人如韩琦、张方平、鲜于侁等人的言论中,发现了大量与《辨奸论》相似的观点,证明《辨奸论》对王安石的不指名批评并非“一反众议”,而是当时的“众议”之一,只是用语更加尖锐而已。于是我在研究苏轼大体告一段落后,为进一步研究苏轼的家学渊源,我又开始研究苏洵,撰写了《苏洵〈辨奸论〉真伪考》等文,出版了《苏洵评传》。
我在研究苏轼的过程中,还发现苏轼兄弟在性格、诗文风格、政治主张、学术观点、文艺思想等各个方面都很不同。为了比较苏轼兄弟的异同,于是我又撰写了《苏辙兄弟异同论》等文和《苏辙评传》。《苏辙评传》也可叫《苏辙兄弟异同论》,着重强调苏轼兄弟的不同。
三 从编纂大型总集到编纂大型类书
1984年我被调到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做负责人,1985年秋开始主持《全宋文》的编纂工作,我只好放弃了原有的研究计划,把全部精力用于编纂《全宋文》。经过全所的努力,1993年基本完成了《全宋文》的校点任务,1995年基本完成了审稿工作。
编书难,出书更难。编书再苦,我们自己还能控制,出书就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了。《全宋文》于1988年就开始出书,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和出版界。以后每年出几册,1994年出至第50册就停止出版了。巴蜀书社为出《全宋文》,赔了不少钱(每出一册要赔一万多元),实际上已无力继续出下去,但他们又不愿让我们另找出版社出版。直至2002年7月31日我们与巴蜀书社正式解除了合同,改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2006年8月,360册《全宋文》终于一次推出了。《全宋文》从上马到出齐,其间艰辛,一言难尽。《全宋文》出齐,作为主编,我本应高兴,但我却高兴不起来。我在《全宋文出版感言》中说:“主编《全宋文》,耗费了我整整二十年的时间,而且是年近半百到年近七旬的二十年,是人生最关键的二十年。理科,二三十岁是出成果的最佳时间;文科,五六十岁、六七十岁才是出成果的最佳年龄段。我病后八年的个人研究成果,超过此前成果的总和,就是明证。我对主编《全宋文》毫不后悔,因为它确实是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但如果有来生,问我还会不会再从事这样的工作,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不会。”
在《全宋文》的校点任务基本完成后,我又承担了大型类书《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编纂任务。从酝酿阶段开始,我就与闻其事,参加几次征寻意见的论证会,并被邀担任《中华大典》的编委,参加北京召开的工委、编委会议。但当时我的思想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我觉得“五四”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终结,现在确有必要对“五四”以前的文化加以总结,作为发展现阶段新文化的借鉴,并以之昭示子孙,传播世界。但另一方面,也深感兹事体大,需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现在未必能完成。正因为当时我有比较浓厚的畏难情绪,故最初不愿意参与这一工作。1993年程千帆先生和江苏古籍出版社来信,聘我为《中华大典·文学典》副主编和《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主编。程老是我一直尊敬的老前辈,程老和邓老邓广铭先生,在我主编《全宋文》时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作了很多指点,对我们帮助很大。程老要我参加,我是不敢推辞的。
但我深深懂得主编大型类书,比主编大型断代总集《全宋文》的难度还要大得多。《全宋文》所收集的资料已经够分散了,而《大典》资料的分散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编全文总集,整个别集、总集的文章部分可以全收,《全宋文》所收大家文章,有一册甚至数册都取材于一部书的,而《大典》连整篇文章全收的都极少,绝大多数都是节录,一部书往往仅节录一则或数则,是否当收及收文起讫都颇费斟酌。小家,我们为资料缺乏而苦恼。真正没有资料也好办,我没有,你也不会有。最令人担心的是自己认为没有别的资料了,读者却从一些常见书中为你指出一条或数条不应漏收的资料。中国图书如此之多,即使是常见书,也不是任何一个人所能完全读完、完全记着的。大家,我们又为资料太多而苦恼。大家不缺资料,取舍却更费神。校对的难度也比《全宋文》大得多,因为《全宋文》往往收整个集子中的文章,找到一种书就够我们校几天了;而校《大典》的每条资料几乎都要找一种书,找出来往往只校几百字甚至几十字,仅找书就花了比《全宋文》多若干倍的时间。而全部资料至少死校过三次以上,工作之繁重,也一言难尽。
在1997年2月北京召开的《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样书评审会上,戴逸先生说:“这本书的确好,非常有用,超过了自己的预料。《文学典》这第一炮应该说是打响了。书的最大特点是资料广博,材料丰富,大大超过了《古今图书集成》;其次书的框架比过去的书科学合理,查找容易多了;第三个特点是资料的出处标得比过去的清楚,给读者带来了很大的方便。”1999年10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出版座谈会上,戴老说了同样意思的话。我作为《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主编,对此书的不足之处,也是比较清楚的。关于框架结构,我曾给主编程老写信,主张应像一般史书的史传那样,传记在前,评论在后。1993年11月20日,程老和江苏古籍出版社的黄希坚先生共同署名给我回了一封长信,表明《文学典》还可以有与现在不尽相同的另一种编法:“可酌先生来函及原《隋唐五代典》两种意见,折中重订其先后次序如下:传记、纪事(作家逸事、作品本事)、艺文(以上属人);著录、论述(综论、分论)(以上属作品);杂录、图表(以上属其他)。”这一“折中重订”的“先后次序”,显然比现在已出版《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先后次序”合理得多。关于资料出处,类书一般只作为研究工作的资料线索,真正作研究都必须反查原书,因此资料出处就显得特别重要。《中华大典》的统一规定引用诗文只用两级标目,即作者加篇名。我们主张四级标目,即作者、书名、卷次、篇名。理由是:有些别集篇幅很大,数十卷,甚至一两百卷,只有作者和篇名,反查很费事;有些作者没有文集,其诗文是从总集、诗话、笔记、类书中收集来的,只有作者和篇名,根本无法反查;即使有文集传世者,其诗文也有辑佚得来的,只标作者和篇名,也无法反查。这都是此书不能尽如人意之处。
四 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扩大
因编纂大型总集和类书的需要,我的研究范围也有所扩大。在校点、审订《全宋文》的过程中,我对一些有兴趣的作家,作过一些研究,如夏竦、二宋(宋庠、宋祁)、丁谓、欧阳修、邵雍、范镇、黄庭坚、陈师道、李之仪、苏过、晁公遡等等,我都写过专论。但往往浅尝辄止,刚开个头,又被迫放下。
研究得稍稍深入一点的,一是辞赋、四六。我从编《全宋文》开始时,就想对宋文作较系统的研究,在校点、审订《全宋文》时,对一些有特色的宋文做了大量摘要。1993年《全宋文》的校点任务基本完成时,我就开始写《宋文通论》。撰写《宋文通论》的难点辞赋和宋代四六文。我先后发表了《论宋代四六文》、《风流嬗变,光景常新——论宋代四六文的演变》、《宋代四六创作的理论总结——论宋代四六话》等。辞赋也作过专题研究,先后发表了《论宋代的骚体辞》、《论宋代仿汉大赋》、《论宋代律赋》、《论宋代文赋》等专论。
二是西昆派。研究宋四六,首先需要研究西昆体四六,先后写有《西昆派的文论主张》、《〈西昆酬唱集〉的思想倾向》、《论西昆派作家群》、《〈西昆酬唱集〉诗人年谱简编》、《西昆十题》等,并在台湾丽文出版公司出版了《论西昆体》。
三是李之仪研究。我在审《全宋文》李之仪文时,对其诗文词都产生了兴趣,想写本《李之仪研究》。但仅撰写了《李之仪年谱》、《姑溪居士杂考》、《姑溪居士的文艺思想与创作成就》、《姑溪居士的词论与词作》等文,专著则至今未完成。
四是《集部要籍概说》和《宋代文学编年史》。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组织为高校文科编写一套参考教材,裘锡圭先生为主编,要我承担此书的编写任务。因为是教材,只能概述学界公认的观点,因此我对此书不甚看重。但正如一位日本朋友所言,可作简明中国文学史读。通过对历代别集和诗文著作的简介,确实提供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
中国史书有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章体。典章体史书是指《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所谓十通,专门记载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有关体制。文学也有自己的体制,这就是文体,诗文词曲的各种体裁。《宋代文学编年史》主要借鉴中国编年体史书的写法,同时汲取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章体、史赞的长处,在文学史撰写体例方面做一些尝试。
五是文体研究。为解决《全宋文》的编纂体例,我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来研究历代总集、别集的文体分类及编序,写成了《〈全宋文〉的文体分类及其编序》一文,这是我研究文体的开始。2005年第6期的《乐山师范学院学报》发表了饶晓明先生的《新近发现东坡词考辨补证》,把《苏轼诗集》中的长短句诗都说成是词,这更使我感到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文科学生太缺乏文体知识了,决心系统研究文体问题,现在正同时编、撰《中国古代文体资料汇编》、《中国古代文体学》、《中国古代文体词典》,这就是我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
五 结语
我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逐渐悟到,从事研究工作,一要有明确的研究方向。我读书是比较杂的,最初爱好文学,故读了不少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后来对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了兴趣,又读了不少这方面的中外典籍。被赶下大学讲坛后,又泛读古籍。真正开始有明确的研究方向,是在研究杜甫、三苏以后。人生精力有限,真正能在一两个研究领域有所突破,就很不错了。这里有一个博与专的关系问题,我觉得读书宜博(即使随便翻翻也好,可以引起你对某些问题的注意),研究宜专,真正对一两个领域作了深入研究,知识面自然就扩大了。我跟着苏轼转了几圈,就大大扩充了我的知识面。有了明确的研究方向,就会注意收集所研究问题的有关资料。否则,一些极有价值的资料,就会在眼皮底下跑掉。以后想起,可能再也查不到了。
二要全面占有资料。我这几十年主要是在做资料员,《全宋文》、《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三苏全书》、《苏诗汇评》、《苏词汇评》、《苏文汇评》等都是资料汇编。至今仍有人看不起资料工作,但不是建立在全面占有资料基础上的所谓“新论”,即使能造成轰动效应,也不可能持久。
三要弄清基本史实。进行作家研究,我主张从作年谱开始(如果该作家没有年谱或虽有年谱而太简略的话),对该作家的生平事迹及其作品先进行编年。我觉得只有如此,研究工作才比较扎实,不致写起文章或论著来,张冠李戴,东拉西扯。故凡我有兴趣,想进行系统研究的作家,我往往先为他作年谱,除《北宋文学家年谱》所收我撰写的5种年谱外,还有好几种年谱的未完稿(《田锡年谱》、《二宋(宋庠、宋祁)年谱》、《晁说之年谱》、《释惠洪年谱》),均因别的工作未能如愿完成。我指导学生进行作家研究也很强调年谱的重要性。1983年我为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培训班的学员开《三苏研究》,并负责他们的实习。为帮助他们校注苏过的《斜川集》,我把未完稿《苏过年谱》拿出来,供他们参考,并嘱咐他们在校注过程中加以补充和订正。当时的学员、现在已接替我担任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的舒大刚先生用力最多,他作了较多的补充和修订,我的初稿只能算引玉之砖,收入《北宋文学家年谱》的《苏过年谱》,基本上应算大刚个人的成果。我还曾建议本所吴洪泽先生专门研究历代年谱的体例及其演变,收集整理宋人年谱,撰成《宋人年谱集目》,编有《宋人年谱丛刊》。我指导日本庆应大学博士生池泽滋子女士研究丁谓,我也要求她先作《丁谓年谱》,然后在此基础上撰写《丁谓研究》。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