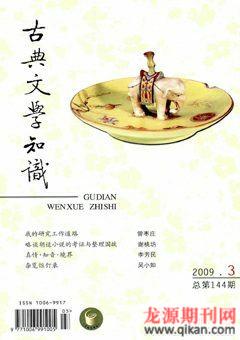范当世与陈三立的文学交往
龚 敏
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陈衍于京城所列的“诗人榜”中,陈三立位列第三(第一未设,第二为郑孝胥)。1925年,汪国垣在《甲寅》周刊连载《光宣诗坛点将录》,以三立为“天魁星及时雨宋江”。由此可见陈三立在晚清诗坛诗名之盛。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提到陈三立“早从通州范当世游,极推其诗”,并对陈、范二人诗学之异同作出比较:伯子“工力甚深,下语不肯犹人,峻峭与三立同。而三立笔势壮险,仿佛韩愈、黄庭坚。当世意思牢愁,依稀孟郊、陈师道”。在汪国垣根据地域对近代诗系所作的划分中,陈三立身居闽赣派领袖之位,范当世虽不著籍闽赣,却以“他籍作桴鼓之应者”,“与闽赣派沆瀣一气,实大声宏,并垂天壤”(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可见,范当世之诗名、诗艺不在陈三立之下,考察范、陈二位的文学交往,对同光诗派内部的研究实有充实、加深的重要意义。
陈、范二位不仅诗路接近,更是好友兼儿女亲家。三立年纪比当世长三岁,陈三立应是先与当世二弟范钟结识的。光绪十七年(1891),范钟由江西萍乡人李有芬推荐,前往陈三立的父亲湖南巡抚陈宝箴处教其孙衡恪,并由此附以婚姻,订下了侄女范孝嫦与其学生陈衡恪的亲事。这门亲事双方都十分满意,陈宝箴曾写信给范钟,表示陈家儿子品学与范氏兄弟相类,孙子师曾(衡恪)又与彦殊(范罕)略同,真可谓门当户对。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范当世离开天津李鸿章幕府赴江夏湖北按察使署省亲嫁女,也就是从这年开始,我们看到《范伯子诗集》中有了与陈三立的赠答之作。
两人初识便一见如故,不欲分离。这大约与他们在诗学路数上的相近有关,由此当世吟出了“海内飘摇数十公,更能坚许两心同”(《余以岁暮疾还里,濒发而为风浪所阻,乃又喜与伯严兄得稍聚也,抚事有赠》)的诗句,可以想见两人在湖北赠诗往答,互为引重,并互相引为诗学上的知音。其时当世以岁暮欲归里,然为风浪所阻回程,心下却“又喜与伯严兄得稍聚”,真是“爱极翻成无不舍,归心忽断喜心回”。“既与伯严稍稍赠答,无几而决行矣,携大集以归”,当世又一路吟道:“余独何为惜今日,支离撼顿一逢兄。寒江照此双心合,夜雨怜渠独角成”,“谈余低首乘流去,窃把君诗海上城”,只“双心合”一句已见浓重的惺惺相惜之意。及至当世回乡,又有“毕竟栖栖有余恋,复从篮辇梦君游”(《里中岁晚郊行》)之句,推重之意尽诉诸笔端。
后六年间,两人酬唱投赠之诗不多。及至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三立父陈宝箴逝世,当世前往南昌吊唁,《伯子集》中始又见二人唱和诗。这六年之中,范当世多里居家乡通州,后赴广东谋取差事未果,期间目睹戊戌、庚子事件,诗作中多呈现帝王国事之忧。陈三立与其父亦在此期间经历被革职、隐居西山,及至陈宝箴去世,家事国难,凡此种种皆令三立痛感忧心,承受着沉重的压力和心灵的创伤。好友范当世抱着衰病之躯亲自前往江西吊丧,此举给予三立许多安慰。当世在一首诗中写道:“壮日吟朋呼啸处,却扶衰病又经过。国闻家事皆抛撇,离合悲欢一刹那。雨不入江秋水浅,楼刚出市夕阳多。哀来独眺西山友,濡滞依然奈尔何。”(《九江迟船怅望伯严》)诗中所流露出的对壮日不再的哀伤、对衰病缠身的无奈、对家国之事的不堪之情不只是他个人的。受陈三立托付,范当世为陈宝箴作《墓志铭》,他通过对墓主生平事例的选择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了他对陈宝箴素来所有的敬重。尽管在国事上,陈宝箴与范当世的幕主李鸿章持不同政见,而且曾对范氏兄弟语出讥诮:“若兄弟皆主李者耶!”然当世并未因此愤愤不平,反而在文中平心道出其语出讥讽的深层原因:“然吾后得其平心之言,则公尤望李公极知不堪战,不以死生去就回上意,而猥随俗塞谤取祸败空国至于斯也。”这篇墓志对陈宝箴生平的陈述和评价都十分客观,陈三立对此亦十分满意,赠送当世影印的日本遗留之宋刻《黄山谷集》作为润笔表达谢意。由此亦可见,两人在诗学上对黄山谷有一种共同共通的心绪情结。在为哀悼陈宝箴所作的《伤秋五首》诗中,当世写得很有悲壮的味道,描绘出险恶的时势,并时时发出“谁将救时涸,云里唤飞龙”这样的呼喊,有一种感慨时人不再的意味,并不是单纯地寄托哀思,更是借此抒发忧国之心。
丧父对人到中年的陈三立打击甚深,他在西山哭墓诗中屡屡抒写作为“孤儿”的伤痛:“扶服崝庐中,气结泪已凝。……终天作孤儿,鬼神下为证”(《崝庐述哀诗》);“群山遮我更无言,莽莽孤儿一片魂”(《雨中去西山二十里至望城冈》)。这“眼花头白一孤儿”的凄切孤苦之感还包含着更深广意义上的情感“失怙”,在末代王朝,不少古典诗人都有类似心理失怙的情感体验,范当世亦不例外,因此他能够充分理解陈三立的痛苦,并给予共情:“怜君似我无根蒂,仍向江山泪眼开”(《伯严卒哭同行舟中有赠》),家——国的锁链已经松动,他们同为失怙人,同为无根蒂的漂泊者,因而更有着“道在人群更不喧”(陈三立《寄肯堂》)的默契与感应。这种默契感与知音感在三立所写的这首诗中亦有反映:“吾尝欲著藏兵论,汝舅还成问孔篇。此意深微俟知者,若论新旧转茫然。生涯获谤余无事,老去耽吟倘见怜!胸有万言艰一字,摩莎泪眼问青天。”(《衡儿就沪学,须过其外舅肯堂通州,率写一诗令持呈代柬》)诗中表露出当世不仅与他在文学上互相匹配,又是他胸中难以言明的深微之意的知者。
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二十九年(1903)间,范当世来往于江宁好友俞明震席上,时三立亦在江宁,故这段时间两人唱和往来颇多。二十八年中秋,范当世与陈三立、俞明震、陶榘林、薛次申等人在金陵共同赏月,当世与三立都有诗记道此事。是晚,众人本相约复成桥,“至则风甚,月不莹不能望远”,这让三立觉得十分扫兴,“遂欲出马路穷探”,当世笔下形容道:“吾知陈生兴堕空,只欲疾走争冥鸿,藉非有妓哀疲癃,遂入深深灌莽丛”,“疾走”、“遂入”二句让人想见三立情状。后乘舟至四象桥,“月色转莹”,“澄辉朗彻天当中,直鉴豪发无昏瞳。可怜四象桥边水,正照天涯两秃翁”,朗朗大月之下,“两个秃翁”徘徊良久,“翩然弄影墟墓中,踯躅掩泣波双瞳”(陈三立《中秋夜……次肯堂韵》)。是年中秋,当世并为三立录甲午年在天津所作之《中秋次韵高季迪张校理宅玩月》诗,录至“人间佳节复有几,沦失八九钟阜南”之句,“觉向时所惋惜能偿以此日之游,而今此所悲哀复绝异于当年之事,伯严愈有‘旦莫承平更百忧之作,感痛可胜言哉”。辛丑年之后,国家更加分崩离析,丧权辱国之条约越签越多,时局每况愈下,两位诗人心中之沉痛,无以复言。时局昏暗,月光却朗照乾坤,站在高寒大月之下的诗人们,“拼将特地清醒眼”(范当世《为伯严录天津甲午中秋诗》),所感到的却只是“大月难窥澈骨忧”(陈三立《肯堂为我录其甲午客天津中秋玩月之作》)。
二十八年冬至前夕,陈三立回江西省墓,当世作诗惜别:“不醉几番真负汝,曰归何事益悽然。惟应岁晚风涛我,落照湖山有泪涟”(《酿雪不成送伯严江西省墓》)。别后的三立特别怀念“放艇江南三四年”,“几共子吟狂雪外”(《雪夜再和肯堂兼感近事》)的日子。然自此以后,两人“暮年怀抱自天壤”,只能“怀人落日满江海,解对琵琶微叹嗟”(陈三立《怀范大肯堂》),唯有借着诗歌往来,各自抒写怀抱。二人年岁相当,同处末世,诗歌路数也相近,因此有许多共通的话题和情感。时正值岁末,自然界的寒冷、时代末世衰败的景象同时刺激着他们,因此他们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无奈悲愤的感情亦是那么共通,二人的知己之感也益深。两人其实都才中年,却都有衰暮残年之感,当世吟出“老病孱颜为君笑”(《云秋奉命治军淮上伯严招同为之寿五十》),三立念出“只余残泪洒残年”,“两人鬓影自摇天”(《和肯堂雪夜之作》),这其中充满了他们作为个人对于时局政事的无助感以及个人生命的无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