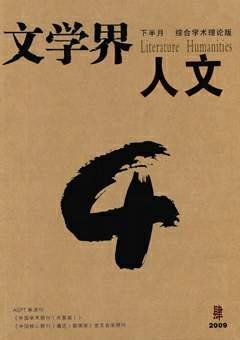简论贺岁片《非诚勿扰》的后现代性
彭在钦 李石光
摘要:冯小刚的贺岁片《非诚勿扰》令人耳目一新,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其影片中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倾向是对现代性的反思与超越。否定与批判中的游戏、陌生城市里的观光者、爱情友情的追寻与超越等等,均展现了对否定性继承之超越的后现代性内涵。
关键词:《非诚勿扰》;后现代性;游戏;超越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9)04-048-03
作者:彭在钦,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石光,湖南科技大学2008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湖南,湘潭,411201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社科基金重点项目(08A020):“现代性”与百年中国文学潮流研究
贺岁片,顾名思义,是指新春佳节的辞旧迎新之际,为贺岁档期而量身定做、专门打造的影片。为了增强喜庆的色调,吻合贺岁的吉祥气氛,符合当今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进而追求商业利益与社会价值。贺岁片往往采用搞笑戏谑、喧嚣热烈的表现形式,呈现一定的草根性和媚俗性。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贺岁片逐渐成熟,不拘一格地呈现或深或浅的文化内涵,不仅启发、开拓当代观众的生命意识与觉悟,而且展现出了批判、审视与反思的人性关怀。无疑,冯小刚是中国贺岁电影的肇始者也是最成功者。在2008年这个多事之秋的年尾,他推出的贺岁片《非诚勿扰》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不仅获得3亿多的票房价值,还赢得影评界的高度关注。笔者试从后现代主义哲学对现代性的反思与超越之角度,来管窥《非诚勿扰》的后现代性元素及其动态形式。
一、游戏中的否定与批判
当代社会的发展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阶级发生了新的变化。中产阶级如雨后春笋矗立在历史的舞台上。英国评论家卡林考斯认为新出现的新中产阶级是后现代主义的阶级基础。他们的社会地位介于资本家和劳工之间,他们嫌弃传统的价值观,热衷于参与文化娱乐活动。现实生活的物质丰富与精神困乏使得他们在困惑与快乐,焦虑与狂喜中挣扎着狂欢,并使他们充满游戏精神,生活环境成了游戏场。“游戏”,是西方文学话语传统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历史上,康德、席勒、斯宾塞、弗洛伊德、伽达默尔等人都曾经从各个方面阐述了“游戏”概念的重要程度和价值。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游戏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和更深层的因素。在后现代主义要求消解意义的同时,历史真相的可靠性也成为悬疑。通过游戏的方式取消意义的唯一性和必然性是很多后现代主义学者所热衷的做法。
《非诚勿扰》里:葛优饰演的秦奋是一个“三无伪海龟”,由于其“天才发明”被范伟饰演的“天使”风险投资人出天价买断而一夜暴富,于是秦奋开始了“征婚”旅程。在海外,“蹉跎中练就一身生存技能”的秦奋眼光深刻毒辣,游戏人生,但骨子里刻着的真诚和放下的淡定,有着一种超然理想主义情怀。
影片的开头,插入的黑白战争电影和建国时影像资料以及马丁·路德·金的演讲影像资料等,与后面繁华兴旺的城市的中产阶级生活形成强烈对比,其一是呈现出后现代的草根叙事对革命的理想叙事的解构;其二,插入的影像资料正是秦奋为了推销其“天才发明”而制作的广告,说白了是为了撮钱。影像资料与现实目的形成鲜明对比。从而为全影片确立了否定与批判的游戏性基调。
《非诚勿扰》讲述的是一场通过征婚来不断相亲的游戏。我们不妨来看看不断相亲的过程及其当事人,就会知晓其中奥妙。影片自始至终是围绕相亲这个主题展开的,爱情无论是在文学世界还是影像世界都是被高度关注而神圣化的母题,但在《非诚勿扰》中不过是生活游戏的引子和狂欢的噱头。
秦奋第一次相亲就遇上了十多年前的男同事:一直暗恋他的同性恋者建国,这本身就是对一心想找一个媳妇结婚生子的秦奋之欲望的嘲弄与消解。秦奋第二次相亲碰上一个感到顺眼却一心是为了推销墓地的胡静,郎有心而妾无意,最后把他架在孝子的高位上,媳妇没娶上,先买了块墓地。娶媳妇生子意味着生,但墓地隐含着死,这是死对生之意义的消解。第三次的对象是梁笑笑(舒淇饰),她是一个外表冰冷内心狂热的重情义的女孩,却是个“小三”,并且非诚心征婚。酒后吐真言,两人擦肩而过。此后,秦奋继续着他的相亲经历,一个是少数民族的,家住遥远的地方,回家要坐飞机、火车,另加一天的拖拉机和一天的牛车,并且分手的话会打断秦奋的腿;一个是患有健忘症,第二天会忘了第一天所有的事和人,秦奋让她别记了今天的事,她竟然问秦奋今天来是什么事;还有一个是性冷淡,告诉秦奋一年一次的夫妻生活比较合适……在飞往杭州的飞机上,秦奋又遇到了梁笑笑,并且遇到了梁笑笑喜欢的有妇之夫(方中信饰),秦奋在飞机上跟梁笑笑说有空找他聊天。梁笑笑约秦奋喝酒,秦奋说约了人相亲,梁笑笑愿意同去,秦奋约见了格瑞丝(徐若瑄饰),格瑞丝得知秦奋喜欢小孩,兴奋地告诉秦奋她怀了小孩,秦奋无法接受,苦笑着让格瑞丝离开了。梁笑笑带着秦奋去见有妇之夫,并说秦奋是她的男朋友,秦奋无法忍受有妇之夫对梁笑笑的关怀,说出了真相,离开了。最后,相亲的对象是炒股女郎,在话不投机的接触后,最终达成共识“现在大市不好,千万别盲目入市,“观望!”,结局还是离开。影片取名《非诚勿扰》,但相亲者们各怀鬼胎,根本谈不上非诚勿扰,用秦奋的话来说:“看来这征婚是挺不靠谱的一个事,我总结了一下,歪瓜裂枣的咱看不上,但凡长得有模有样看着顺眼的不是性冷淡就是心怀鬼胎,心理健康历史清白的姑娘都哪去了,我怎么一个都碰不上啊!”。影片最后的完美的爱情结局也是在女主人公为“小三私情”死而后生的基础上才实现的。这场爱情因此构成了整体性暗喻结构,意味着要对现代性进行全面解构与超越——死而后生,才能真正消除其弊端。
二、陌生城市中的观光者
城市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现代化的象征。高楼大厦、商贸中心、巨幅广告、摩登女郎、股票交易等等城市符号,是人类对现代化的印象与理解。正如陈晓明所言:“喧嚣热闹的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他的各种符号——包括城市地图、街区分布、各种标牌明示的场所:商店、饭馆、剧场、咖啡店、酒店以及处理公共事务的政府部门,这些不同的城市符号仿佛都在向你发出邀请和暗示;另一方面城市的这些符号又是一种冷漠的拒绝,他以‘陌生化的环境——建筑环境、语言环境、交往环境等拒绝了所有的‘城市他者。”因此城市以其暗示规则的“现代化”来建构其暧昧性和模糊不明性。
《非诚勿扰》中所有的故事情节都是在城市里展开。在看似荒诞却痛彻心扉的“相亲”过程中,高楼大厦、商贸中心不断迎面扑来,在风景如画的背影里,张牙舞爪。而影片本身的插入式广告就是消费社会的形象说明,从而整体上构成解构与建构的巨大悖论。于是,在似是而非的陌生化环境里,正在狂欢的人们需要死而后生才能找寻到真爱。秦奋在改革开放之初出国,回国后难免感到陌生,有如路人在旅游。那段历经九死
一生而得来的真爱也被放置于日本北海道的旅行途中。通观全片,你会发现,无论是背景、音乐、情节,还是人物形象,都给人一种旅游之感。片中相亲的芸芸众生,都有如旅游的观光者,不知所往,不明所云。现代化给予他们无限膨胀的欲望,却束缚了他们对自由的想象。从此,他们永远和事物的核心、世界、历史与时间的真相拒之千里,他们浑浑噩噩的人生将永远是一场旅行,他们自身是其中的观光客之一。
三、爱情、友情的追寻与超越
至于后现代主义,我国国内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继承了尼采、海德格尔对现代主义哲学的一种极端主义,持全面否定批判的观点。另一种是在具有否定、破坏性一面的同时,还具有建设性,并提倡创造性,提倡多元的思维方式。笔者以为,《非诚勿扰》影片中后现代性显现为后者的特征。后者被誉名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针对现代性中“个人中心主义”的观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不要把人物割裂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个人与社会,与他人之间存在有内在的本质联系,在与他人的联系中表现个体特性构成了自己的身份。《非诚勿扰》一片自始至终把人物放置在人际交往中,潜伏在神圣的母题里,来对现代启蒙理性进行否定性继承上的超越。冯氏幽默的阶段性升华
在《非诚勿扰》里,正如其影名,诚信一直是或者说是导演试图坚持的救命稻草,这一点,卜文军的论文《将诚信进行到底——从<非诚勿扰>看冯小刚电影的生命力》中进行了论述。他认为诚信是其永不更改的底色,将诚信进行到底,是拥有旺盛生命力的食粮。诚信使冯氏影片具有较强的亲和力、感染力、生命力。但笔者以为,冯小刚或者说秦奋(葛优)一直坚持的是对理想主义的爱情和友情的向往与追求。爱情和友情的向往与追求是一直贯穿影片的主题。
在漫长的相亲旅途里,创作者不断对此主题通过搞笑戏谑,冷嘲热讽地否定、批判、解构。狂放的游戏里,诚与非诚的不断的摩擦、碰撞使得爱情与友情上升到悲天称世、救苦救难的人性关怀的神性地位,从而赋予了对现代性的否定性继承上之超越性意义。秦奋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一直在寻找,那个和自己一样的带有些许性情的人。这种寻找是痛苦的,是孤独的。梁笑笑何尝不是性情中人?就如笑笑说的“一见钟情不是你一眼看上了我或者是我一眼看上了你,不是看,跟心灵也没有关系,是气味,彼此被对方的气味吸引,迷住了,气味相投”。他老笑她傻,他又何尝不是像一个傻瓜样陷在爱情里无力自拔。在道德伦理层面上,“小三”是社会所不耻的,但笑笑(舒淇饰)对有妇之夫(方中信饰)的那段出生入死的婚外之恋,不正是对前面那群玩相亲游戏的芸芸众生的尖锐反讽。至于友情,影片中也先后提到几处。先是秦奋与笑笑饮酒时,讲的关于小白的故事,朋友的出卖导致小白的逝世是对友情的第一层解构;再是,秦奋到海南相亲,朋友给他说媒时将女方说得天花乱坠,现实证明此女乃一性冷淡!友情至此还有何诚信可言?但影片的最后,秦奋欲回国时,与邬桑告别,他拿出一叠信封装着的钱送给邬桑,并满怀忧虑地说这钱是给他妻子和孩子的,不缺钱,缺的是朋友!邬桑一个人开着车,在北海道起伏的山路上唱着和秦奋一起唱过的歌,唱着唱着哽咽了,慢慢停下了车,伤心地哭了。哭过了,又开车走在绵长起伏的山路上,渐渐消失了。唱的是《知床旅情》,也是影片为远离的友情送上最后一首悼词。这里的爱情、友情因此上升到哲理层面。
毋庸讳言,“真实的伦理问题从来就只是在道德的特殊状况中出现的。”难道不是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掩盖、扭曲个体性的生命体验?不去关注“这个令人心寒而又诱人的世界”上每个“零落之生息”。“用对个体命运忠心耿耿的目光深情地注视现代社会中破损的个人道德感觉”,“体味在这个生活制度中生活的个人眼里噙着的泪光”。
冯小刚的《非诚勿扰》取得空前的成功,有其必然性:在于冯氏幽默的方式及演员葛优的个人魅力,更在于其紧握时代脉搏、美学变奏与人性关怀,并体现出后现代主义哲学对现代性的反思与超越。这是“时代弄潮儿”的独立的超越性的努力;是对启蒙现代性的否定性继承之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