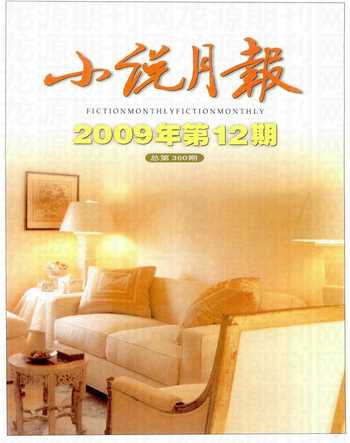少年辽西
坐席
马莲出阁那天,夜里下了一场雪。早晨我在被窝里刚醒,就听见父亲在外屋地上跺着脚说,这雪下的!有半尺多厚,我看马莲这孩子没什么福。母亲拉着风匣问父亲晴天了没有。父亲说天倒是放晴了。母亲说,只要晴天就不碍事了,人家今天才是正日子。
马莲出阁的事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我就听见母亲跟父亲说,马莲已经有日子了,问我们家随什么礼。我们村有随礼的习惯,谁家有个大事小情,你一点儿表示没有,就会被人说成是灶坑打井、屋顶开门、不擗菜叶子的吝啬鬼。父亲想了想,问,四儿那时候他们随的啥?父亲说的“四儿”是我四姐,她是去年出的阁。母亲说,我记着呢,是一双袜子。父亲说,那就买双袜子吧。母亲说,不差差样?父亲说,送条围巾太贵了,送一对小镜子又怕重了,没用;还是送双袜子吧,到啥时候都穿得着。第二天父亲就骑着毛驴儿跑了十多里地,到供销社买回一双袜子,是那种大红色的,袜桩上还印着两只小喜鹊。母亲爱惜地看了看,说行,挺喜庆的。然后就让我给马莲家送了过去。
送去袜子之后,我就把马莲出阁的事忘了,准确地说是没当成一回事。丫头出阁比不得小子娶媳妇,小子娶媳妇才叫热闹。新媳妇进了村,当天没大小,不管男女老少,都可以堵在门口里要喜糖,抢喜糖。抢不到喜糖的,就抢新媳妇从娘家带来的随身物品。捞着啥抢啥,扒鞋的都有。要想被抢去的东西物归原主,就得拿喜糖来交换。晚上,还得搅酒,摆一桌酒菜,让新郎新娘挨着个儿地敬,却不痛痛快快地喝,而是百般刁难,不是问新媳妇这个,就是问新媳妇那个,不是让人家这样,就是让人家那样……净出幺蛾子。羞得新媳妇一个劲儿地捂脸,还不许恼。一直闹小半夜才散场。估计小两口该休息了,睡觉了,一些好事的坏小子还可以踅回去,蹲在窗子底下听听声……特有意思。因此,村里的男女老少,都盼着娶媳妇。尽管娶来的媳妇与自己没什么关系,也盼。至少她可以给苦闷的山村带来一种短暂的喜庆与欢乐。
丫头出阁就没这么热闹了。无非是在正日子那天摆上两桌酒席,请请那些随了礼的亲戚朋友和老邻旧居(都是大人们的事,与孩子无关)。第二天,婆家那边来一驾大马车,或来一辆小驴车,有的干脆牵来一头驴,把个哭天抹泪的丫头一接就走了。剩下一村子的寂寞与没趣儿。谁还把这样的事当一回事呢?
吃早饭的时候,父亲突然宣布说,这次坐席他不去了。
一般地说,坐席都是一家之主的事,或者说是男人的事。只有男人有事不在家的时候,女人才出面。母亲不解地看着父亲,问他是不是不舒服。父亲不慌不忙地喝尽碗里的最后一口粥,然后,他郑重其事地叫着我的大名,说这次坐席让我去。
我听了一怔。
平常,父亲和母亲都是叫我“学生”,这次父亲意外地使用了我的名字,听起来感觉有些陌生,同时,父亲让我去坐席这件事的本身也很突然,让我吃惊。
我说我不去。
父亲问,今天不是星期天么?
我说,那我也不去,我还想去套鸟哪。
辽西的冬天漫长而枯燥,只有下了雪,才会给人一种别样的生机与乐趣。一场大雪之后,房子、树木,以及周围的山山峁峁,全白了,大地一片静谧。在这样的天气里,我们一些男孩子最喜欢做的就是套鸟了。套鸟首先得扎套子。我们跑到生产队的马圈里捡回一些白色的马尾,找来秫秸秆,揻成三脚架。然后,用小刀在架子上扎出小缝,再用一片席篾儿顶着马尾往缝里一塞,把马尾套子夹住。这样一个挨一个,越密越好。套子扎好之后,找一片鸟儿们无食可觅的地方,扫去浮雪,埋上套子,撒点谷糠之类的食物,人就可以回避了。估计差不多的时候,跑去一看,梦幻一般,果然有鸟儿在那里张着翅膀扑棱呢……会哨的,或者好看的,像“风头”、“三道门儿”什么的,就剪去翅膀,或装进笼子里,养着玩;要是麻雀之类,则包成个泥团埋在火盆里烧。烧得恰到好处时,剥去泥丸,喷香的一个小肉蛋儿就出来了。坐席有什么意思?
父亲看着我说,你也干点儿正事!
我不认为坐席就是什么正事,至少,对我来说不是。我还是个孩子。我没坐过什么席,也不会坐。
我把目光转向母亲的时候,母亲也正在看着我。以往遇到我不愿意做的事,母亲差不多都会替我说话,可这次她分明地站在了父亲一边。
她说,你吃还不会?你去了,也让赵旺家的看看,我的小子能坐席了!
赵旺家的就是马莲她妈。过去我常听母亲念叨,马莲她妈一连生了五个丫头,自己没儿子,看谁家生出个小子她都眼气。母亲也是一连给我生下四个姐姐,怀孕第五胎的时候,马莲她妈逢人就说,等着吧,她要是生出个小子,我把两个眼珠子都抠出来!结果,后来母亲生下我的时候,马莲她妈是最后一个来下汤米的。一进屋,她还不太相信似的在我的腿裆里摸了一把……当时,她那才叫不好意思呢。
听了母亲的话,父亲有些不以为然,他说,行了行了,都啥时候的事了,你还磨叽!
母亲温下声来说,不是我磨叽,她不是要把两个眼珠子都抠出来吗……这么多年了,她咋一个也没抠出来?
正说着,马莲的四叔来了,问我们家晌午谁去坐席,好安排桌。
父亲又一次报出我的大名,而且语气郑重,听起来有一种隆重推出的意思。
马莲的四叔看了我一眼,他说那就坐头悠儿吧。
父亲不容置疑地说,让他坐二悠儿。
那时候,遇到婚丧嫁娶,还不时兴上饭店,村子里也没饭店,都是在家里摆酒席。家也不大,差不多都是三间土房,最多的可以同时摆两桌:东屋一桌,西屋一桌。坐得下,就一勺烩了;坐不下,就得分“悠儿”。一般地说,头悠儿坐女桌,女的不喝酒,散席快;男人都被安排在二悠儿。
我坐的是二悠儿。
尽管十分不情愿,后来我还是去了。这是没办法的事,我没有理由违背父亲的旨意。即使有理由也不行,他毕竟是父亲。再说,我也不愿让他骂我不闯荡,没出息,是个见不了大天儿的“夹尴头”。
到马莲家去的时候,我走得磨磨蹭蹭。村子里到处覆盖着厚厚的白雪。沟沿的那棵老榆树上,聚集着许多麻雀,唧唧喳喳地叫着,像是在讨论雪天里到哪儿才可以找到食物。村子里很静。三十多户人家,一半靠近南边的大沟,另一半稀稀落落地散落在山坡上,中间是一条狭长而弯曲的村道。我们家住在村东头,马莲家在西头,平时除了万不得已,我很少到村子西头去。我怕老刘福多家的狗。老刘福多家在村西头的一个坡坎上。他们家养着一只大黑狗,整天趴在门口外边。人从坡下一过它就会跳起来狂吠。父亲的经验是,它不咬人,就是瞎咋呼。但是你可不能跟它对着眼瞅,也不能跑。因此,每次我不得不从老刘福多家经过时,尽管心里害怕得不行,却不得不硬着脖子、夹着腿慢慢地走过去……
我来到马莲家的时候,坐席的人已经到了很多,沾满雪水的破鞋脱了一地。那时候坐席都是在炕上,还没有圆桌,要是有圆桌就好了,两间屋子,地上搁一桌,炕上搁一桌,就不用分悠儿了。
那天,给马莲家“支客(qiě)”的是王少泉。村子里办红白喜事,都要请个能料理事的人,现在叫“知宾”。这人要能说会道,出了差错,会打圆场,死人也能说活了。还得好酒量,遇上能喝的客人,必须要一陪到底。总之,就是要替东道主把亲戚朋友都支应得乐乐呵呵,不能让亲戚朋友挑了礼。知宾的人不坐席,而是这屋那屋地转,来回视察,看有没有可料理的事。即使没什么事,也是一脸很忙的样子。
王少泉五十多岁,长瓜脸,嘬腮。平时我不太喜欢这个得叫他“五叔”的人,见了面,他总是揪着我耳朵,问我睡觉又尿炕了没有。挺讨厌的。不过,这次他却很响亮地叫着我的大名,让我脱鞋,上炕,回腿往里……看来,坐席的确是一件很严肃、很庄重的事。
最后到的人是老刘福多。他快八十岁了,腿脚已经不太灵便,是刘三背着他来的。刘福多六个儿子,除了老大去年娶回一个寡妇,其余五个还全是光棍儿。刘三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他把背上的刘福多放在炕上,抽身便走,王少泉招呼说,你站下得了。刘三却头也没回,跟谁赌气似的,一声不吭地走了出去。
该来的人都到齐了。王少泉便招呼大伙开席。听说开席,我突然有些紧张。其实,临来之前,母亲就把坐席的一些注意事项跟我讲了。她告诉我,看别人吃菜了,才能动筷,夹一口菜就把筷子放下,不能连着吃。夹菜的时候,不能夹别人跟前的菜,更不能满盘子乱翻……没想到坐席会有这么多讲究。而且,吃菜不说吃菜,叫“取着”;喝酒也不说喝酒,叫“走着”。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既郑重而又陌生。特别是夹在一些大人之间,我感到非常拘束、别扭。好在那些大人似乎没怎么留意我,只是不停地“取着”、“走着”……
菜一道一道端上来。
我觉得每道菜都非常好吃,香!但是没有一个人说香的,所有的人都显得漫不经心,一种很见过世面的样子。村里人自有村里人的自尊与风度。
赵素云今年多大了?
虚岁十六。
登上记了吗?
登啥登,先结婚,到了岁数再登一样,啥也不耽误。
也是。早打发早利索……
他们说的赵素云就是马莲。她瘦高个儿,大眼睛,梳着两条齐肩的辫子。我进屋的时候,碰见她正在外屋里切菜,好像今天不是她出阁,而是在给别人忙碌。见了我,她还吐了一下舌头,莫名其妙地一笑。
说了一会儿马莲的事,人们的话题就散了。开始谈天说地,说眼下的这场雪,说开春后的青苗……都是些枯燥无味的事。后来,妖精三扑哧一声乐了。
妖精三是个有趣的人。不知因为什么人们都叫他妖精三,但我们一些孩子都叫他三叔。他四十多岁,矮小黑瘦,是个老光棍儿。按理说,他的生活里没什么快乐,但他却没乐找乐,整天快乐着。
有人问妖精三笑啥。妖精三说,今儿个是赵素云小侄女出阁,让他想起一个和结婚有关的乐子。大伙一听,都问什么乐子,让他说说。妖精三说,前几天我去了一趟赤峰,你们说,我在火车上碰到谁啦?他瞪着眼睛看着每一个人。王少泉站在地上,手里提着一个热酒的水吊子,装作生气的样子说,他妈这话问的,我们又没在跟前儿,谁知道你碰上谁了?
妖精三说,碰上我老丈人了。
大家一愣,你啥时候还有老丈人啦?
妖精三说,可不?我老丈人一见到我,抓着我的手就哭了,一边哭一边给我赔礼道歉,他说,孩子,我对不起你呀,我一辈子没结婚不要紧,把你给耽误啦!
大家怔了一会儿,然后,都忍不住扑哧扑哧地笑。
当时我也跟着乐了。不过我却是装乐。主要是当时的理解力不行,觉得没什么可笑的。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想起这段话来,才突然体会到妖精三是一个多么幽默的人。又总是想,一点儿文化没有的妖精三,他的智慧是哪儿来的呢?
一场婚宴,说说笑笑就结束了。我的头有点儿晕,还一剜一剜地疼。本来我一点儿酒不想喝,也不会喝。可妖精三不让,他说狗戴上帽子也算顶个人儿来的,不喝哪行?结果硬是灌了我两盅酒。到家后,我一头躺在了炕上。
醒来时天已经黑了。这是十二月初,白天总是显得十分短暂。父亲和母亲正在吃饭。母亲问我是不是喝醉了。父亲说,两盅酒就喝这样?你得练着点了。又说,往后,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就都是你的事了。
那你呢?
我这么大年纪了,你还指靠我一辈子?
人是慢慢变老的。可我发现父亲的“老”,却是在那极短暂的一瞬:昏黄的煤油灯下,父亲佝偻着身子坐在炕上,他两颊深陷,胡须稀疏,鬓角上的短发全白了……说起来,父亲算是老年得子。生我那年,他已经五十五岁。以前我就听村里人说过,别看老了老了还得个儿子,没用,得不上济……
父亲叹了一口气,用一种很老的样子说,我看不到你出人头地,但是你得给我学着出头露面了。
至此,父亲让我去坐席的用意,我全明白了。
那年我十三岁。
此前,我还从没有好奇地想过,我距一个真正的成人世界有多远?
母亲让我吃饭。桌子上摆着的还是棒子 粥。在七十年代初的辽西山村,不吃棒子 粥吃啥呢?但那天晚上我感觉一点儿不饿。母亲问我中午都吃了什么,是八个碟子还是八个碗儿。
我说,是四个碟子,四个碗儿。
母亲问,有三尖吗?
“三尖”就是把带着肉皮的猪肉切成三角块儿,在碗底下垫上三角形的土豆块儿,加好各种作料,放在锅里,蒸熟。一块入口,满嘴是油,能香你一个跟头。这是硬菜。
我说有。
母亲又问,有白片吗?
“白片”就是肥肉片,底下垫上白菜帮儿,也是硬菜。
我说有。
母亲没再吱声。
这时,父亲已经放下了粥碗。他用手抹了一下嘴角,自言自语地说,这个赵旺,席倒是还不赖呢。说着,父亲松弛的脖颈上喉咙滚动,像是悄悄地咽了一口唾沫……
甜草
小米囤儿来找我的时候,我刚吃早饭。小米囤儿的家就在我们家西院,每天早晨他都来找我。有时候我还没洗脸呢,他就来了。因此父亲动不动就瞪着眼睛说我,你早起一会儿不行?弄得我很狼狈,也很烦。我告诉小米囤儿,你走你的,老是找我干啥?可小米囤儿不走,一直等着我吃完饭,然后跟着我往三里地以外的学校走。我比小米囤儿大三岁,他一直叫我小哥儿。走着走着,小米囤儿就说,小哥儿,咱们跑吧?我说,要跑你不会跑?小米囤儿就不吭声地跟着我走。我迟到,他也迟到,就像我的影子。
我和小米囤儿在一个混合班里上学。我五年,他三年。小米囤儿长得瘦小,一直坐在教室第一排。从后面看过去,小脑袋,细脖颈儿,背诵课文时摇头晃脑的样子,就像一只光腚子小麻雀。小米囤儿上课很用功,学习好。老师不但常常表扬他,还把他的作业本在班里让其他同学传着看。不是五分,就是一个大大的“好!”当然,小米囤儿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有一次,一个女老师很生气,问他为啥把铅笔尖修得像针似的,字又写得像小虱子?小米囤儿站在那里,半天才嘟哝着说,省本儿……女老师看着小米囤儿,啥也没说,她扶着眼镜低下头去,然后摆摆手,就让小米囤儿坐下了。
小米囤儿家里很穷。但他爸爸却是我们村里唯一的“富农”,名字就叫余有富。为此村里还开过一次批斗会,斗过他。村里人本来没想要斗他,都是老邻旧居,再说了,每天早晨人家都是不言不语地到各家各户挑大粪,还不让村长记工分,很知道自我改造,挺老实的一个人,斗人家干啥?但是贫宣队员老仁不让。他说这不是老实不老实的事,关键是一点儿行动没有,上头不让。那就斗吧。那天晚上,村里的男女老少全去了。生产队里只有一间屋子,招不下,就在房檐下挂一盏马灯,所有的人都坐到地上。只是余有富反背着双手,弯着九十度的腰在前边撅着。
一片沉默中,妖精三站起来,提了提裤腰说,我先斗吧。人们都愣愣地看他。妖精三开始发言,他说解放前他爹给余有富他爹扛了半辈子活儿,还挨过余有富他爹的大耳刮子,到死了,连口棺材都买不起……说到这儿,妖精三说不下去了。老仁只好把话接过来,他说,揭发得好啊,贫下中农同志们,大家想一想,一个扛了半辈子活儿、还挨过耳刮子的人,为啥到死连一口棺材都买不起?这不是剥削是什么?这时妖精三在一边开口了,他说,不是!我爹他好抽大烟儿……人们一听,没乐死。
接下来,其他发言的人也是揭发不到点子上。有的说,过去家里一没有吃的,就得到余有富他们家去借;有的说,当时给余有富他们家耪地的时候,吃的不是黏糕就是豆包,还有粉条子炖猪肉,可劲儿造,那叫顶劲!越说越不像话,这还咋斗?老仁泄气地说,今天就斗到这儿吧,散会!
后来,村里人再没有批斗过余有富,倒是我们一些半大小子在放学的路上批斗过一次小米囤儿。事情是由李结实提出来的。李结实长得五大三粗,比我们高半头,平时他总是喜欢指挥我们干这干那。他掐着小米囤儿的脖子,说你这个富农羔子,不斗你一次,你就不老实!他让小米囤儿猫着腰站在一个土坎上,还在他的脖子上挂了两个书包。当时,我发现小米囤儿低着头翻着眼睛找我,眼神中的意思我明白,他希望我阻止。但是我却一声没吭。这是我的错。后来小米囤儿就哭了。小米囤儿爱哭,村里的一些大人喜欢逗他,哎,你们看,小米囤儿哭了,哭了……他就真的哭了;又说,你们看,小米囤儿笑了,笑了……小米囤儿也哭了。我们都知道小米囤儿爱哭,就没当回事儿。这时去大队开会的李栋过来了,他是队长,也是李结实他爸,脾气不好,好动手。他二话没说,上前给了李结实一个脖溜儿,还不解气,又在屁股上踹了一脚。吓得我们一溜烟全跑了。第二天,我以为小米囤儿不会跟我一起上学了。可是我刚吃饭,他就来找我了。天天如此。
这一次,小米囤儿却是来找我挖甜草的。
甜草,是辽西人的一种叫法。后来我才知道,它的学名是甘草。《现代汉语词典》里是这么注释的:甘草:多年生草本植物,茎有毛,花紫色,荚果褐色。根有甜味,可入药,又可做烟草、酱油等的香料。以前我不知道这些,大概村里人也不知道,它“又可做烟草、酱油等的香料”吧?
我们只知道甜草是一种药材,能卖钱。还知道它分两类:一种是须子,一种是草;草又根据粗细分成一二三等。须子六分钱一斤,一等草两毛一,二等草一毛七,三等草一毛三。不过,地区不同可能价格也不一样。听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还有人专门贩卖过甜草,在辽西一带收购,然后用大货车运到南方去卖,发了不小的财。我们那时候不行。收购甜草的地方只有乡里的供销社,还不是常收,一年只收那么一阵子。而且收着收着就叫停了,不要了,这才糟蹋人呢。没卖掉的甜草基本上就算瞎了,晒干了不收,挖坑埋上也不行,一场雨过后全烂了。没办法就只好扔在院子里,任凭鸡刨猪拱。有时候,大人孩子的也嚼上一小块儿,或泡水喝,很甜,却不知道是败火还是上火,一连几天滋的全是黄尿。
前几天,村里人突然得到一个消息,说供销社收甜草了。
这消息是妖精三去打煤油的时候带回来的。当时人们还不信,说妖精三是瞪着眼儿胡呲。第二天一早,有人到井台去挑水,发现妖精三扛着铁锹从他家房后的院墙豁口跨出去,直奔西梁,这才相信收甜草的事是真的了。随着这一消息的不胫而走,全村的人都兴奋起来了。在那种只挣“工分”的年月,平时除了能从鸡屁股里抠出几个小钱来,挖甜草,算是通过劳动能够直接兑换现钱的唯一方式。也就是说,人们可以用卖甜草的钱,稍稍宽裕一下拮据的生活。比如买盐,买煤油,给孩子添置一些上学的用品。奢侈一点儿的,还可以称上几斤肥肥的猪肉,炼一坛子荤油,能吃上半年……谁不兴奋呢。当时,正是少有的几天农闲时间,孩子们也是刚刚放了暑假,于是,村里的强壮男人和一些半大小子都相继从家里走出来,扛着铁锹上了西梁。
西梁离村子有五里多地,属于无人居住区,大小不一的山丘连绵起伏,一直滚到了天边。平时,除了附近村子里的牛倌、羊倌在这里相隔很远地骂一骂山头儿,荒凉空旷得连一只鸟都没有。现在就不同了。我们到了山上一看,到处都散落着像舞蹈一般挥锹劳作的身影。
在这些人里,年纪最大的是宝顺叔。他快六十岁了,耳朵还聋,跟他说话那叫费劲。一次我和小米囤儿在上学的路上碰到了他,他问你们两个干啥去?我喊着说,上学去!他侧着耳朵听了听,说,噢,我还以为你们上学去呢。
年龄最小的就是小米囤儿了。他十二岁,个子又瘦又小,站直了,才和铁锹把一般高。妖精三一见他就乐了,说个小鸡巴家伙,你挖得动吗,你爹呢?
小米囤儿说,去生产队干活儿去了。
干啥活儿?
倒粪……
倒什么粪?又没人斗他,这才是扯淡呢。妖精三泄气地说。
小米囤儿他爸可是挖甜草的一把好手。主要是他有力气,能翻窝子。他总是找一片长势强壮又密集的甜草秧,先在旁边开出一溜深槽,然后一排一排地往外扩展,说白了,就是与倒粪的方式差不多。不同的是,随着窝子越翻越大,最终那片甜草不管是须子还是草,都会被他一网打尽。这样几个窝子翻下来,横七竖八的甜草在地上扔了一大片。晚上回家的时候一看,谁也比不上他挖的甜草多。
此外,妖精三也是挖甜草的好手。说来奇怪,一看秧子,他就能判断出它有没有草。他还会找“地皮露”——瞅准了一棵甜草秧,往往是一锹下去,一个草疙瘩就露出来了,他却不急于把它挖出来,而是先“晾”着,然后去找下一棵。我们来到山上的时候,他在一个山坡上已经“晾”了十几棵这样的草。
我们就不行。一棵壮实的甜草秧,须子也很粗,却常常追到一人多深也不见草。也有的时候,刚挖几锹,看看须子挺细的,不像有草的样子,就放弃了。妖精三发现之后,歪着头看了看,用铁锹拨弄一下,然后一锹下去,就会挖出一个草疙瘩来。他嘿嘿一乐,看了没?这就叫捡落蛋儿!
三叔,你怎么知道它能见草呢?我们问他。
妖精三说,你们不知道吧?我能看地三尺!
又说,有草的秧子,我往那儿一站,它就会冲着我笑……
显然,这样的经验对我们毫无帮助。我们尝试了半天,发现所有的甜草秧都一样,你觉得它笑,它就笑,你觉得它没笑,它又不笑了。小米囤儿迷惑地问我,小哥儿,三叔是不是在骗我们?我装成很懂行的样子说,别听他的,该怎么挖就怎么挖。
小米囤儿从没有挖过甜草,也不会挖。开始他就靠在我的旁边挖,他不知道这是一种忌讳。挖甜草不能扎堆,得散开挖。你离别人太近,就会影响人家翻窝子。当然,除了小米囤儿他爸,很少有人翻窝子,因为翻窝子至少要多付出一倍以上的力气。我们都是选一棵挖一棵,打独坑儿。即使这样也不行。甜草这东西有个特点,它的须子会爬,也只有几根须子在地下爬到一起,突然结成一个疙瘩,疙瘩下面连接着的就是草了。如果两个人离得太近,挖着挖着,须子爬到了一起,那算谁的草呢?
小米囤儿是听话的。知道这些之后,他就跑到离我很远的地方,还问我他在那里挖行不行。在得到我的答复之后,小米囤儿便开始挖起来。远远看去,他的动作很兴奋,也有点儿心急,挖几锹,就会蹲下身去用手到坑子里抠一抠,看下面是不是见草了。一旦见了草,他就激动地冲着我喊,小哥儿,我这里见草啦!即使这样,一天下来,小米囤儿才挖了十多棵草,都是小拇指般粗细的末等草,其余全是须子。他学着别人的样子,把草和须子隔开,分成几小把,再捆成一大捆,插在铁锹把上,往肩上一扛,我们背着落日的余晖,下山。
到了村子,小米囤儿却不回家。我们家有一杆秤,他让我帮他称一下他的甜草。一称,草一斤多,须子是二斤半,还不及我的一半多。小米囤儿有些羞涩,接着却又很知足的样子,计算起他的草能卖多少钱,须子能卖多少钱,用这些钱能买几个算草本、几个田字格……算来算去,小米囤儿龇着小虎牙乐了,他说,小哥儿,明天咱们早点上山行吗?
这样的情形一连持续了两天。
第三天,小米囤儿就出事了。
应该说,那一天,小米囤儿的运气非常不错。上午他就已经创了自己的纪录,挖了十多棵草,而且最粗的两棵能够得上二等。小米囤儿很高兴,也很有成就感。中午的时候,我们把甜草埋起来,跟随着那些大人们到山脚下的一条深沟里吃饭。那里有阴凉,有大如碾盘的石头,还有一脉泉水沿着蜿蜒的沟底活活地流……因为西梁离村子很远,为了节约时间,我们每天都是带上饭在这里吃。饭都差不多,无非是棒面饼子,咸菜疙瘩。奇怪的是,同样的东西,在野外吃起来却很不一样,让人感觉到满沟堂子都弥漫着一种奇异的香味。因为天气炎热,吃饭时,所有的人都光着膀子,有的甚至把裤子也脱了,精赤条条地坐在石头上,像是一群原始的山民。
吃完了饭,我和小米囤儿躺在一块平展的大石头上,很快就睡着了。挖甜草是个累活儿,只要歇下来就觉得全身酸痛,再不想动弹。成年之后,每当白天特别劳累的时候,夜里,我总是梦见我在不停地挖着甜草。梦境里的甜草横七竖八,又粗又壮,我不停地挖着……直到累得两只手又酸又软,几乎握不住铁锹把了……倏然醒来,才知道自己做了一个梦。
小米囤儿也做了一个梦。
那天中午,我们被李结实喊起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扛着铁锹往沟上走去了。我和小米囤儿迷迷糊糊地爬起来,从后边跟上去。走出很远,小米囤儿才醒过神来,他告诉我,刚才他做了个梦,梦见他牵着他们家的毛驴,驮着很多很多的甜草到供销社去卖,一下子就卖了十块钱。
小米囤儿认真地问我,小哥儿,你说我能卖十块钱吗?
我说,肯定能!去年暑假,我卖了二十多块呢。
小米囤儿想了想说,那太好啦,我妈说,我挖甜草卖了钱,家里一分不要,全都给我……说完,他又想象着什么似的,目光里充满了憧憬。
回到山上,我们便分头去挖甜草。
没想到,两个小时不到,小米囤儿就倒栽葱死在了他挖的一个很深的甜草坑子里。事后人们断定,他肯定是扎进坑子里,想看看下边的须子见没见草,没退出来,憋死了。这是挖甜草的大忌。据宝顺叔讲,他小时候听大人们说过,有一个外村的孩子就是这么憋死的。没想到,一个如此遥远的悲剧,如今竟落到了小米囤儿的头上。为什么扎进去却没退出来?有的说小米囤儿挖的坑子太窄,也有的说小米囤儿年龄太小了,人又没什么劲儿……
那天下午异常燥热,八月的阳光无遮无拦地暴晒着山野,地上热气扑脸。我不时地放下铁锹,把双手插进刚刚挖出来的湿土里,才体会到一丝凉快。同时,我不停地喝水,还是觉得口渴。没一会儿,就把从沟底下灌的那瓶子泉水喝没了。
我想看看小米囤儿的瓶子里还有没有水。
小米囤儿在三十多米外的一个背坡上。我走过去,没看到小米囤儿的人影,只见一把铁锹插在一堆新土上。到了跟前一看,小米囤儿倒栽葱扎在甜草坑子里,外边只露着两条赤裸的小腿。像我一样,那天小米囤儿从上到下,只穿了一条裤衩和一双家做的硬帮儿布鞋。我叫了两声,没有动静。我以为他是故意的,便抓着他的两条小腿把他拖出来,小米囤儿满脑袋是土,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我大喊了一声不远处的宝顺叔,让他看看小米囤儿是怎么啦!耳聋的宝顺叔侧过头来木讷地看着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等他终于放下铁锹走过来一看,才突然大惊失色。然后,随着一阵大呼小叫,山上所有的人都围了过来……
我和李结实跑回村子的时候,小米囤儿他爸正和队长蹲在生产队的粪堆旁边抽烟。听说了小米囤儿的事之后,他们呼地从地上弹起来。两个五十多岁的人,在通往西梁的路上,竟把我和李结实远远地落在了后边。
小米囤儿是被妖精三等几个大人轮流背回去的。一路上,队长则像绑架似的一直挎着小米囤儿他爸的胳膊。
辽西丘陵,残阳如血。
那天傍晚,小米囤儿家的院子里,灌满了炸了锅似的哭声;同时,堆着小山一样的甜草……
时间埋去了岁月。
后来,我们村子也被埋掉了。
——两年前,那里成了一座大型露天煤矿的排土场(我在想,几百年、乃至上千年以后,或许会有人惊奇地发现,这里曾经是“古人类”居住过的遗址)。那年秋天,接到民政部门的通知后,我从北京回到了老家。村子里的房屋早已是残垣断壁。经过两天的认真勘察,选址,我把父母的坟墓迁到了一块新的“风水宝地”,心里却仍有一种说不出的怅然。这时,我又突然想起了什么,便从西梁来到北山。在一个山洼里,我发现小米囤儿的坟已经被人迁走,只剩下了半个很小的土堆。放眼过去,土堆上,以及周围的整个山坡都长满了甜草,密密麻麻,苍凉,茁壮,在秋风中沙沙作响。
我立在那里,往事回到眼前。耳边似乎又听到了“小哥儿、小哥儿……”的叫声——隔着三十多年的岁月,一声一声,把我的心叫疼。
偷瓜
吃过晚饭,我像往常一样到老井台上去。
老井台在村子中部的一个土坡下边,那是我们村唯一的一口水井。夏天的晚上,到老井台上去纳凉、聊天,是村里人的习惯,也是消磨时间的一种方式。试想,在一个没有电视机,也没有卡拉OK,甚至电灯都没有的地方,不到老井台上聊天还能去干什么呢!若干年后,我听过一个段子,说是一位很大的领导去西北山村访贫问苦,在和一个老汉谈话时,领导问老汉平时都搞些什么娱乐活动。老汉不懂什么叫娱乐,随行人员解释说,就是问你,吃完晚饭后干什么。老汉这才听明白,于是拉着长声说,噢——日婆姨!这虽是一则不雅的笑话,不过,在农村,特别是在那些偏远的山村,人们的业余生活单调、匮乏,却是一种普遍的事实。
我来到老井台的时候,妖精三正坐在那里抽烟。这个老光棍儿最是喜欢一年中这样的季节,在时间上,也总是比别人显得宽裕,每天晚上,他都是第一个到达井台边上的人。如果没有大人在场,他就会和我们一些半大小子逗上一会儿。有一次,他把我们叫在一起,审问我们夜里睡觉的时候都听过什么声音没有,比如喘气声啦,吭吭声啦什么的……我们都说,没有,没听见。只听见刮风了,下雨了,或者说,听见猫头鹰叫了,特别瘆人……妖精三听了,皱着眉头,好像挺失望的样子,也很生气,他说滚!都给我玩蛋去!
有时候,我们就真的滚了。
我们有我们的快乐方式,什么撞拐,打嘎儿,弹球,扇片子……多了去了。不过,这些都是适合于冬天里玩的游戏,而且是在白天。夏天的晚上,我们唯一可玩的游戏就是藏猫猫。一帮孩子,分成两伙,你藏我找。我们几乎藏遍了生产队的犄角旮旯,也找遍了村子里的沟沟岔岔……只是,时间一长,就有点儿腻了,不愿意玩了。
我们都不滚。
不滚,妖精三也没办法。沉闷了一会儿,倒是他自己憋不住了。
他说,我能用胳膊夹住蚊子,你们信不?
我们都摇着头,说不信。
这些个小兔崽子,我夹住的话,让你们吃了它!
说着,他把袖子往上一捋,把裸露的胳膊伸了出去。
山区的傍晚,是蚊子最多的时候。它们总是围着你的耳朵绕来绕去,唱着钻心的歌曲,烦得你,恨不得把自己的耳朵打掉了。没一会儿,我们就发现妖精三的胳膊上落了一只蚊子,又落了一只。妖精三也不说话,只是攥着拳头,暗暗用劲儿,把肌肉绷紧。然后,他告诉我们用手去扇他胳膊上的蚊子。奇怪的是,怎么扇,那两只蚊子只是颤动着翅膀,并不飞走。
我们这才相信,说夹住啦,夹住啦!
妖精三嘿嘿一乐,突然举起巴掌,“啪”的一声,又“啪”的一声。两只蚊子全扁了,一手血。
这时候,晚霞黯然消散。东山上,一轮磨盘似的月亮正悄悄地升起来。大人们已经陆续来到了老井台,开始他们每天一次的精神会餐——谈天说地。我们一些孩子也都坐在旁边,仔细听着。当然,如果没有人讲穆桂英,讲赵云,讲黄鼠狼推碾子之类,就没啥意思了。剩下的话题,无非是哪个村子里的谁谁没了,谁谁因为破坏军婚,被判了五年,要么,就是生产队里一些鸡零狗碎的事。这天晚上,人们说的是庄稼。什么北沟的玉米长得不赖,西坡的谷子不行,又招虫子了,等等。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都是一些我们不感兴趣的事。正听得无聊,妖精三说话了,他说,不说地的事我还忘了,今年老窑还种打瓜了呢!
是吗,在哪儿种的?
沟外的山坡上,好大一片了。
接着话题就转到打瓜上来了。
打瓜是西瓜的一个品种。不知道这东西是否普及到各地了,当年,辽西一带却是常种。它比西瓜小,吃起来也不像西瓜那么甜,甚至有点儿酸不叽的,白瓤,子多,种这种瓜主要是为了收瓜子。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生产队里曾种过一次。开园后,全村出动,男女老少跑到瓜地,一天一个饱,可劲儿吃,不要钱,只要把瓜子留在生产队的草笸箩里就行。
现在一说起打瓜来,人们似乎都很怀念那样的日子。这时,妖精三站起来,从井里摇上一斗子凉水,蹲下身子咕咚咕咚喝了一气,然后用手背抹着嘴说,他妈的,怎么一说到打瓜,我还觉得渴了呢。
队长说,你馋打瓜了呗。
队长是个镇脸子人。他从来不笑,说话不说话,都是一种很有权威的样子。
这时,王少泉乐了,又想起什么似的,说,哎,妖精三,我考考你。
妖精三问,考啥?说!
王少泉说,有西瓜,有东(冬)瓜,也有南瓜,你说为啥没有北瓜?
妖精三顿了一下,我操,这还真是个问题呢。
王少泉说,咋样?别看你是个妖精,也有不知道的事吧?
妖精三乐了,问王少泉是怎么回事。
王少泉慢吞吞地说,这话说起来可长了。
我正想把事情听个明白,旁边的李结实站了起来,要拉着我走。我问他干啥去,他说藏猫猫去。我不想走,尤其是不愿意跟他藏猫猫,这家伙满脑袋坏点子。有一次,他把自己扣在生产队的草笸箩里,让我们找了半宿。还有一次,他告诉我们,找不到他就不能散伙。说完,他就溜回家里睡觉去了。要不是半夜的时候有几个大人出来喊自家的孩子回去,就是寻到天亮,我们也找不到他。心太硬了。
见我迟疑着不动,李结实一边冲我甩头,一边给我使眼色,暗示什么。经不住他的怂恿,我还是和他离开了老井台。同时,其他在场的孩子也都跟在了我们后边。我们拐过一个墙角,李结实才小声告诉我们,说不藏猫猫了,今天要搞一次特别行动。
我们问他什么行动?
李结实说,到老窑偷瓜去!
听了这话,我们都觉得很新鲜,很好玩,心里立刻泛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刺激。我们都很亢奋,说,去就去!但说完之后,我又突然有些担心,万一被抓住怎么办?这时,王宝德扭扭捏捏地说,他妈让他早点回家呢,他不去……显然是找借口,推脱。李结实不耐烦地看着王宝德,他说我越看你咋还越像个娘儿们呢?不去拉倒,赶紧回家吃奶去,滚!
本来,我也想象王宝德那样,打退堂鼓,但又怕像王宝德那样挨骂,就没有吱声。王宝德走后,李结实看着小民,告诉他别去了。其他人也愿意让小民别去,他比我们小两岁,都觉得他是个累赘。可小民不干,还挺拗,他说,瓜又不是你们家的,我偏去!同时他还威胁说,要是不让他去,他就回去告诉大人。没办法,李结实只好让他跟着。
老窑村在我们村东面。根据妖精三的说法,那块瓜地离我们村可能有三里多地,中间还隔着一条大沟。路线倒是很熟悉,平时上集赶店的,我们总要从那个山坡下面经过。于是我们六个孩子就悄悄地上路了。
俗话说,做贼心虚。行动刚开始,我就进入了一种心情紧张的状态。其他的人大概也一样,一路上,我们谁也不说话。山区的夜,比平时还要寂静。傍晚时在东山角上那个像磨盘似的月亮已经升得很高,天空深邃浩渺。如水的月光下,山野里到处都呈现着模糊而奇异的形象。沟边的树毛子,山坡上的坟包,甚至一些平常的沟沟坎坎,所有的东西都与它们原来的形状不一样,神秘莫测,有的像狗,有的像牛,走着走着,又突然发现前面的山沟里站着一个很高的黑影,戴着草帽,弯着很细的腰……许不是大人们说的“魔”呀?走近一看,才知道啥也不是,它只是一个被山洪冲出来的水沟……
我们像梦游似的,翻沟越坎,一路默行。
后来,在一块高粱地旁边,我们终于找到了那片开阔的瓜地。我们并没有像饿虎扑食那样急于下手,而是躲进高粱地,哈着腰,仔细侦察瓜地里的情况。
夜很静,一点儿风丝儿都没有。天空中的月亮像一面小镜子似的照着瓜地,真好,真白。如果不是后来出了事,可以说,那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美的月亮了。
在确定没有瓜窝铺、也没有其他可以让人栖身的疑点之后,我们才按着李结实的布置,开始行动。因为是临时动议,谁都没带什么家伙,我们就学着李结实的样子,把上衣的下摆扎进裤腰,以便摘了瓜就装进怀里。然后,我们散开队形,一人一条垄,顺着垄沟往瓜地里爬……
唧唧唧,四野里一片虫声。
草叶上,以及瓜秧上,都挂着点点滴滴的露珠。
我双膝跪地,立刻闻到一种泥土的清香……
遗憾的是,瓜不大。也就是拳头一般大小,可能刚刚结子儿,肯定还没有开瓤,总之,吃起来也是生瓜蛋。可既然这么远跑来了,总不能空着手回去,是不是?那就整吧。拣大个儿的摸吧。
刚摸到三个,也可能是五个,记不清了。正往前爬,一抬头,我突然发现前边有一片坟地。还没来得及害怕,却眼瞅着在一个坟包后面像幽灵似的立起两个人影,与此同时,一声詈骂在寂静的夜里如雷炸响:
王八蛋操的!干什么呢?
…………
说实话,除了我们几个在场的孩子,我不知道还有谁曾遇到过如此的惊吓。当时,我只觉得头发都立起来了。在一种猝不及防的恐惧推动下,我从地上弹起来就跑。我一边跑,一边抽出衣摆,让怀里的瓜蛋噼里啪啦掉到地上……
可以想象,事情来得如此突然,提前又没做什么预案,结果,我们个个如鼠逃窜,慌不择路。有的扎进了高粱地;有的沿着一片谷地边上跑;我则斜刺里顺坡而下。糟糕的是,下边竟是学大寨时修的一坡梯田,每一条坝埂下面都是两米深的坎子,我一连跳下好几个,没把肠子蹾断了真是万幸。
梯田里种的是荞麦。七月的荞麦花,在月光下开出白生生的希望,真是美极了。可当时,我只觉得心在狂跳,脑子里一片空白……就在我蹚着雪白的荞麦花没命奔跑的时候,山坡上突然传来一阵揪心的哭叫声……
第二天下午,我们参与偷瓜的六个孩子,一个不落地被家长押到了生产队的院子里。头天晚上,年龄最小的小民被抓住之后,经不住两个看瓜人揪着耳朵一顿吓唬,最终做了叛徒——他把我们每个家长的名字都供了出去。第二天上午,老窑村的队长带着两个看瓜的人来到我们村里(不知道那时候的人咋都那么认真),他们找到队长,理直气壮地要求赔钱。作为一种很少遇到的“跨村事件”,这可把我们村的队长难住了。那时候还不时兴请客,要是现在,摆上一桌酒席,你兄我弟地一造,别说是偷了几个青瓜蛋子,就是犯了再大的刑事案件,也可以通融,说不定,最后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问题是,那时候还不时兴这个,也没那个条件。别说是酒席,就是一杯茶水也端不上去。队长只能卷上一支旱烟,用舌头舐一下,粘好,递给老窑村的队长,让人家“抽着”……就这样,整个上午,不知道他费了多少唇舌,说了多少好话,总算是把事情摆平了。
接下来,就是教育那几个祸头!
不过,这样的事情就好办多了。那天下午,天气很热,生产队院子里的空气异常沉闷。李结实我们站成一排,低着头,等着大人发话。小个子李栋,也就是队长,蹲在生产队院子里的一只碌碡上,像是一只老鹰。他抽完了一支烟,又问了几句事情的经过,然后从碌碡上下来,率先垂范地给了李结实一个耳光。
就这么简单。
接着,其他孩子也都顺理成章地挨了自己父亲的耳光,并受到了同样的斥问:说!你还敢不敢去偷了?孩子们都嘟哝说,不敢了,再也不敢了。谁都没有哭。我发现,李结实还扭过头去,偷着笑。那时候农村的孩子挨打是常事。习惯了。
再接着,就应该轮到我了。很意外,我父亲却没打我的耳光。也可能是觉得像其他人那么做,就有点千篇一律,俗了。他只是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眼神盯了我一会儿,恨恨地说,等着,回家再说!
那天回家以后,父亲是怎么“教育”我的,以及都说了些什么,我已经全忘了。倒是前一天夜里在瓜地里的那一场惊吓,却让我刻骨铭心。
有人说,儿童时代留给人的回忆是甜蜜的。
其实,那得看回忆什么样的事了。
——如水的月光下,几座坟包后边突然立起两个人影……无论如何,这样的回忆一点儿都不甜蜜。甚至,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每当看见月亮,我就会生出一种莫名的担心,总觉得,越是美妙的月光下的一切都充满了不怀好意,或者说是危机四伏;而那一声如雷炸响的詈骂,则说不定在哪一时刻就会让我突然想起……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已经成为我一生的警钟。
前年春天,我去南方参加一个会。在飞机上,一位年轻的女记者曾为我看过一次手相。她告诉我说,我要走桃花运了。
我说,是吗?
她肯定地说,没错。而且……
我问她“而且”什么。
她说,而且……还是不会影响到你家庭的那种……
我在心里顿了一下。没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只是傻呵呵地乐。
女记者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又继续看我的手。然后她沉吟着说,不过呢,你这个人好像太理性了,对不对?
我笑着说,也不是,主要是胆子小。
她说,为什么?
我说,我被人吓破过胆……
她歪着头,妩媚而调皮地看着我,是偷情?
我说,不是,是偷瓜。
原刊责编 王 霆
【作者简介】荆永鸣,男,1958年生,内蒙古赤峰人。著有散文集《心灵之约》,中短篇小说五十余万字。短篇小说《外地人》获2001年—2002年小说选刊奖。现在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公司就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