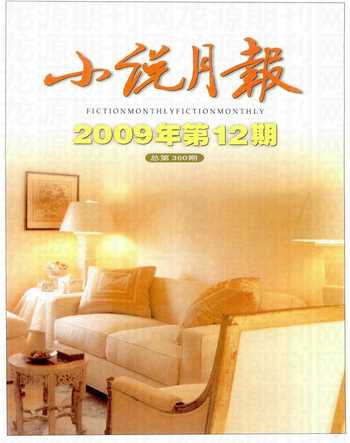重阳
听到敲门声时,我正在和眼皮较量。小时候常听娘说世界上最重的东西就是眼皮了,今天再一次得到验证。
六月被娘叫醒时,还拖着一个长长的梦的尾巴。六月拖着那个梦的尾巴像梦一样枝枝蔓蔓地穿着衣服。五月看着六月拖着梦的尾巴穿衣服的样子,忍不住在那胖嘟嘟的脸蛋上拍了一巴掌。六月就顺势倒在五月的怀里。五月喜欢六月倒在自己怀里的感觉,却不愿意承认这种喜欢,于是身子一闪,让六月滚在炕上,压得梦的尾巴咯吧一声。
这个样子,还想抢头山?
娘的话像一瓢凉水泼下来,让六月一下子醒透了。
几下子穿好衣服,跳到地下,奔到院里。
熟睡中的村子像一块墨,黑在寂静中。
等着我们的是一队骆驼,无比安顺地卧着,就像佛陀身边的十八罗汉。没有一点儿生分,没有一点儿挑肥拣瘦,也没有问大家为何方人氏,静静地等着我们骑稳,就霍然起立,迈开大步,向着沙漠进发,一派绅士风度。
爹把五月和六月放在马驹背上,六月在前,五月在后。天有些冷,来自五月怀抱的温暖一阵阵钻进六月的骨头里。这是一种不同于被窝的温暖。姐姐的小肚子贴在他的屁股上腰上;姐姐的胸怀贴在他的后背上。马驹一摇一晃,来自姐姐的这种温暖就一摇一晃。恍惚间,他觉得整个世界都在这一摇一晃里。
就在这时,他发现他把爹给忽略了。爹就走在他身旁,牵着马驹的缰绳,可他把爹给忽略了,他怎么就把爹给忽略了呢?看了一眼爹,爹像一只船一样浮在黑暗里;爹只不过是黑暗里的一个动静;看不见爹的眉眼,却能看见爹的呼吸;恍惚间,六月觉得爹的呼吸就是夜的呼吸。
骑在骆驼上,在茫茫黑夜中行走,其实是一种行走的睡眠。没有路,骆驼本身就是路。船一样在沙漠中颠簸,在如海的夜色中颠簸,有一种颠簸的安稳,更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六月发现,是黑暗加强了姐给他的温暖,水果糖一样的温暖。他从未有过的喜欢这种黑暗,他甚至不希望光明早些到来,甚至不喜欢高高山早些到来。六月觉得,有爹陪着的黑暗是一种安全。平时在被窝里,半夜被尿憋醒,他常常发现自己在五月姐的怀里。爹和娘都上地去了,炕上只有他和五月姐。他就腾地跳到地下去,解决了问题,然后重新钻进被窝,赖在五月姐的怀里。五月姐的怀抱不同于爹的怀抱,也不同于娘的怀抱。爹的怀抱硬硬的,有一股书的味道;娘的怀抱软软的,有一种墨的味道。姐的怀抱不同于爹的,也不同于娘的,既软又硬,既暄又瓷,还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怎么说呢,没法说。六月常常在这种没法说的味道里再次进入梦乡。
骆驼颠簸了一下,开始爬坡。驼峰顶在我的小腹上,让小腹害羞。我不知道骆驼是否感觉到小腹的害羞。
六月第一次体会到摇摇晃晃给他带来的快乐。他才明白为啥新媳妇要骑着马驹到婆家,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让六月快乐的除过摇摇晃晃,还有靠,一种来自摇摇晃晃背面的靠。
一次,六月从梦里醒来,发现那个“醒”靠在一个既凉又热的地方。悄悄地揭开被子,原来是一个屁股蛋儿。
嗨嗨,美女蛇。
冷不防就过来一个巴掌。
打你爹。
又一巴掌。
打你爷。
奸巧语,污秽词……
市井气,切戒之。六月一边抢过五月的话头,一边在自己嘴上扇了几下。
不想就在这时,美女蛇突然翻转过来,把他箍在怀里,直箍得他气都喘不过来。
再箍一阵就把人给箍死了。
有那么悬吗?
真的,我都能闻到那个死了。
有那么悬吗?
我都能看到那个死了。
有那么悬吗?
我都能听到死的脚步了。
有那么悬吗?
我都能摸到死的沿沿儿了。
六月乘五月不备,一把把五月箍在怀里,憋足劲地箍。
就真把五月给箍死了。
天色仍如黑漆,让人觉得大家就在一个漆桶里晃荡。回头看队伍,视线里却只有一串蹄声。更加衬托了夜的寂静。那是一种残余的蹄声,一种被沙层吃残的蹄声。
跟着蹄声,我就进去了,渐渐地进去了,进到一个只有出来时才能意识到的世界。
突然想到了一个词:涅槃。
涅槃也可以是摇摇晃晃的吗?
五月活过来时,六月正在哭。
六月的眼泪急刹车,把五月给惹笑了。
美女蛇原来在骗人!
五月就伸出手,无比深情地把六月脸上的泪水擦掉了。
假如姐真死了,有这么一个人牵心,姐也值了。
假如你真死了,我才不哭呢,天这么旱,留下眼泪还能润肠子里。
润你的鸡呢,说着在他的鸡上抓了一下。
润你的个鸡呢,也在她的鸡上抓了一下。
这一抓就吓了六月一跳,姐的鸡窝里怎么没有鸡呢?
好不容易等娘回来。问娘。回答他的却是娘的一叩。
把中指弯成一个弓,用弓背在额头上不轻不重地碰一下,虽然不怎么用劲,却特别地痛,古时私塾先生常用,不想娘也继承了下来。
他委屈地摸着烫烫的额头,想,又是哪儿犯错了呢?不想娘却笑了,怎么突然想到这个问题的?
六月就叉开双腿,挺了肚皮,说,我有,姐没有,爹有,你没有。
六月这样给娘说时,似乎已经明白了一些什么,但又无法究竟。
只见娘像一盆水泼在地上,半天,才从地面上泛出来一个声音,等你长大就明白了。
又是长大就明白了,难道我现在还不够大吗?
现在,我算是长大了吧?如果说我是为了明白才拼命地长大,那么当我真的长大时,恰把当初的那个问题给忘了。一个拼命赶路的人,忘了自己因何出发。这不,一晃,告别马鞍已经三十多年,日子就像白驹过隙,但我却找不到驹上的那个鞍子,找不到来自鞍子的安稳,也找不到驹蹄落在黄土路上的清脆。日子浑浊得像一团泥浆。多亏了这无所事事的敦煌之夜,这为了行走而行走的行走。原来,这回到童年的小径就藏在无所事事里。白天就不行,白天的风景太多,主人的安排也太多,忙不过来,而一个作家的坏毛病是要在任何地方都想发现大义。当我在风里寻找内容时,我发现我已经和风错过;当我在雨里寻找意义时,我发现我已经和雨擦肩;还有手里的相机,也是最最可恶的东西;同样的人的坏毛病,总想把一切留下来,或者装在什么里面,带回家;为此,我们又和这些要留的东西错过。我们总是不愿意进入当下,我们总是想着未来,一个人就是这样错过风景的。
感谢夜,让我的相机失效;感谢风,让我的眼睛失效。
我吃惊地发现,就在这一刻,那个真正的“看”发生了。
风景随之到来。
六月喜欢闭着眼睛看太阳,也喜欢闭着眼睛看天空,还喜欢闭着眼睛看糖。姑夫从南里给他们带来了两粒水果糖,他和姐一人一粒。他们当然没敢轻易动手。他们在商量一个可以把糖品到家的最佳方案。
最后姐说,我们要闭住气,闭上眼睛,隔着糖纸拿着糖的一端,把糖的另一端轻轻地轻轻地点在舌尖上,让那一点慢慢放大,放大,再放大,大到不能再大,然后再点一次,这样就会让糖永远活着。
开始。开始。开始。
品。品。品。
啊。啊。啊。
……
就有一缕芬芳弥漫开来,那是莫高窟卧佛的眼神。
五月问六月把甜放了多大。六月说像院子这么大。五月说还是小了。六月问五月放了多大。五月说像天空那么大。六月就惭愧得不行。可是六月不信,六月说我怎么没有看见那个天空?五月说你肯定不会看到天空。六月问为什么。五月说因为你在品的时候睁着眼睛。
难道只有闭着眼睛才能看到天空?
当然,这眼睛一睁,舌头就失灵了,舌头一失灵,当然看不到天空。
你是说这天空是舌头看见的?
五月惊了一下,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六月的问题。说是么,舌头上又没有长眼睛;说不是么,又觉得分明不是眼睛看到的,那到底是哪个看到的?
好在六月没有继续追问,他接着说,这眼睛原来是个坏东西,里通外国的坏东西。
是啊,要不爹为啥说孔老夫子教导我们非礼勿视呢。
难怪娘在品爹的时候要闭着眼睛。
五月眼仁鼓得像青蛙,你说啥?
那天,我在堡墙上睡着了。醒来,听见屋里有人说话,从气孔往里一看,爹正在吃娘呢,娘问啥味道,爹说水果糖的味道。娘说这话时,就闲着眼睛,原来是非礼勿视呢。
那才不是非礼勿视呢。
是啥?
肯定是为了把爹放大,放到天空那么大。
可是爹还动手呢,爹不是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吗?
爹怎么动手了,他打娘?
不是,爹的手从娘的下襟伸进去……
不想五月一把把六月的嘴捂上了,孔老夫子不让你害烂眼病才怪呢。
为啥?
这才是真正的非礼勿视呢。
姑姑——油——
一声鸡鸣把我从比天空还大的水果糖里带出来。睁眼一看,天比刚才还要黑。真佩服带驼人,他们可以不打灯在如此漆黑的夜色中行走。也许正因为没有路,大家才可以闭上眼睛行进。一条没有路的路,那就是沙漠。可是,如果没有路,这些沙子又是从哪里过来的?
姑姑——油——既然有鸡鸣,肯定附近有村庄。果然,从驼峰传来和在沙漠上行走不一样的地面传感,说明骆驼上路了。
回忆小时候躺在热炕上听雄鸡报晓的情景,是我生命中的最大享受之一。多年以后,学了现代汉语规范用词,我也不愿意把这个象声词写成“咕咕——呦——”,而坚持写为“姑姑——油——”我觉得“姑姑——油——”里有一种希望,一种提醒,对幸福的提醒,就像是一个无比可爱的侄女无数次地给姑姑说,看,油,而且是故乡最好吃的胡麻油。五月姐说,还可以是煤油,好多好多的煤油,我们就可以点好多好多的灯盏,让大年亮透,让正月十五亮透,让高高山亮透……
咩——不防,羊羔软软地叫了一声,把人的心提了一下。那叫声穿过夜色,既可爱又可怜。五月让爹把羊羔给他抱着,爹说不行,上山时马驹颠脚六月后仰会压着它的。六月说那给他抱。爹说,你把灯笼打好就行。六月说,那我下来走上,让我姐抱着羊。爹说地上露水很重。六月说你的鞋早湿了吧?爹说,爹穿的是旧鞋,湿了没关系。六月就下意识地翘了翘自己的新鞋,觉得那双脚板也变成了新的,觉得被脚板划过的夜色也变成了新的。
这人为啥这么喜新厌旧呢?
可是,这新鞋迟早得落在地上啊。
还是旧的好,只有用旧的东西才不怕用旧。
咩——为啥羊羔不穿鞋?
羊羔想吃奶了,姐说。
羊羔知道今天是重阳吗?
人家当然知道的,要不然怎么叫重阳呢。
重阳是九月九的意思,傻瓜。
谁不知道。
知道怎么胡说呢?
谁胡说了,重阳再加一个羊,就是三个羊。
哈哈,那叫“三羊开泰”,傻瓜。
六月能够这么巧妙地把爹的春联用在这里,让五月既佩服又嫉妒。
五月不甘示弱,羊羔本来就是“高”,再加两个,就变成三个“高”,比高高山还高。
那也没有人的嘴高,人们嘴一张,就把这个“高”给吃了。
娘说凡是吃羊羔的人都要倒大霉的。
为啥?
因为“三羊开泰”。
这次轮到六月佩服了。
娘说,那些吃羊羔的人,上再多的高高山也是没有用的。
为啥?
因为重阳神最讨厌吃奶嘴的人。
我的老家宁夏西吉县将台堡一带,把还在吃奶的孩子包括幼畜叫“奶嘴”。说起“奶嘴”,我想起一次在公园里听两位女同志聊天。一位说她有一年到乡下支教,住在一个老乡家里,老乡为了感谢她们,硬要给她们杀羊。当老乡从羊圈抱了一个羊羔往外走时,乳羊像是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似的发疯地阻拦;可是羊羔终究被老乡带离羊圈,只见被关在栏内的乳羊拼命地撞击圈栏。当羊羔在老乡刀下的叫声渐渐弱下去的时候,那个乳羊停止了冲撞,呆呆地站在那里,头上流着血,嘴里喘着气,脸上的表情让人不敢也不忍去看,她说那是她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一种表情,比绝望还绝望,比无奈还无奈,比悲伤还悲伤。她说她当时从未有过地想念孩子,恨不得立即回到城里,回到孩子的身边。当羊羔肉端上来时,她觉得那不再是一盘羊羔肉,而是一个母亲的眼神,让她不寒而栗,更不要说动筷子了。另一位说,不吃是对的,科学家说当动物被宰杀时会把所有的仇恨都转化为毒素注入到肉中,人吃肉其实是吃毒,是往身体里埋定时炸弹,你看牛蹄疫是吃出来的吧,禽流感是吃出来的吧,“非典”是吃出来的吧。同样是两个素食主义者,境界却是天壤之别。后者是出于保护自己才茹素,前者则是出于善良,出于慈悲,出于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出于“忠恕”,出于“夫子之道”。
小时候常听爹讲一个词“共体”,有些习以为常,及至年长,才发现这个词的了不起。既然大家都是造化的孩子,那么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既然大家都是兄弟姐妹,那么当我们路过草坪的时候,就不应该从小草的身上踩过去;既然大家都是兄弟姐妹,那么我们在看到可爱的羊羔时,就不应把它看作盘中餐;既然大家都是兄弟姐妹,那么我们引弓搭箭时,就要想到“母在巢中盼子归”。
六月接着说,如果娘来就好了,她还可以把小鸡抱了来,把小猫抱了来,让它们也重阳一回。
那还有小狗呢,还有燕子呢,还有鸽子呢。
娘说有羊羔代表就行了。
爹说话了,过去就是全家齐上呢,那时咱们还人全势全,上山时你爷爷总指挥,爹领人,你二叔领牛,三叔领羊,四叔领鸡,秩序得像队伍一样。
后来为啥不人全势全了呢?
后来他们就进城了。
为啥进城呢?
因为城里是花花世界。
花花世界有多好?
在爹看来没多好。
没多好他们为啥还要去?
将来你们去了就明白了。
骆驼从村子穿过时,让人有种不真实的感觉,或者说是荒谬的感觉,尽管强烈的人间气息扑面而来,一种让人心乱的人间气息。
好在很快村子就不见了,骆驼开始持续地爬坡。
一行人就从漆黑的海底渐渐地浮到水面。
沙峰上隐约有灯火,那是先行到达的筹备组。
突然,前面的安妮叫了一声。几乎在同时,带驼员打过来一个手电,把夜捅了一个光明的洞。安妮的那个“哎哟”就落在那个洞上。安妮的红色夹克像炉塘里沉睡的火传过来一点点温暖,让人觉得她的那个“哎哟”就像一块睡眼惺忪的炭。
顺着电光看去,原来是一条蜥蜴惊扰了骆驼,或者说是骆驼为了躲过蜥蜴,才不得不给主人一场虚惊。骆驼一副对不起的神情,认真谦退,虚怀若谷,好像在说,为了蜥蜴先生,本大人不得不委屈贵小姐一下,却又隐忍,让人想起古中国那些训练有素的外交大臣。
六月要骑在姐后面,爹坚持不让,什么原因呢?
爹说让你坐在前面打灯笼啊。六月说我姐坐在前面也可以打灯笼啊。爹说重阳节的灯笼要少爷打呢。六月的腰杆里就蹿上一种东西,旗杆一样呼呼呼地拔向天空。一种来自旗杆的优越感烧着他的心,也烧着他的后背。姐像是感觉到了这种烧,把胸怀挪开,又让六月失落。六月说,爹现在把灯点着吧。爹说现在还是大路,爹能看得见,等小路上再点。六月换了一个手提了灯笼,虽然灯笼还在睡觉,但他却能从中看到一种亮,却不分明。没有点着的灯笼还是灯笼吗?
但六月很快就忘了这个问题,因为六月想到了娘,娘为什么不来呢?
爹说,你娘在山底等着接你的锅盔呢。
六月说,我们家的锅盔最大最圆了,肯定能够第一个滚到娘怀里。
五月摸了摸背上的锅盔,觉得把这么大的一个白面锅盔从山上滚下去,多可惜啊。可是她立即又发现自己的这个想法小气了,就表态似的说,从高高山上滚下的锅盔已经不是锅盔了,是吉祥如意……
六月拦截:是五谷丰登,是风调雨顺……是国泰民安!
六月和五月傻眼了,他们居然同时“国泰民安”。
六月嗨嗨。五月嗨嗨。
骆驼往沙峰攀登时,我看到了倒扣在头顶的海,和闪烁在海里的星群。更为准确些说,是一条河。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词“恒河沙”,一条河是一粒沙,一粒沙是一条河,那么我们现在就在无数条河上浮游,这胯下的骆驼就是舟了。如此说来,我们是在无数条河上?而且同时在无数条河上?嗨嗨你在错解如来意,错解如来意是要被罚做狐狸的。但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记得小时候问父亲世界有多大。父亲如此给我们打比方:
佛国有河名恒河,
恒河之沙不可数;
恒河一沙是一河,
沙沙为河不可数;
河河之沙不可数,
沙沙河河不可数……
这样不停地想下去,直到你想不动,世界就这么大。
五月和六月就比赛着想。突然,五月两手捂了脑瓜说,我的头怎么没有了。六月就在五月的脑门上一考儿。
老家把中指借大拇指发力弹人叫“考儿”。
五月没有感觉。六月就害怕起来。莫非五月的头真没有了?可是他分明看见在她脖子上啊。又一考,就把五月考哭了。
可是这次五月没有还击他,而是十分认真地哭。
哭了一会儿,扑哧一声笑了。
神经病,六月说。
我现在能感觉到我的头还在。口气是庆幸的,表情是劫后余生的,有惊无险的。
六月的眼睛就直了,莫非姐的头刚才真没了?
你呢,难道你的头一直在?
六月说,我的头倒是一直在,可是上面挂满了恒河,比头发还多,哗里哗啦地响呢。
娘不是说上古时的人把头发叫三千烦恼丝吗?你的头上倒有三千烦恼河。
六月的眼睛又直了,怎么今天奇迹都发生在姐的身上?怎么今天好想法都出现在姐的脑瓜里?莫非姐的头不是肉头不成?
相处的时间一长,觉得一头金发长在美国人的头上真是好看,再配上那种宝玉一样的眼仁儿。再想那些如此效仿的中国人,就觉得俗不可耐了。黑发之于中国人,金发之于美国人,天经地义,可是现在的人们却要地经天义。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中国到美国
而是我现在坐在你对面
你却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美国到中国
而是我现在坐在你对面
你却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
这是我给写作组交的第一份作业,我不知道翻译是如何给美国朋友翻译的,但我从美国朋友的眼神里,看到了他们的“懂”,又看到了他们的“不懂”。真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难怪老祖先要不立文字以心传心。可是以心传心,又如何是我等五谷俗人使得。因此,世界就变成一个误会的世界。如果我是孙悟空就好了,就可以钻进他们的脑瓜里看个明白,看看他们现在在想什么;就可以钻到他们的心里说个明白,让他们不打折扣地看到我在想什么。
一天晚上,写完作业,已是子夜;楼上静静的,想必大家都已进入梦乡;就穿了外套,拿了钥匙,一个人悄悄地登上楼顶。不想休和爱德华正坐在烛光下对饮,不由得一阵感动。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原想这只是中国人的浪漫,不想现在却成了美国人的写照。一时间有种凑上去加入到他们中间的冲动,可转念一想,自己是无法加入到他们行列中间的,因为门被封着,那个可恶的语言之门。
只好退到一个他们看不见的角落,打量沉睡的敦煌;目光就穿越鸣沙,月光一样落在月牙泉上;此刻,倘若独对月牙泉,那该是一种怎样的享受?
相看两不厌,只有月牙泉。
如此想时,已打扰了月牙泉了。
还是回家睡觉吧。不,是回屋睡觉。不,是回家睡觉。回。
下楼时,不禁又回头看了一眼“美国”,心想,他们现在在聊些什么呢?
躺在床上,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居然不是莫高窟,不是鸣沙山,不是月牙泉,而是美国,他俩坐在那里,一直在说什么呢,他们总不会一直坐到天亮吧?
不甘心,第二晚的同一时刻,再一次登上楼顶,嗨,还是他们俩。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莫非要把这晾台坐穿不成?莫非要把这鸣沙之月全部揽入你们的眼底不成?话是这么说,但从心底升起的,却是感动。几天来,看着美国朋友孩童一样用筷子把菜几经周折夹在嘴里,有种感同身受的成就感,并无端地为此感动,因此常常忘了用餐,追随着他们手中的筷子。
这时,我仿佛能够看到,他们的脑瓜里也有无数的筷子,在如此夹着翻译递给他们的面点、菜蔬、饮料。小时候,爹就是这样教自己蹒跚学步;稍大些,爹就是这样教自己鹦鹉学舌。那天晚上,爹就让他用平时背的古诗描述一下骑在马驹背上的感觉。
六月脱口而出,大姑娘骑驴,恰如其分。住嘴!六月没有想到,爹的口气像生铁一样。六月还为自己得意呢,以为自己说了一句再贴切不过、再水平不过的话呢。这是双全哥常说的一句话。双全哥是木匠,他在合榫时常常这样说。当时他并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只是觉得好玩。今天,虽然五月姐不是大姑娘,但也是姑娘,虽然不是驴是马驹,但总也是骑。可是爹为什么要阻止他呢?每当平时自己把背来的句子用在事情上,爹总要夸奖的,可是今天爹为什么这么“生铁”呢?
现在,我的脑海里再次闪过这句话。队伍中有许多大姑娘,当“大姑娘骑驴”在脑海里升起时,我一巴掌把下半句打掉了,反倒觉得自己的这一巴掌恰如其分。一次,爹带我们去看马戏,当一个人上演走钢丝时,爹说,人的一生,就像走钢丝,左一下右一下都会葬身深渊。那时不大懂得。及至成年,成为一个半吊子作家,才发现带着文字行走也是走钢丝。我们太容易滑向惯性,写着写着就被惯性带跑了,不知不觉就开始脱,就开始上床,就开始下流,就开始低级趣味……那时的文字就像是一个从山上滚下的磨盘,要想改变它的方向,非有神力不可。那是一种扭转的力量,一个作家的腕力就是在这时练成的。现在想来,我们就是父亲手里的文字,年年岁岁,时时处处,他在带我们走钢丝,处心积虑。
那天和美国作家交流,翻译刘雪岚老师选择的是我发在《文艺报》上的一篇短文《提防不洁的文字和长命百岁的文学》:
茶杯刚喝完就洗,也许不需要动手,在清水中冲一下就可以了,但是过上一会儿,就需要茶巾了;过上一天,茶巾都没办法了。
这让我蓦然想到时间,结在杯子上的,不是茶垢,而是时间,一种非当下的时间。
由此想到古人为什么强调要回到当下,因为回到当下是对时间的最大礼敬,而延误了的时间即变成了“业”,它的功能是“障”,这也许就是民间“业障”(孽障)一词的含义吧?再漂亮的杯子,由业所障,也变得丑陋了,甚至失去本来面目。
这让我想起神秀的一个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
因为有慧能对比,曾经觉得神秀不怎么的。但是现在看来,神秀已经了不得了,而且他的药方可能更适合我们。因为更多的人根本无法做到真空,而只要“有”在,就不可能不染尘,因此还是“时时勤拂拭”靠得住。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妙是妙,却让我们无法企及。
明珠之所以蒙尘是因为它没有一双除尘的手,为此明珠不明。
那么生命呢?一个双手被绑的人是无法自己松绑的,就像一个沉睡的蜡烛无法自燃。为此,“对方”就显得重要,火种就显得重要,已经解脱的人就显得重要。
沉睡何尝不是另一种尘垢,绳子何尝不是另一种尘垢。
它是何时落在我们身上的呢?
我们又是如何落入它的圈套中的呢?
我们找不到答案,因为我们的心上满是尘垢。
尘是最不起眼的东西,最容易让人忽略的东西,但正是这种不起眼,让我们不知不觉地蒙上了眼睛,一个蒙尘的眼睛当然看不到真相。
一个蒙尘的心灵呢?
尘是落的,垢是结的;尘是无法避免的,垢是可以避免的。因此尘可以借助吹气扫除,垢则需要水了。这让人不由想到水,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水?
剩下的话都毋须说了。
水,一个多么盛大的慈悲。
水不能洗水,尘不能染尘。
太喜欢这个句子了。
一个多深多大的奥妙啊。
水为什么不能洗水?因为水是无分别的,准确些说是无法分别的,是“一”,一滴脏了,所有都脏了。
水是无法把其中的任何一滴脏水从中清除的,因为即一即亿。
这个秘密真是太大了,大得让人胆战心惊。
那么怎么办呢?只有防微杜渐,只有从防做起。
这就回到尘。
但尘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为此除尘显得必需。
剩下的事情,就是除尘了。
甚至可以说是全部。
尘为什么不能染尘?还是因为尘是无分别的,只要是尘,不论你是哪路来的,姓甚名谁,都是一样的。
为此,尘就有机可乘。
因为前尘,后尘得逞;因为后尘,前尘得逞。
这个天大的掩护,就打到底了。
只要是尘。
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尘垢,可能是不洁的文字。它们不经意落入我们心田,积久成垢,再久成岩,洗也难了。
灵魂往往就是这么窒息的。
即使洁净的文字,假如不能变成水,也是灰尘之一种了。
为此,水性的文字才是地道的文字,善的文字。
而要把文字变成水,或者说让如水的文字流布人间,需要怎样的一种心泉。
由此观之,一直争论不休的真假文学之辩,也许就有了依据,同时也变得明了起来。
而尘是无法避免的,只要我们在时间里。
那么洗就成为生命的必须和必需。
那么水就成为生命的必须和必需。
那么如水的文字就成为生命的必须和必需。
那么生产净水的人就成为生命的必须和必需。
那么,文学还会死吗?
美国带队休主动要求朗读,当我听到自己的文字以另一种声音出现时,有种时空恍惚之感。第一个发问的是诗人欣玉,这是不是你把你的诗集名为《我被我的眼睛带坏》的原因?我说是。欣玉说,你能不能给我们更为详细地讲讲“菩提”是什么意思?我说“菩提”一词译自古印度语(即梵文),用以指人忽如睡醒,豁然开悟,通达真理,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等。我知道,因为这个回答,我又要做一次狐狸了。接着西川老师问我,你怎么看待“水至清则无鱼”。我说,还是有鱼,只不过是另一种我们看不见的鱼。
大家哑然。
事实上当翻译选中这篇短文时,我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得到翻译认可,担心的是我知道这是一个大暴露,而一个暴露了的作家意味着给自己贴上标签,不好玩儿。这也许就是小时候每每向爹和娘问问题,爹和娘每每回答等你长大就知道了的原因。现在想来,让人好生感动。
六月问,今天全世界的人都要滚锅盔吗?美国人也要滚锅盔吗?日本人也要滚锅盔吗?啊我把你压(阿尔巴尼亚)人也要滚锅盔吗?毛里求死(毛里求斯)人也要滚锅盔吗?
五月说,那当然,不但全世界的人在滚,而且……
我看你而且个啥。
不想五月滚豆子似的说,而且全银河的人都在滚。
六月用一个响屁表达了对五月姐的佩服。
连屁都在滚,五月抢先回答了这个问题,又有些后悔。这本来是爹回答的一个问题。就回头看了爹一眼。
哈哈,现在把灯笼点着吧。爹说。
小时候,父亲常用一个词“照灭”,他说,人的心里要有一盏灯,一盏长明灯,任何不洁的念头只要一升起就要照灭,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是防漏防腐防偏的关键。“照”怎么能够“灭”?当时不懂这个词,及至年长,这个词就出味儿了,接下来是佩服,继而五体投地了。
六月把火柴一划,灯笼里的灯就醒了,灯笼里的灯一醒,夜就醒了,夜一醒,路就醒了。六月回头看了一眼五月,五月整个背上是一个锅盖一样的锅盔,就像一个红军女战士。再看,又不像了,像个什么呢?还是像新媳妇。怎么女孩子骑在马驹上就像个新媳妇呢?六月又看爹,爹就像个新媳妇她爹,爹怀里的羊羔就像是新媳妇她外甥。六月又看马驹,马驹倒像个新郎官。如果马驹是新郎官,我呢?六月想看一下他自己,可是看不到。六月的心里就有了一个遗憾。如果他是五月就好了,就可以看见他,就可以想啥时看他就啥时看他。可是,他又如何变成五月呢?当然要把鸡窝里的鸡打飞。然后呢?还要编一个辫子,还要穿上花衫子,还要……可是既然自己变成五月,那么六月就不在了,六月不在,五月又在哪里看六月呢?六月被自己搞糊涂了。
一天晚上,爹躺在被窝里给我和姐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我问爹孙悟空是不是最有神通?爹说不是,最有神通的是佛,佛的神通是漏尽通,什么意思呢?并不是漏光才能通,而是把所有漏的可能全消灭完才能通;就像一个水管,如果有沙眼,就不可能让水通过去,因为它有漏;就像一个桶子,如果桶底有缝儿,水就装不满,因为它有漏。现在想来,写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假如我们在途中不停地漏,又何尝不是在玩蒸沙成饭的游戏?而古人用沙做漏,真是再智慧不过,他让我们看到非永恒的光阴就是这样行走的,他提醒我们寻找永恒时间,可是我们却是那样的不情愿。
而现在,我就在一望无际的沙中,也在一望无际的漏中,包括我的这些有关漏的念头。
东方动时,四面八方的人到山头,四面八方的牛羊到山头,四面八方的灯笼摆在黄土香案上,四面八方的小脑瓜映在灯光里。
会长清了清嗓子,神情庄严地点燃了主烛。然后手捧一束檀香,屏息点燃。向着祭台跪了,吰吰吰地诵唱:
良善民上山来双膝跪倒。
众人哗地一下齐齐跪了,合唱:
良善民上山来双膝跪倒。
会长领唱:
金炉里点着了十炷信香。
众人合唱:
点着了,点着了,十炷信香。
会长插一炷香,唱:
一炷香烧予了风调雨顺。
众人合唱:
烧予了,烧予了,风调雨顺。
会长插第二炷香,唱:
二炷香烧予了国泰民安。
众人合唱:
烧予了,烧予了,国泰民安。
插第三炷香,唱:
三炷香烧予了三皇治世。
众人合唱:
烧予了,烧予了,三皇治世。
……
三皇是怎么治世的?六月问爹,爹示意六月不要分心。六月这才发现,今天的爹和平时是不一样的。六月从爹的脸上看到了一个空,一个无比坚决的空,铁板钉钉的空。
骆驼竖着身子攀峰时,我的脑海一片空白。“高空”这个词蓦然闪现在眼前,只有“高”才能“空”。伸手摸一把天,天空就留下我的五道指痕。
依次,会长向黄土香炉插了十炷香,唱了十句词,信民附和,依次为:
良善民上山来双膝跪倒,
金炉里点着了十炷信香;
一炷香烧予了风调雨顺,
二炷香烧予了国泰民安;
三炷香烧予了三皇治世,
四炷香烧予了四海龙王;
五炷香烧予了五方土地,
六炷香烧予了南斗六郎;
七炷香烧予了北斗七星,
八炷香烧予了八大金刚;
九炷香烧予了九天仙女,
十炷香烧予了十殿阎君。
绕过一个沙丘,天哗地一下亮起来。再看眼前的沙漠,就像一面巨大的绸缎被面。丝绸之路,原来如此。
接着,会长把一面上面写着“报答神恩”的大红绸匾披在众神位的身上,然后长腔拖地:
一叩头。
只听刷地一声,山头上就垂下了沉甸甸的麦穗。
二叩头。
谷穗。
三叩头。
糜穗。
叩头一毕,三声罄响,就有一种声音的波浪在山头上荡漾开来,在无边无际的天地间留下一道道涟漪,也在五月和六月的心上留下一道道涟漪。
在五月和六月心上留下涟漪的还有“报答神恩”四个大字,那是爹的杰作呢,爹为了写这四个字,专门到集上买了新毛笔、新墨汁、新衬纸;爹为了写这四个字,把身子洗了十遍,把脸洗了二十遍,把手洗了三十遍;爹为了写好这四个字,用旧毛笔在报纸上演习了四十遍,用新毛笔在新衬纸上演习了五十遍。
现在,这么多人对着它磕头,怎不让人自豪得脚心发痒。
日出峰终于到了。
不等驼人指令,骆驼就自动跪了,温顺得让人心生潮湿。等最后一个人下完,它们就哗地一下站起来,迅速随着驼人下山。大步流星的,义无反顾的,毫不拖泥带水的,就像刚才的这趟辛苦没有发生过似的,就像沙峰上的这些人和它们了无干系似的。让人想起故乡,想起故乡的那些良家女子,她们给邻家做了整整一天义工,主人要留饭,她们一声不用了,就起身回家,尽管她们已经很饿,很渴,也很累,但她们的步子轻盈神态安闲,主人的客气还没有落地,她们已经从大门口消失了。
在心里向它们招了招手,说了声再见,我不知道它们是否听得见。
事实上不可能再见,若要再见,除非来世了。
看着驼队从沙丘背后消失,我的心里一阵莫名的难过。天底下有无数的骆驼,也有无数的人,可是和这些骆驼,我们却有一程之缘,一程,仅仅是一程。尤其对于这些美国朋友来说,这是一次多么偶然的邂逅。不由得想,安排这次邂逅的,该是一种怎样的大力,又该是一种怎样的古道热肠?
接着唱诗班齐唱《孝经》。六月和五月都是其中的一员。会长一声“开宗明义章第一,预备起”,天地间就刷地长出无数的青禾,那是孩子们带了露珠的“之乎者也”:
开宗明义章第一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大雅》云:‘无念尔祖,聿脩厥德。”
天子章第二
子曰:“爱亲者不敢恶於人,敬亲者不敢慢於人。爱敬尽於事亲,而德孝加於百姓,刑於四海,盖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诸侯章第三
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卿大夫章第四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地主为大家准备的早餐是菊花茶加重阳糕,蓝天清风相佐,让人觉得进的并不是茶,用的并不是糕,而是一种风餐露宿的味道,还有一点晨钟暮鼓的肃穆,连同一种被强调被唤醒了的时空。平时喜欢笑闹的队员,也收起了鬼点子话匣子。翻译给美国队员讲着“糕”“高”相谐,“九九”“久久”相谐之妙,“一阳”难遇“二阳”难逢之殊胜。美方带队休说,就像美国作家和中国作家在一起,也是重阳。翻译看了看大家,赞赏地点了点头。翻译说,其实吃糕饮菊只是各地重阳节的共性项目,个性项目那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走进中国的传统节日,你就会发现,中华民族是一个批量生产诗意的民族。
就有一条河在美国朋友的脸上汩汩流淌,那是一个有关诗意的流水线。
士章第五
资於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诗》云:“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
六月能够看到从他们嘴里出去的“之乎者也”敲打在天上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声音,能够看到从他们嘴里出去的“之乎者也”种子一样落在土里的声音,发芽的声音,开花的声音。六月觉得脚下的高高山不再是高高山,而是一个别的什么东西,至于是什么东西,他一时想不清楚,也不敢想,因为他得记句子。爹说,背诵就凭着个专心,要像锥子那样,扎下去,扎下去,一直扎到底。
这时,有一只鸟从人群里飞出来,在厚厚的诗的海面上翩翩起舞,那是五月姐的声音。六月加了一个码追上去,和姐比翼双飞:
庶人章第六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三才章第七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
……
翻译说,如果把中国人吟诵重阳的诗作连在一起,可能会绕地球九十九圈。就有一个名叫重阳的宇宙飞船绕着地球旋转,直把菊花酒洒满了宇宙,把茱萸种子洒满了大地。最后,翻译给他们讲了那首中国人妇孺皆知的古诗。借着曙光,我从爱德华的眼睛里看到了“独在异乡为异客”,从大卫的眼睛里看到了“每逢佳节倍思亲”,从爱莉斯的眼睛里看到了“遥知兄弟登高处”,从开开的眼睛里看到了“遍插茱萸少一人”……却一点儿也没有看到“战地黄花分外香”。一种格外的感动从心里升起。“人生易老天难老”。特别想给美国朋友讲讲这个“天”,讲讲中国人心中的“天同覆,地同载”,可是我偏偏不懂英语。就有一个“遍插茱萸少一人”一样的遗憾横亘在心里。
在漫山遍野的《孝经》中,黑暗散去,曦光微露。接着出场的是一个化了脸的人。六月问爹他是谁,爹说是重阳神。
只见重阳神手捧一个锅盖那么大的大饼,开口了:
重阳神下界来手持大饼,
它本是玉皇帝赏于黎民;
一个饼赏予了吉方宝地,
两个饼赏予了福寿双星;
三个饼赏予了孝子贤孙,
四个饼赏予了平安四季;
五个饼赏予了五谷丰登,
六个饼赏予了六六大顺;
七个饼赏予了七七有巧,
八个饼赏予了阴阳八卦;
九个饼赏予了九九重阳,
十个饼赏予了十全十美。
重阳神赏饼时,六月早已双手端着大锅盔,无数次地向自家院子瞄准了。
重阳神的那个“美”一落地,六月手里的锅盔就第一个起跑了。
接着有无数的锅盔跟着出发。
就有一山的锅盔在转,就有一山的重阳在转,就有一山的六六大顺在转,就有一山的十全十美在转。
十全有多全?就像重阳一样全。
十美有多美?就像锅盔一样美。
十全有多全?就像爹一样全。
十美有多美?就像娘一样美。
十全有多全?就像天一样全。
十美有多美?就像地一样美。
……
对面是一个茫茫沙海。太阳的先头部队已经出发,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做着热场。早点已经吃过,家当已经备好,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期待,就像是一场战斗马上就要打响。而那将要从海岸上升起的太阳,既是信号,又是目标。
就在我做如此想时,太阳的头皮冒了出来。几乎在同时,我听到大家的喉结嘎地响了一下。接着,就有许多“长枪短炮”向太阳瞄准。这次我没有动,我让我的相机寂寞在包里。我在用心观察着太阳是如何出生的。我终于发现,太阳不是升起来的,而是滚上来的。就像锅盔,故乡重阳节漫山遍野的锅盔,十全十美一样旋转的锅盔。
后记
2009年重阳,中美爱荷华写作计划文化探寻项目组行在中国,这是不才在敦煌段的一篇作业。
作者补记:2009年5月12日至26日,中美爱荷华写作计划文化探寻项目途中,左手大拇指进刺,未及时手术,致使感染化脓,26日在北京协和医院引流,回家疗养期间,右手草成,6月底输入电脑改定。
原刊责编 李向荣
【作者简介】郭文斌,男,祖籍甘肃,1966年生于宁夏西吉县,先后就读于固原师范、宁夏教育学院中文系、鲁迅文学院,已发表作品近二百万字。著有小说集《大年》、《吉祥如意》,散文集《空信封》、《点灯时分》、《孔子到底离我们有多远》,诗集《我被我的眼睛带坏》等,作品先后多次被多种选刊选载,被收入多种选本,被中央电视台选播。曾获第二届冰心散文奖、第二届国家金童奖、中央电视台电视散文奖、宁夏第七次文艺评奖一等奖。短篇小说《吉祥如意》获“人民文学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散文《腊月,怀念一种花》被收入《百年中国经典散文》。现在宁夏银川市文联供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