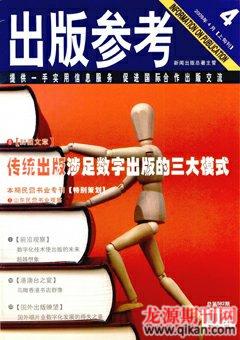传统出版涉足数字出版的三大模式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2007-2008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课题组
传统出版应该尽快向数字出版转型,实现产业升级,这是国际出版业发展的大趋势,这一点大部分出版人都能认识到,但对于该如何向数字出版转型,如何搞好数字出版则比较迷茫,无所适从。本文拟从教育出版、大众出版、专业出版三个方面对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的三大模式加以探讨,以期对各出版单位搞好数字出版有所借鉴。
一、 教育出版:数字信息服务模式
追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是一部知识和智慧累积的历史,出版物承担着人类智慧与文明的传承。当前信息社会,不仅提供信息,而且提供知识与学习知识的新方式、新环境。数字化时代,移动学习即是一种新型的学习方式。“移动学习是指利用无线移动通信网络技术以及无线移动通信设备(如移动电话、个人数字助理PDA、Pocket PC 等)获取教育信息、教育资源和教育服务的一种新型学习形式……移动学习的出现,本质上是教育与技术相互作用的结果,经历了一个教育需求与技术发展交互驱动的过程;它的出现不仅会带来人们观念的转变,还会促使整个人类学习环境的彻底改变。” 面对这种学习方式的改变、学习环境的变化,教材出版商如何根据这种移动学习的特点提供更为有效的内容?这是当前一大困惑所在。
从经济效益而言,当前数字化革命并没有给教育出版领域带来很大的冲击,尤其在我国,教育出版往往拥有自身一套内容资源与发行资源。数字技术在教育出版领域能被高效地运用于竞争之中,研发优质的数字化产品来获取教师的关注和采用,建设服务于学生教学的网络平台来赢得人心,积累数字化资源库以准备多元化产品的输出。这些在当前均是锦上添花,并非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1. 海外教育出版的启示
第一,积极建设标准化数据库。
教材出版领域运用数字技术来巩固原有出版业务,也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空间。通过搭建内容整合的在线学习平台,为原有的图书销售提供增值服务,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开展终身学习计划和远程学习服务,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空间。而这内容整合平台的资源来源,离不开以教育为中心的标准化数据库建设。例如培生教育集团的4000种信息类图书的在线数据库便是一种为客户机构提供的一种在线服务。
第二,发展基于提高服务的教育出版数字化模式。
在提供增值服务的过程中,逐渐会形成独立于印刷媒介的服务,无论何种形式的媒介,提供的均是服务。教育出版区别于其他出版领域最大的特点是服务意识,为教学服务是其根本所在。在数字化发展过程中,这种服务意识同样不可缺少。麦格劳·希尔的免费黑板服务(Blackboard Service),源自美国康奈尔大学提供的信息技术软件,通过这一软件平台不同的教育资源可实现交流共享。麦格劳希尔免费为这个平台提供内容资源,还为老师提供免费WebCT教学管理系统,在这上面老师可开展教学调查等活动。Page Out互动交流在线服务则是指导老师建立和学生交流的讨论区,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另外还有通过网络提供多种素材,指导老师如何定制教学所用电子书的Primis Online服务。
麦格劳·希尔、培生等出版商建立CourseMart平台,用来和学生交流,了解学生学习中的切实困难以此来优化服务。如每个学生的喜好有所不同,听课、记录的学习方式和喜好在练习中学习的方法是不同的。只有切实了解这些不同的需求,方能实现真正的个性化出版。这些平台的建设既巩固了原有教材的市场份额,又为远程学习和终身学习项目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高效的平台。
第三,协调好组织内部关系,在技术研发上投入资金。
培生教育出版集团中国区总经理桑建平认为,教育与多媒体信息技术的结合将是必然的趋势,而且会进一步加强。同时内容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技术仍将是服务于教学的辅助工具。但未来数字化对管理者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具有胆识与在实践中创新的能力。管理者要具有前瞻性,预见技术对于教育的影响与应用,数字化投入需要很多资金,管理者要能够说服股东。传统出版业在发展数字化过程中的观念转变,在管理体制上的打通,都是颇为重要的问题。
无论出版社规模大小,投入产出比的悬殊使得投入多少资金问题始终成为各社数字化的掣肘因素,部门之间的利益亟待协调。国内不少赞同改革的出版人认为,与其为出版社盖一栋新楼,或做其他奢侈的消费,还不如用作数字化的研发。
2. 我国教育出版数字化发展现状及可探寻的模式
教育出版紧密围绕个性化学习来实现,我国的文化和教育都有着与众不同之处,学校教育以应试为主,文化强调更多的是共性而非个性。在探索教育出版数字化的道路上,须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在实际中更要结合本国、本社的自身状况来实施。
在我国教育出版领域,或许只有高等教育出版社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和人力资源来做数字化的各项探索。对于其他大多数教育出版社而言,能做的可能应是如下几个方面的努力:
(1)数据库建设是发展教育图书出版数字化的基础。将多种媒体的资源按照统一的标准,分门别类数字化,为网络平台的查询服务及在线测评提供基本条件。数据库是重要的出版资源,对数据库进行内容的整合开发,实现多种利用,切不可将数据库资源全部出售,可考虑售卖数据库的服务和多种形态的产品。
(2)发行数字化版本或提供短版印刷,结合网络平台上的原创文字、课件进行重新组合。这项措施最佳实现平台是在内容管理系统,但大多数出版社只能坐等这一系统进一步完善得以广泛推广之日。国家目前正在研发的复合出版系统,正是为将来出版的同一资源重复利用做好准备。
(3)推广移动学习定制。中国具有近14亿人口,是全球手机使用的最大市场。关于使用手机的各项数据表明,和通信运营商的合作,开发教学短信包定制服务、原创手机小说定制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还可拓展至在一定范围内的手机群组中开展千人共创一本书之类的活动,在一个年级或是一个学校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对特定的教材进行增改,提供意见。我国的教材地域性很明显,并不是完全统一,此举能满足特定师生的个性化需求。
(4)形成学习和服务相结合的网络整合平台。借用这一平台实现互动教学,将测试、教学资源、教学管理等融为一体。研发平台需要相对应主要学校相关部门的切实配合,在应用推广方面同样须借助校方力量。其中,致力于教育学习游戏的开发也大有可为。“在游戏中学习,一边玩一边学” 是尼葛洛庞蒂的数字化生存畅想之一。
(5)实现网络营销,创建或和行业内合作,组建永不下架的销售平台,充分发挥长尾效应。在新课标重组教材出版市场、招投标压缩教材出版利润空间等情况之下,我国教育出版近年来利润率下滑。在这前提之下,运用数字技术吸引更多的原有份额是最重要的部分,运用提供电子教材、网络教育资源、互动学习等技术支撑,为内容的输出提供保障。在增加收入来源方面,提供无线增值服务和定制服务都是可优先考虑的措施。
另外,其他行业所建立的在线学习网站也值得教育出版界探讨。比如用播客推动远程培训,一百易 (100e)的数字内容交易服务平台模式,在网络平台上实现付费在线阅读、下载、学习、互动交流,将教育、出版、互联网紧密结合。
二、大众出版:与内容相应市场互动模式
1. 海外大众出版数字化的启示
企鹅出版公司的CEO约翰·马金森、兰登书屋CEO彼得·奥尔森、哈珀·柯林斯主席布里恩·莫里和霍兹布林克董事会成员鲁迪戈·萨拉,在2007年10月10日法兰克福书展上就如何进行数字化并取得销售收入进行了讨论。这四位是国际四大大众出版社的代表人物,一致认为出版社对数字化投资是必要的。马金森和奥尔森均表示,尽管各自出版社中数字出版的销售仅占总销售的1%,但是集中发展数字化的工作非常紧迫。如哈珀·柯林斯大众出版领域数字化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1%,高等教育可能是10%,STM达85%~90%。
第一,和搜索引擎实现共赢。正如哈珀·柯林斯总裁Brian Murray说:“我们认为年轻人喜欢用上网浏览的方式进行阅读,当下在美国每月大约有100亿个搜索问题在网上得到解答。所以有必要和搜索引擎建立关系,让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到我们的书,这是机遇所在。” 第二,特定领域实施网站营销,建立直销渠道。哈珀·柯林斯市场营销计划是创建了一个爱情小说作者的网站,大约40位作者进入网站,放上他们的作品和新书等,编辑对内容进行加工。读者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浏览、看视频、买书等。第三,不同版本图书实现立体化开发。大众出版只靠图书的收益比较单一,影、视、书立体开发逐渐成为趋势,利用图书的内容创意,拍摄电影、电视剧,实现融合发展。第四,和专业出版、教育出版一样,大众出版领域数据库的建立和积累是开展数字化的基础,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另外,在大众出版领域,德法出版传媒集团逐渐控制英国图书市场。在英国《卫报》评出的年度百本畅销书中,有83本出自四大集团:贝塔斯曼32本、阿歇特(Hachette)28本、新闻集团9 本、培生14 本。其余的 17 本则出自布鲁姆斯伯里、法布尔及其他小出版社。 这些大型集团发展数字化出版具有相对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人才储备。
2. 我国大众出版可探寻的模式
随着经济生活的提高和休假制度的调整,旅游逐渐成为生活时尚的一大重要方式。旅游热带动旅游类图书的销售,“在2000、2001、2002年,旅游图书市场规模几乎成倍增长,2003年受非典重创大幅下滑,在探底反弹之后市场增长速度趋于平缓。但其中的出境游图书还有较大的市场潜力”。
发展与相应市场互动的模式是值得推广的,以旅游类图书为例,出版周期过长使其承载信息失效是一大弊端。信息更新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难以得到及时更新。读者往往需要购买全面的指南类图书,其中所提供的景点、车次及餐馆等各类信息须是当下具有指导意义的。另外,缺乏互动性和无法满足个性化需求同样成为印刷版本的旅游图书发展掣肘因素。www.phsea.com.tw 是提供权威的关于澎湖地区旅游信息的网站,包含互享的丰富旅游资料。不仅吸引了众多旅游产品厂商和企业,而且还有手持电子地图导航器制造商欲付费取得网站信息使用版权,该网站还将推出印刷出版物。另外,旅游图书还有多种形式的数字化拓展空间,如台湾大舆出版社从事地图与旅游内容出版40年,当地排名前十的汽车制造厂生产的汽车均能看到大舆的数字地图产品,并于2001年开始研制手持电子地图导航器。
国内大众出版市场在这十年间传记文学得到快速发展,明星人物的经历、观点和思想成为图书出版的丰富资源。199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赵忠祥的《岁月随想》首开先河,随后刘晓庆、杨澜、程前、姜昆、倪萍、宋世雄等名人纷纷出书。图书与相应的影视市场相结合,图书立体开发是当前一大热门,凤凰卫视的各主播吴小莉、曾子墨、陈鲁豫等闻名海内外,其相关的图书销量也非常可观。陈鲁豫与节目相关的图书逐渐形成一系列,数量和杨澜访谈录看齐。在此基础之上,出版人可考虑鼓励作者开通与图书相关的网站,创办与此内容相关的电子杂志。演员徐静蕾在出版博客书之后还创办电子杂志《开啦》,并有意打造开啦娃娃这一品牌,塑造成卡通的标志,印在服装、茶杯等物品之上销售,通过广告、下载次数售卖、会员制等方式实现赢利,并以此举办像春季运动会之类的活动,获得赞助。这些举措自然而然贯通了产业链,堪称与内容相应的市场互动模式的典范。
(三)专业出版:基于知识结构的定制模式
专业图书包括法律、金融、科技、医疗等行业的专业用书,包括行业性专著、学术性专著和专业性工具书,为行业从业人员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服务。专业出版提供功能性较强、能解决问题的信息产品。这一领域图书的受众群体定位清晰,从事研究、教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会主动通过互联网搜求相关信息。相对其他领域,专业图书出版数字化发展的制约因素不在于技术,而在于经费及相关政策配合。国际上学术期刊开放存取模式已相对成熟,而在图书领域却值得进一步探究。
1. 专业出版受数字技术影响现状
数字技术对传统专业出版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知识的快速更新使得专业出版满足不了读者的需求。图书可能还在印刷厂,书中的观点和知识可能已被后来者更新,读者宁可选择其他途径获取知识。另外,大学图书馆是专业出版所对应的主要销售对象,由于信息检索技术高速发展,读者能极其便捷地在各数据库中搜索资料。比如,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包括57个不同的电子库,由580万页的文档组成。目前用户能够用一个简单的搜索引擎快速浏览其中23个电子库。 习惯用计算机写作的一代,喜欢将所有的资料存储于硬盘之中,方便携带、快速查询内容。
然而社会上对新知识、新技术的需求使这种独特的信息产品具有稳定的市场和持续的发展潜力。随着科学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专业出版的市场前景看好。在美国行业高度集中,三家出版集团占据90%的份额,深度细分。目前我国存在专业出版大众化、专业出版不专业的弊端,为此应强化形成自身专业的特色,使专业出版真正在本领域起到引领知识创新的作用。有的行业面临出版资源市场化的挑战,需要面对垄断资源减少的问题。市场还可采取直销的形式,建立读者数据库。
2. 专业出版发展的契机
由于专业图书读者面窄,一旦断档,绝版、脱销就很难再次印刷,POD可解决专业图书出版生命周期不断缩短等问题,可及时修订,实现随时更新。按需印刷还能为个性化和特色化的服务提供良好的平台,拓宽发行范围,缩短出版周期。在台湾出版界总结出获利平衡点的衡量标准,认为印数1000本以下的适合POD,事实上早期的标准约为350到500本,但因为技术的不断提高,这个衡量标准的数量将不断提高。 在内地出版界总结的获利平衡点标准一般为300本左右。
专业图书内容呈现出链接的重要性,知识之间的关联是专业内容的一大特色。《哈佛商业评论》原执行编辑尼古拉·卡尔曾在不列颠百科的博客上写道:“那种逐句逐段地去理解世界的深思冥想者,已经一去不返了。他被那种在链接和链接之间冲撞的飘忽不定之人所取代,此人在连续不断地成排更新的孤立元素之间以及在映象中更新的映象之间变魔术似地将世界显现出来。思维的线性变化成了印象的非线性。” 正是基于这种知识之间的关联,专业出版可发展基于知识结构的定制出版模式。清华同方从1996 年开始做知识内容整合的工作,按照知识体系及其内在联系,将分散无序的各类文献资源整合在一起。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研究生著作和学术出版中心,如能进一步推广高教社在其他分社进行试点的数字化经验,其专业出版数字化定制也不失为可探索的项目。另外,在内容结构化基础之上,法律、金融、卫生等专业出版领域的出版社可发展信息定制。
定制模式离不开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约翰·威立的Steven Miron认为,过去出版社出版图书都是以产品为中心,现在已变成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即网络技术创新使其能为客户提供更加符合需要的内容和服务。
在专业出版的数字化领域,更多关注的是专业期刊,专业图书的数字化正在起步。2007年由中国版协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主办,人民卫生出版社承办的“科技出版社‘十一五规划制定交流会”在京召开。会议代表们均明确表示要积极发展专业出版数字化,认为标准化的格式是重中之重。(本文节选自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2007-2008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有删节、修改,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