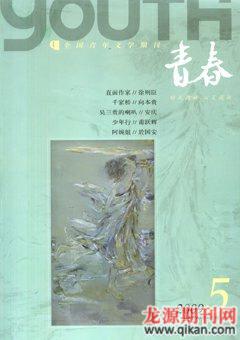短暂的猫咪
聂 尔
妻子认为我们家厨房里钻进了老鼠。这是我的说法,妻子的说法是,怎么能说是我认为,明明就是有嘛!但她所发现的却只是老鼠活动的迹象,并非真的老鼠。紧接着,客厅里空调通向外面的那条管道里,传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有灰泥的小碎块掉落下来。这是我在深夜里亲耳听见和看见的。于是我基本同意了妻子的说法。
有一天,妻子下班回来,买回几团洗碗用的铁球,塞进空调管道里,从此客厅里无事。但厨房仍不太平,标志就是夹鼠板始终张开着,却完好如初。妻子认为这是老鼠不肯就范。卖夹鼠板的那个妇女对我妻子说,老鼠是意虫,对于它的任何意图都不可声张,只能悄悄地,仿佛没事一样,有一天你会终于发现,老鼠上了夹鼠板。我笑着说我妻子,你就是太能声张,你跟门房路师傅站在小天井里大声嚷嚷的那些话,老鼠岂能听不见。
我和妻子整天在厨房里遍查各种孔洞,以求得老鼠的来历,也无结果。我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出了在各自心中都曾酝酿过的一个办法,那就是只好求助于莫非家的那只猫了。第二天我发短信给莫非,询问猫的近况。那只猫是我和莫非在前年秋天从邢昊的故乡襄垣县南姚村带回来的,那时它尚在童年。为了带着它越过二百多华里的路程,而且中途转了一趟车,吃了一顿饭,其中的小小辛苦我至今仍然记得。但是,莫非却仿佛忘记了,他对我关心猫的情况感到困惑。当我说明意图之后,他才表示:“非常乐意效劳,定当不辱使命。”当天傍晚,我在小区遇见莫非妻子,她说她已知道情况,正准备回家把猫抱下来。但她也不无忧虑,她说猫被楼下那家装修的声音吓坏了,怕见人,不敢出门,不知能否完全得了这个任务。
我说过,前天秋天时,猫尚处于瘦弱而无知的童年,是我陪同它从南姚村走进城里,上了莫非家的六楼。那以后,我并没有再见过它。此番重逢,令我大吃一惊。那天晚上,我外出应酬回来,问妻子,猫来了吗?答曰,来了。在哪呢?在床底。哪个床?中间卧室的床。妻子走到床前,猫咪猫咪叫了半天,并以食物相引诱,它终于亮相了。它踏着轻柔的虎步来到卧室门口,它全身的毛发长长地张开,粗尾巴竖立在空中,颇有意味地高高摇摆着。我不由得大声叫道,它怎么这么漂亮!妻子说,它是挺漂亮,但它胆小,来了就钻进床底不出来。说话间,它又重返床底。
晚11时以后,妻子好说歹说把它引进厨房,关住厨房门,让它与老鼠共处。约凌晨三四时,我和妻子都听见,它在厨房里一声又一声不停地叫:阿呜阿呜阿呜。打开厨房门,放它出来,仔细观察整个厨房,到处都没有它吃掉老鼠留下的痕迹。到底吃了老鼠没有呢?它不回答,它开始在全家各个角落里逡巡,它有时抬起虎样的头来,望一眼我们,更多时候它望都不望我们一眼,低下头独自在地板上来回走动,它低头捉摸着任何一块地板,捉摸着每一寸光滑而没有内容的地方。它的目光引得我也去看它所捉摸的地方,我却看不到任何东西。
随后两天,白天它仍钻进床底,不知在里面干些什么,随着夜色降临它才出来,并神秘地活泼起来了。我们敞开所有的门,包括厨房的门,任它走动。它的一个小爱好是穿越茶几下方的搁板,从药品,食品和调味品等乱七八糟东西形成的复杂道路上穿过,却能丝毫不改变那物品摆放的脆弱局面。有一回它跳上床头柜,从电话,台灯,烟灰缸,打火机和我的茶杯中间穿过,床头柜很小,而它却可以称之为是一只雄壮的猫,所以我特别担心我的茶杯,但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它喜欢行走在狭小而复杂的局面里,它来到这里,那里,并非有什么目的,它好像一切都只是为了经历过,就像我小时候去我们村附近的那些村庄一样,只为的是我已经去过了那里,并且两次三次无数次地去过了。它也是如此,它最常去的地方是窗台,它蹲在窗台上凝望着窗外的夜色,那若有所思的样子令我心潮为之起伏。有一回,我靠在床上看书,它进来了,它用头挑起窗帘,呼的一声跳上窗台,然后是一段令人心动的寂静的时光。我一边看书,一边用眼角的余光瞅着窗帘,但窗帘安然地垂下,仿佛后面没有一只猫,直到哗啦一声响,它从暖气片的隔板上滑下来了,证明它确实是在上面的。它对高处真是情有独钟。我数次看它如何跃上窗台和写字台。我把我的观察所得向妻子报告,她说它其实很想上柜顶,好几回蹲在沙发上望着柜顶,跃跃欲试,但它可能知道自己跳不了那么高而最终没有贸然尝试。而我觉得它蹲在写字台上的样子很好。我甚至设想,如果有爱伦·坡来为它在写字台上的身姿赋诗一首,那是何等的情致啊。我的写字台足够宽大,因为我长期使用电脑近年来较少走近它而使得它略显荒凉,如今有猫庄严而神秘地蹲坐其上,伴以旁边高高的书堆,和两侧森然的书架,以及窗户所透示出来的黑暗的夜色,令整个书房为之顿然改观。但它忽又蹿下,进了厨房。我在卫生间时,有时看它从厨房悠悠走来,以为它进卫生间有事,它也的确有事,它在卫生间远不够宽敞的地板上游刃有余地连打几个滚,呼一声又蹿出去,奔进了书房。它的这一连串的动作初看是围绕着有一个目的的,但究竟目的何在,却非我所能理解。
又一日,二哥全家来我们家闲坐,看到猫,自然夸奖了一番。二嫂说,这只猫不像猫,倒像只狐狸。这主要指的它尾巴粗大,并摇曳有致。二哥是插过队的,比我毕竟多见识。他讲起了有关的经验。他说猫吃老鼠是不留一点痕迹的,它要把最后一滴血都舔干净。这为厨房里老鼠的存在与否更增疑云。二哥小时竟然多次带领猫捉拿过老鼠,令我大为称奇,因我竟没有一次这样的经历。二哥说,领上一只猫,拍拍柜门,然后人离去,从门缝往里偷窥,看到的是,猫警惕地注视着柜门,等待老鼠出来,老鼠一出来,猫首先发出叫声,令老鼠变得迟钝,然后迅速出击捉住它成为易事。天生就是捉老鼠的呀!二哥感叹说。
但它到底捉住并吃掉厨房里的老鼠没有,成为一个谜。既然它吃与不吃都不留痕迹,这谜就一时无法破解。倒是它那锋利的爪子在我家沙发下部的棕色皮革上,留下了不可消失的印记。我几次看见它是如何对待那块无辜的皮革的。它以快速的节奏和无数的动作,令那块皮革发出嘶哑的叫声。我大声吆喝着赶走它,它却又在完全出人意料的时机里重做一遍。我以前就听说过,它这样做是为了磨短它的指甲,因为它是爱干净的。这倒使我无法过于怪罪它。而且,哪怕是在它刚刚做过这事的当时,它的样子也显得比那块棕色的皮革还要无辜得多。它总是显出一付悠闲而毫无负疚之心的样子,它难道知晓人心总是不欲深究罪恶,甚至是迷恋于犯罪的?
最后一天,妻子去上班,我外出开会,整整一天家中无人。到傍晚回家,家里猫臊味冲天。妻子大叫,你闻到味道了吗?我嗅一嗅,确实是有。她又说,你知道它在哪里睡觉了?我说,哪里?它在我的被窝里睡了一天!哎呀,送走它吧!恰在此时,猫主人莫非打来电话,问,我的猫表现如何?我答道尚可尚可。然后,莫非来我家要领回他的猫。彼时,它正端坐在我女儿房间的写字台上,莫非满面笑容进去,把它托在手上,高高举起,带它回了家。猫本来没有家园感,它在我家只呆了三几天,已经能够表现得体并怡然自得,但我不能凭此一条,就否认猫是莫非家的猫。
只是从此我进家门,没有了猫咪可叫,我不再能够叫它一声,然后等着看它究竟从哪一个隐秘处走出来,给我一个惊喜。但无论如何,它毕竟来过我家了。几天来,它像一个神秘的存在主义者,带我勘探了:窗台以及其外别样浓重的夜色,茶几下搁板上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隐秘通道,地板上的每一条砖缝直至其每一寸光洁的空无之处,还有我那久已无人光顾的大写字台荒凉的表面,以及我家所有可能的角落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多少年来,这些事物被我熟视无睹的目光和丑陋而实用的原则所扼杀,如今在它的注视之下,它们才重新返回到了存在的领域,并呈现出如同山峰一般不同的高度,就像夏季的即将来临的雷雨照亮了蚂蚁的通衢大道一样,尽管广大的天空前所未有地阴晦而恐怖,但正是在此时,各种各样的存在才反而能够尽逞其无尽的悲情和欢乐。
我记得,我在我的童年时代曾经有过这种对于存在的多样性的关注,但后来成长把它夺走了。现在我写出了上述的文字,可它顶多只是对早已走过的林间道路的眺望和怀想。那条路已经不可能再返回。
作者简介:
聂尔原名聂利民,生于1960年,出版有散文集《隐居者的收藏》和《最后一班地铁》。现居山西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