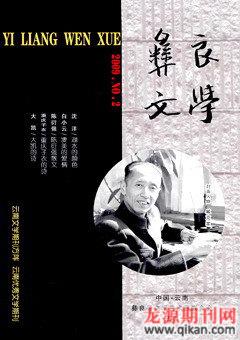梅花驿的诗
梅花驿
矿难
在酒局上
他说起昨天的矿难
眉飞色舞
像传达毛时代的特大喜讯
“这些被淹的35人
一个出不来才好
看看市长县长镇长们的
乌纱帽怎样去保”
说到这里
正好电视播出
记者从现场发来的最新报道
“经过20多个小时
全力营救
郏县高门垌煤矿透水事故
被困井下的35名矿工
有33人生还
2人死亡”
电视画面上
这些矿工
个个蓬头垢面
走出井口
全场一片欢呼声
这样的结局
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也让他大失所望
“砰”的一声
他关掉了身边的电视
“管这些鸟事干啥
来来来
今天咱们一醉方休”
他似乎有点沮丧
与先前兴奋的样子
判若两人
两棵香樟树
学校操场旁边
有两棵
根深叶茂的香樟树
树冠很大
我常常在树下
等女儿放学
有时我来的早
我就站在树下瞎想
如果我有钱了
我会出五十万
或一百万
把两棵树买下
让这两棵香樟树
永远长在那里
我把想法告诉女儿
女儿笑我傻了
说我不掏一分钱
这两棵香樟树
也会永远长在那里的
我常常梦见母亲
母亲已经不在人世
做梦时也能意识到这一点
让我稍稍宽慰的是
我仍然能够梦见
她在病床上坐起
口服一种很黄的药片
像生前一模一样
我们做不到的地方
她会指点我们去做
而我们个个听话孝顺
重要的是她说的都对
譬如她昨天对我说的
对人要有仁慈之心
即使对可恨的敌人
也不要怀恨在心
我又一次记住了她的话
决定从今天开始
宽恕每一个有罪的人
朱丽叶
我见过她朱丽叶
不是在剧本里
电影里或舞台上
十八年前的某日
我目送她上了小火车
目的地是一个叫梁洼的
煤矿她在矿医院做护士
现在她在哪里我不知道
前几年听说那个地方
地下的煤已经挖完
煤矿关闭人去楼空
而她又能做什么
从一个少女到一个女人
要不了多少光阴
在大街上每每看到
漂亮女人我都会遐想
她也许就是朱丽叶
中秋节的月亮
写这首诗之前
我看了一眼月亮
月亮已经升起来了
她和七月十五的月亮
没有什么两样
写这首诗时
我又从窗口看了她一眼
她还是原来的样子
挂在树梢
傍晚,天上有一张笑脸
今天天气出奇的好
站在平顶山上往下看
能看到远处的平西湖
和对面缓缓的山坡
平时这些都是难得一见
所以我们兴致很高
多玩了一会儿
回到山下已是华灯初上
看冷晚的月芽儿越发清爽
她的上方还有两颗很亮的星
她们共同组成一张笑脸
稚气十足俯瞰着大地
我们心里也洋溢着笑
只是谁也没有向谁表达
山行
沿着羊肠小道
走到半山腰
几声鸡叫
从前面传来
我知道那户人家
已经不远了
槐花败了
从树上落下
花香也在飘
两头牛不见生
只顾埋头吃草
草房子比去年
更旧了一些
五亩山地
也基本撂荒
主人说孩子们
都搬山下去了
一棵千年古树
遮天蔽目
它的树冠里
藏着千万只蜜蜂
采蜜的嗡嗡声
病房记事
她来自太康
三十岁左右的年龄
患有乳腺癌
去年在县医院做了手术
现在来到省城
继续化疗
陪护她的是她的母亲
这次看病的钱
也是她娘家人凑的
她丈夫已经不主张
给她看病了
她拉着母亲的手
哭着说
“我不想死啊”
她的丈夫正在省城打工
晚上从工地赶来看她
见面的第一句话
“你怎么还不死啊”
接下来便是
她的丈夫和她的母亲
激烈争吵
她的丈夫解释说
去年做手术就花了
一万多块
粮食卖了
树也卖了
家里还有两个孩子
再这样治疗下去
什么时候是一个头儿
她的母亲决定明天回去
卖掉家中的棉花
现在帐上的余额
已经所剩无几了
无论如何
也要治完这个疗程
她躺在病床上
自始至终一句话
也没有说
只有她的泪在流
泪一直在默默地流
病房里的所有病人
和所有陪护
也都选择了沉默
白茄子
这种茄子
似乎已经不多了
平日我们常见的
是那种紫茄子
搁到三十年前
或者更早一点
我们经常把它挂在嘴边
“白茄子”
是一个地主的绰号
解放前的教书先生
他皮肤白白的
“白茄子白茄子”
大街里的孩子
在他的背后大声喊他
他正挑着一担大粪
往田里送
有一次在无人处
他神秘地
告诉我
他是我父亲的老师
并夸我父亲
小时候写小楷
写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