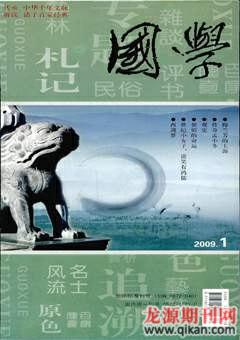写“梅孟”不如写“梅程”
徐城北
程砚秋不仅是梅兰芳的徒弟,而且更是梅兰芳的对手。在程砚秋最盛的时候,梅不得不暂时后退上一步半步。梅程间有矛盾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甚至在程砚秋逝世一周年时,周总理举行小型宴会招待程砚秋的家人时,还对一边作陪的梅兰芳说:“其实程砚秋对你是很尊重的,他的传记中几次提到你对他的帮助……”梅兰芳听了,连连点头称“是”。
说起程梅之争,颇有些曲折。30年代初年,程砚秋说,他梅兰芳访问过了美国,我程砚秋就紧跟着要去欧洲!1932年的元旦,他在报纸上宣布:去掉原来名字中的“艳”字,改名叫了“砚秋”;同时把原来的“玉霜”也改称“御霜”。同一天,他收荀慧生的长子令香为徒,举行了郑重的拜师仪式。随后的半个月中,程砚秋天天有即将赴欧的盛大宣传,梅兰芳几乎天天作陪。直到中旬,梅兰芳在北平前门火车站把程砚秋送走,这场“程旋风”才算结束。细看“程旋风”中的梅兰芳,却又是从容自若,当众亲切呼之“砚秋”,私下还是旧的叫法——老四。为什么梅兰芳能如此忍耐并殷勤,除了人的品性之外,还因为他身后赞助的银行力量弱了,不如程砚秋身后的风头正盛。一年半后,程砚秋从欧洲返回上海,随后又回到北京,他接受各方面的采访,发表了“访问欧洲戏剧十九点”的意见书,说出一些颇有力度的新思想。在这些方面,程似乎是强于梅的。
1946年,程砚秋与梅兰芳在上海不期而遇,先是奉蒋夫人宋美龄之约,梅程率徒合演了《四五花洞》——梅先生这边是新收的徒弟杨畹农,程先生那边则是赵荣琛。而赵荣琛随后则充当起梅程二人之间的“协调人”。此时的梅兰芳,“大面儿”上对程是尊重的,安排了戏的大格局,又显示了谦让之意。可随后两人在用谁的胡琴上发生矛盾,梅坚持用自己的文场:徐兰沅加王少卿。梅兰芳说,“就那么几句唱,还何必换来换去呢?”赵荣琛回去禀报,程砚秋没有办法,只能在约定时间来到梅宅合练。梨园在这方面是有规矩的,只能是弱势一方到强手一方去合练,而不能是相反的。再后,程提出服装要变革,梅兰芳则坚决不答应,“老四真有主意,竟要在腰上挖洞!他如真想挖——就让他自己去挖,我跟畹农反正不挖,我们还是用老服装老扮相……”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各穿各的。及至进入最后的排练,程砚秋来到了梅宅见梅兰芳——初见面时还是垂手侍立,并恭敬地叫声“先生”。梅兰芳则大度又随便地说,“坐吧,老四!”可以想见:程砚秋心中的感受应该是复杂的。随后梅程展开合练,当程砚秋唱出他那幽幽咽咽的声腔时,是京胡琴师徐兰沅先把胡琴放下,“您这腔儿我拉不了,还是把周长华(程砚秋的琴师)叫来吧……”程砚秋当然暗中高兴,徐是梅兰芳的长辈,他有了意见梅兰芳是不能驳的。于是以两堂文场分别为两人伴奏的格局就此形成。
随后不久,梅兰芳与程砚秋果真在上海打起了对台。梅在“中国”,程在“天蟾”,老生一边是杨宝森,另一边是谭富英,基本上打了平手。但最后程砚秋抛出了“杀手锏”《锁麟囊》,连续卖了几个满堂,这气势就把梅兰芳给“压”下去了。
程砚秋解放初期又到上海,献演了新戏《英台抗婚》,可能是身材太高也太胖了,效果颇不理想,这让他心里很恼。不久,他俩又险些在上海形成第三次对撞!当时,是程正在上海唱戏,而梅剧团则从江苏巡回,按计划很快就要到达上海——眼看又要跟程砚秋撞上了。这形势外人并不注意,但知道内情的戏迷会觉得“更有好戏可看了”。可远在北京的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得知,马上把马少波(中国京剧院党组书记)找来,命其立刻“把你们的两位院长拉开”。马少波雷厉风行,先找到梅兰芳。梅服从大局,延长了在江苏的演出期限;马又赶到上海,在戏院后台找到了程砚秋,向他讲明险些发生的对撞。程砚秋负气地发了牢骚,感叹人生的怨气真是挺大的。梅程之间的矛盾纠葛不仅有趣,既是时代的与社会的,同时还是戏曲的。
据说,梅兰芳之子梅葆琛在临终前留下遗言,希望电影在梅兰芳、孟小冬问题上不要过多纠缠。因为这段露水姻缘虽有噱头,但毕竟不是梅兰芳艺术生命中的最重要的部分。从二三十年代起,梅兰芳就一直处在整个梨园的主线与主导位置,但挑战者程砚秋也给他不小的威胁。如果程砚秋的机遇再好一些,如果他在饮食上的自我控制再强一些,如果万一梅兰芳这边又出现了闪失,那么随后的梨园到底是一种什么格局,就真的很难说了。
当然,也不能回避梅孟的婚姻。梅兰芳在遇到孟小冬之时(甚至之前),他就从极高处成名了,作为男性的他非常稳固。只要不出意外,多娶几房小老婆也根本不是“问题”。而孟小冬一方,无论舞台上怎么好,无论台下有多少人捧场,但终究是年轻女性,舞台上的青春也只有短短的几年。面对舞台上下的追捧,也丝毫不能减少她内心的煎熬:自己的归宿在哪里?作为女子,终究是要嫁人的。不但要及时出嫁,更要嫁得好并嫁得准。她不能像今天的时尚女郎那样,随随便便就委身靓男,以后再轻松说声“随缘”就又分手了。在旧时代,女性往往是“一嫁定终身”的。虽然她仅仅与梅兰芳同台演出过两次,但她深深懂得了梅的重要与稳固。嫁给他是不冤枉的,尽管是“小”,也是完全值得的。后来她进入了梅兰芳金丝雀的牢笼,那日子最初可能是美丽的。时间一久,她或许才感到其中的孤苦。她与梅兰芳离婚后,转向了对余派声腔的追求,文化品格有了大幅提升。
孟小冬中年陪伴杜月笙到了香港,过了一阵之后,她终于要杜给自己一个“身份”:“我在你这儿究竟算什么呢?是女朋友?是小老婆?……恐怕什么也不是。”杜很尴尬,把前房生的儿子叫来,让他跪在地上磕头叫“妈”。又在香港的饭店摆了几桌。这才让孟小冬踏实下来。我猜想杜在病重之际,一定会让孟小冬反复为之轻哼余派声腔,他甚至会在这声腔中检点平生。等杜死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孟小冬才移居台湾,像一个男人般过完她的最后岁月——她艺术上确是“冬皇”,其实又很惨淡。甚至作为孟小冬最有特征也最有意义的时间,是她以余腔陪同杜月笙走向死亡的那段岁月。孟小冬不断在杜的耳边轻唱。杜听得很认真也很陶然,他命令自己在上海的门徒“不许跟政府作对”,由此减少了解放初期上海可能产生的动乱。从这个意义上讲,孟小冬应该说是有功的。由此可以说,孟小冬与杜月笙,甚至比她与梅兰芳还要有“戏”,这里的“戏”,主要是指政治与文化上的价值。
舞台上的梅兰芳,看过的人太多太多。而舞台下的梅兰芳,真正见过的人则很有限。我们从纪录电影中见过梅的谈吐,他实在是一位梨园深处的行内之人,说话的男旦痕迹很重。就这个意义说,即使请梅先生本人扮演现实生活中的他自己,也不是很容易的。因为他是一位从里到外都被虚拟化了的杰出演员,每一举手与每一投足,都会自然而然带着京戏的“范儿”。想让他按照梨园外的普通人那样讲话与动作,肯定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如今,是在梅兰芳逝世将近半个世纪之时,由另外一些从没见过他本人的、也很不通晓梨园礼法风范的当代明星,风急火忙般就把梅兰芳等搬上银幕,实在不是明智之举。但反过来想,时代又是急切需要把梅大师搬上银幕的,即使一次不成就来第二、第三次。为什么?就因为梅兰芳这一代的大师的文化价值,太需要传递给今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