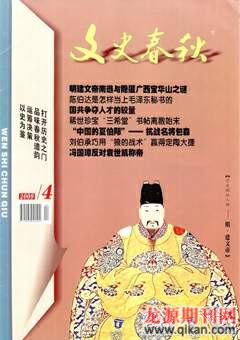民国“错中错”的“刺蒋杀宋”疑案
渝 文
孙科是孙中山的独生子,为了争夺国民政府主席一职,他两次出巨款请号称“江淮大侠”的暗杀大王及“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潜上庐山行刺蒋介石。事败后,他又策划行刺宋子文。与此同时,日本军部正密谋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制造侵略中国的借口。于是,在“江淮大侠”的子弹射向宋子文的同时,青红帮的枪口也对准了重光公使……
两份完全不同的回忆录
1931年7月24日上海《申报》载:“财政部长宋子文偕机要秘书唐腴胪及侍卫六人,昨晨七时由京乘快车抵沪。宋等下车后步出月台,方入该大厅,过问讯处,在候车室门前,突有暴徒多名抽出手榴弹、盒子枪、手枪向宋猛掷。宋之卫士亦拔枪还击,一时子弹横飞,烟雾迷漫,北站大厅忽变战场。当时正值旅客出站,闻声后四散惊走,秩序大乱。结果,宋氏以身幸免,秘书唐腴胪则身中三弹,于昨午十一时三十分因伤重殒命。”
此次行刺事件的内幕到底如何?战后,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他的《外交回忆录》中阐明事实真相:“(那时)日本樱会军官集团的一些人在上海不断进行策动,想要在日华之间挑起事端……当时的驻华公使馆陆军武官辅佐官田中隆吉大尉也是其中的一员。”“因为我是他们策动计划的障碍,所以他曾想杀死我。田中大尉想在宋子文和我搭乘同一列车到达上海站并肩走过来的时候,让他们开枪射击。直接进行暗杀的人是当时上海恐怖团体青红帮。但是我们日本公使一行人提前走出了车站,得以幸免于难。”重光葵还指出,在事情发生的当时,就有人觉察到这是日本军官的阴谋,并且在日本做过报道,战后田中隆吉还亲口告诉他当时的详细情况。

然而,过了半个世纪,同此事有直接关系的王亚樵的胞弟王述樵,在他的回忆录中却说,是孙科派马超俊到上海,商请王亚樵刺杀宋子文的。经费由马超俊负责;刺宋行动由王亚樵负责;上海方面由华克之负责;往来京沪联络由王亚樵的挚友洪耀斗负责。参与刺宋的人员还有郑抱真、张慧中……
1931年7月23日上午7时08分,宋子文下车时,华克之即嘱部下开枪,不意宋与秘书唐腴胪均着白哔叽西装,戴拿破仑帽,因分辨不清,误将唐腴胪击毙。
在叙述同一历史事件时,两份回忆录出入如此之大,究竟哪个是真实的?此次暗杀的谋划者究竟是田中隆吉还是王亚樵?枪击的对象是重光葵还是宋子文?枪击的幕后牵线人是孙科还是日本军部?误击唐腴胪的,是王亚樵的人还是田中隆吉的人?
现在,经过匡费时日的会集、鉴别中日双方的资料,特别是对于惟一了解事件始末的郑抱真遗留资料的整理,加上对其后人的深入探访,终于揭开这一疑案重重笼罩的面纱……
日本特务麇集上海
1931年春,垂涎中国“满蒙”已久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经过准备之后,一切基本就绪,侵略中国东北的纲领性行动文件《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和《1931年度形势判断》已经下达,发动事变的班子已经组成,进攻时间表也大体定了下来。
但是,日本的陆军谋略家认为,中国军队的数量远远超过日军,日军仅在“满洲”一地进军作战怕难以保证在短期内占领并巩固偌大一块地方,反而会引来中国军队的驰援,因而必须开展谋略,钳制中国关内特别是南方的反日军队。
为此,军部第二部派出土肥原贤二去华北,拉拢石友三反对张学良,使他的军队不能回防;同时将号称“魔法军人”的田中隆吉从华北调往上海日本总领事馆,密令他在上海挑起一场“假战争”(有限战争)作为佯攻,策应陆军在“满洲”的行动。
田中隆吉一到上海,便通过军中的“樱会”要来“天剑党”(军中暗杀组织)的宪兵大尉重藤千春作助手,率领极右反华帮会“太平洋军团”、“在华青年同志会”成员秘密准备,拟在上海制造一起重大事件,挑起军事冲突。
考虑到发生一般问题不易激起日本本土反华仇华的狂热情绪,田中隆吉决定雇佣中国青红帮流氓暗杀重光公使,然后栽赃给中国,以此刺激日本内阁尽快批准出兵。
田中隆吉之所以要选重光公使作为暗杀目标,也还因为重光葵那时执行“币原外交路线”,反对使用武力,反对田中隆吉策动阴谋行动,主张以经济渗透的方式巩固和扩大日本在华的权益和影响,因而“成为他们计划的障碍”。此前,前任日本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便是因为执行同一路线而被军部暗杀,现在该轮到重光葵了。
扣留胡汉民激发“剌蒋”行动
日本特务在上海、东北紧锣密鼓地策划侵华阴谋,而中国此时却正在打内战、闹内讧。在年前的中原大战中,蒋介石打垮阎锡山、冯玉祥和桂系联军后,便张罗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企图借此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长期积集在国民党内部宁(南京)、粤(广东)两大派之间的争权夺利斗争便以“约法之争”的形式爆发了。
1930年11月12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交的召开国民会议案。会上,无人敢表示反对,只有当时任立法院长的粤系元老胡汉民起来激烈抨击蒋介石,引起蒋的极大不快。
1931年2月28日晚,蒋介石以“宴请议事”为名,将胡汉民扣留,软禁于汤山。于是,宁、粤两大派的矛盾立即激化。
孙科早就对蒋介石的独裁行径不满。胡汉民被扣留后,经过孙科的串连,粤派中央执委、监委纷纷提出辞职,离宁去粤。孙科、胡汉民的“再造派”、汪精卫的“改组派”、强山的“会议派”,以及唐生智、唐绍仪、李烈钧、陈友仁等人都到了广州,形成反蒋大联合。在那里,他们又成立了一个与南京同样名称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汪精卫、孙科、古应芳为常委,汪精卫为主席,同蒋介石唱对台戏。
蒋介石极为恼怒,欲杀胡汉民以示报复,这一来可急坏了胡汉民的老亲家林焕庭。他决定先行下手,邀李少川暗中疏通“暗杀大王”王亚樵,干掉“草头先生”(指蒋介石)以解救胡汉民。孙科当然更希望如此,南京政府如若“断梁”,广州的“国民政府”便可取而代之,这实在是“胜利的捷径”,于是便暗中赠予20万元作为刺蒋的代价。
王亚樵自1927年因杀戮上海工人一事与蒋介石闹翻以来,一直耿耿于怀,便一口答应下来,接受了孙科的巨款。
当时,蒋介石在庐山和南京两地轮流穿梭,王亚樵便在两地派人分别侦察。南京派去郑抱真,庐山由华克之负责侦察,并带金陵大学的学生陈成及刘刚作助手。郑抱真到南京后住在警察局张凤桐家中,很快就探知蒋介石要乘军舰去庐山,下榻太乙峰别墅,便赶回上海报告王亚樵。
郑抱真(1897—1954),安徽寿县吴山镇人,自幼父母双亡,家境贫困,依靠长兄郑绍成抚养,直到18岁时始破蒙读书,5年后辍学,随即投军。1924年,安徽国民党元老石寅生出巨资购买枪械,组成“淮上国民自卫军第一路军”讨伐北方军阀,郑抱真参加后任军需。l925年春,该军在奉军的进攻下失败,退入河南,被冯玉祥的西北军收编,郑抱真任少校副官兼兵站主任。1929年春,被军阀排挤打击的安徽志士在上海聚义,郑抱真接受余亚农(后为安徽省副省长)的邀请,去上海参加王亚樵所组织的秘密反霸团体“铁血锄奸团”,仍负责后勤军需,管理经费及武器。在活动中,他以思考缜密、办事敏捷著称,不久就成为该组织的核心人物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郑抱真参加了李宗仁组建的“皖北人民抗日自卫军”,出任第二支队司令。1939年初,他率部参加新四军,先后任江北游击纵队副司令等军政职务。1949年1月21日率第三野战军先遣分队进入合肥,任合肥市长,后转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1954年2月12日病逝,身后未留下任何回忆资料,只在病重时断断续续地向妻子李兰英讲述了1931年在上海时的反霸锄奸活动,这是后话。
当下,王亚樵闻报情况后,立即决定派人送武器去庐山,准备在那里动手。郑抱真设法把火腿挖空,将两枝三号花口手枪及子弹塞进去,外面再以肉末和盐泥封死,看不出破绽。
王亚樵将它交与妻子王亚瑛、表弟媳刘小莲二人带上庐山,交华克之使用。郑抱真本来要亲自送去,但被王亚樵挽留,命他用孙科付与的巨款张罗几间商店……
“刺蒋”失败改为“剌宋”

再说王亚瑛,她携带内藏枪支的火腿顺利到达星子县城,见到了华克之。在华克之的安排下,王亚瑛、刘小莲坐“滑杆”把火腿送上山,取出枪支埋在太乙峰前的竹林中待用,随后将不能吃的火腿丢在附近。那时,蒋介石的军统局尚未成立,但侍从室中有不少侦探。他们在巡逻中发现了丢弃的火腿,便起了怀疑,经检验又发现有铁锈与黄铜味,判断是有人用它夹带武器上山,乃引起高度警觉。
这一天,蒋介石在调兵遣将之余又到竹林中散步。担任狙击任务的陈成拔出手枪准备射击,此时早有警惕的侍从们匆忙簇拥着蒋介石折返回去。陈成惟恐失去机会,连连扣动扳机,两发均未命中。霎时间,侍从们乱枪还击,陈成立即中弹身亡。
事后,由于找不到证据,弄不到口供,蒋介石吩咐不要登报张扬,把陈的尸体掩埋了事。华克之撤退回来后,王亚樵安慰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但此时蒋介石已料到广州方面还会继续派遣刺客,加强了戒备,这种情势下,已经很难下手。
孙科领衔的广东反蒋派眼巴巴地望着好消息,心想一旦刺蒋得手便立即趁乱发兵,北上“统一”,登上领袖的宝座。两广的军阀已敲响锣鼓,分袭湘、赣,占领柳州、衡阳。同时,以50万元收买石友三,让他在北方进攻张学良,使之不能援蒋。但是过了许久仍不见动静,便派与王亚樵私交较深的萧佛成(粤系国民党中监委)、马超俊前来联系,再次送来4万元经费。
王亚樵据实以报,马超俊当即表示刺蒋不成,可改刺宋(子文),以杀鸡儆猴。宋子文是蒋介石的“输血机器”,刺宋成功可断绝蒋的财源,逼他下台。宋子文经常往来于宁沪两地,喜欢抛头露面,易于得手。
王亚樵认为此计可行,当即在大华公寓召开骨干会议,秘密布置。当时,宋子文任行政院财政部长兼外交委员,家住在上海西摩路14l号,每逢星期五自宁返沪度假,到下周星期一再去南京上班。
郑抱真已探知他的行动规律,提议在上海北站趁旅客上下车混乱之机动手,然后施放烟幕撤退。王亚樵同意这一计划,成立了南京与上海两个刺宋行动小组,南京仍由郑抱真负责,组员有张四明、张慧中、华克之等人,住仙鹤街的余立奎(时为广东政府委任的第十七军军长)在家中待机;上海方面有组员孙凤鸣(1935年刺杀汪精卫时身亡)、刘刚、萧佩伟、谢文达等人,由王亚樵亲自指挥,每人各发手枪1枝、子弹10发,并在北站附近的天目路租赁三层楼房一幢,供行动人员集中休息。王亚樵指令郑抱真设法从日本浪人处购买烟幕弹,以备撤退之用。
一切预备停当,两个刺宋小组分别在上海和南京等待时机。
同日本浪人做生意
郑抱真来到八仙桥和平米店张罗购买烟幕弹。这家米店是他从孙科赠款中抽出18000元顶下的,专事经营淮北船帮贩运到上海的粳米,赚钱供“铁血锄奸团”开支。他是这里的“老板”,收了几名“徒弟”支撑门面。其中有一人绰号“小泥鳅”,浙江人,极活跃,善交际,郑抱真用他为助手。此人凭着他的机灵钻进虹口亲日青红帮中,与日本浪人有秘密来往,因而便托人去购买所需烟幕弹。
“小泥鳅”去后不久,就弄来一枚日本浪人秘密制造的烟幕弹,代价800元,这在当时已是不小的数目。郑抱真问他来路是否可靠,他答:“有常玉清家门的徒弟作中人,出错可以找他去算账。”
他们说的常玉清,是上海滩著名的流氓地痞、杜月笙的头号门徒,在上海公共租界泥城桥开设一家“大观园浴室”(变相妓院)。他充当日商工厂的工头,经常在日本浪人的庇护下,利用黑势力杀人越货、制造事端,工部局曾悬赏20万元缉捕,终因有日军为靠山,未能捕获(战后此人被处决)。
郑抱真已有风闻,常玉清一伙要在日本特务田中隆吉的策动下搞点什么行动,便提醒“小泥鳅”说:“最近虹口来了不少日本黑帮,来者不善。要多跟他们打交道,趁机探听些什么,如有情况立即报告!”
“剌宋”情报与青红帮的
“特别行动”
郑抱真将买到的烟幕弹交给王亚樵后,就去了南京。在南京,他买通了财政部的一名主办会计,让他常秘密传递宋子文的情报。这名会计每天都要当面向宋子文汇报外汇市场的行情,宋子文每有行止都会向他打招呼,所以情报极准。
7月22日,宋子文对他说,接青岛电报知悉母亲病重,拟于当晚回沪打点,不日去青岛,所以一周之内停止办公。
郑抱真获情报后,立即给在上海的王亚樵发去密语快电:“康叔准于22日晚乘快车去沪,23日到北站,望迎接勿误。”暗示宋去沪后及时动手。
郑抱真发完电报,刚刚回到住处,便遇到从上海专程来报告情况的“小泥鳅”。他急切地说:“我探到了日本特务的计划,很紧急……”原来他在买到烟幕弹后,顺便探听到了常玉清正在和田中隆吉组织一次“特别行动”。
“小泥鳅”购买浪人的烟幕弹时发现,他们那里还有两枚同样的烟幕弹。经套话才知道,田中隆吉已雇佣常玉清在上海北站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然后嫁祸给“铁血锄奸团”。
他们探知,重光葵把办事基地放在上海总领事馆,每周到南京公使馆办公一次,按时往返,已成规律。他在南京主要是同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打交道,也和外交委员宋子文有密切来往。二人来往宁沪时间大体一致,所以经常同乘一列车尾挂花的车,到沪停车后待一般旅客走光才下车。他们常肩并肩地走到出口处,在那里还要彼此谦让一番才出站。
他们认为,这是行刺的最好时机,安排在此时下手万无一失。得手后,施放烟幕弹撤退,同时故意在站内外丢下武器及写有“斧头党”(“铁血锄奸团”前身)字样的未响炸弹,嫁祸给王亚樵。这样一来,中国人就必须承担事端的责任,日本陆军就可以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萨拉热窝事件”一样,“名正言顺”地兴师问罪了。
“小泥鳅”还了解到,常玉清已经知道宋子文23日返沪,拟届时狙击。他在上海找不到王亚樵,没法报告,便只好找到南京来。
郑抱真听了报告,感到问题十分严重。这事情太巧了,明天(23日)宋子文返沪,重光葵也返沪;明天王亚樵行刺(宋子文),常玉清也行刺(重光葵)。如果王亚樵按照自己的密语电报所示准时动手,那么正好为常玉清刺重光葵作了掩护,并为日本特务的栽诬留了空隙,有口难辩。如果由此而引起中日两国武装冲突,王亚樵就会成为万世唾骂、洗刷不清的民族罪人。如果停止刺宋,则怕是箭在弦上,撤不回来了。
华克之主张立即拍发一份加急电报,暗示情况起了变化,郑抱真认为不妥:万一王亚樵未能及时看到怎么办,(因为他在上海的住处极秘密)万一泄密怎么办?
二人商议到最后,郑抱真毅然决定:搭乘当晚快车与宋子文、重光葵同车去沪,到达北站时,抢在宋子文与重光葵出车厢之前对空鸣枪,给宋与重光发信号,叫他们勿出车厢,破坏常玉清的行刺计划,同时也通知王亚樵撤出战斗。至于刺宋,能成则成,不成则罢,事后再向王亚樵解释。无疑,这是一个巧妙勇敢而又富于正义的“紧急措施”。
南京刺宋小组一致同意这个措施,郑抱真便去购票抢搭当夜快车。
双方都在云雾中
在上海的王亚樵接到密语电报后就作了周密的布置:他亲自率领张四明、孙凤鸣、萧佩伟把守北站月台迎击;龚春圃率刘刚、龚林、唐明、李凯、彭光耀进入候车室堵截;谢文达率黄立群、刘文成、陶惠吾在车站外马路上接应,各守一段,各负其责。当然,他没有料到还有什么帮派在打另外的主意。
为了不致引人怀疑,王亚樵让这些人扮作旅客,连夜守在候车室内,事实上如果郑抱真发来停止执行行动的电报,王亚樵也很难及时撤出全部人马。
就在王亚樵紧急指挥的同时,常玉清也率领人马来到现场作了部署。他在重光葵有可能进入的贵宾室门前配置两名化装成杂役的刺客,待机而动。在出口处,他作了重点布置,他安排两名擦皮鞋的小瘪三监视列车,及时发出重光公使是否到站的信号;另两名化装成旅店侍者,混在群众中按信号行刺;在马路边沿铁栅栏处隐匿二人专司“栽诬”。一旦得手便悄悄丢下事先准备好的包裹,内藏一枚手榴弹并附一纸,上写“斧头党专炸日本人”。
火车到来前,常玉清特别交待监视的人要注意刺杀对象的特征:重光葵历来都和宋子文并肩走出车站,在出口处看到与宋子文谦让的人便是重光葵无疑,下手勿迟!当然,他也不知道王亚樵那边做了行动,更不知道郑抱真的“紧急措施”!于是一场巧合的“错中错”好戏便等着开台。
重光葵的“官脾气”救了命
重光葵和宋子文所乘车厢,是一节挂在列车尾部的“花车”,只有他二人和随员。重光葵带的是公使馆书记官堀内干城和林出贤;宋子文带了6名贴身卫士和机要秘书唐腴胪。唐32岁,10年前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得硕士学位,刚刚结婚不久,此次专程陪宋回沪,听候调遣。
说来也巧,每次重光葵与宋子文乘这班车回上海,都是在列车过真如站后,列车员才把熟睡的贵宾唤醒。偏是在这一天,列车员鬼使神差,在比往常早得多的时间叫醒了重光葵。这位公使大人美梦正甜,被扰醒后看看时间还早,便发起了官脾气,索性穿好衣服起来大骂特骂,愈骂愈气。每次,他都是邀宋子文一齐下车,而这次,车刚停稳他便跳了下来,连招呼也不打,径自走向出口,混在人群中走出月台。这似乎是故意做给宋子文看,以示抗议,但迷惑了常玉清布置的刺客和车上的郑抱真。
担负监视任务的小瘪三,还在等待着与宋子文并肩而行的重光公使,想不到他已经轻装简从到达门外,上了汽车。车厢里的宋子文看到重光葵呕气的架式,感到过意不去,便没等众多旅客走光,就赶了上去,希望作点解释,因此也杂在人群中。
这时,守在车厢中待机的郑抱真、华克之,还在等待旅客走完再发出信号,以免误伤无辜,不料忽然看到宋子文已经走近出口,眼看就要进入常玉清的狙击圈内,似乎重光葵就在他身侧。郑抱真感到形势危急,便不顾一切跳出车厢,对空鸣枪,以示警告。
此时,宋子文的卫士听到枪声便拔枪还击;王亚樵布置的孙凤鸣、萧佩伟等人看到郑抱真信号还以为需要支援,便与卫士展开枪战,一时间站内站外子弹横飞。
枪响一刹那,宋子文正在出口处。此时同他并肩走的不是日本公使,而是机要秘书唐腴胪。唐身披雨衣,手持日式黑色公文皮包,又与宋子文“肩并肩”,这在专司情报的人看来,无疑就是“重光公使”,遂发出“目标已到”的信号,于是混在人群中的常玉清刺客立即趁乱集中射击这位“重光公使”。
唐腴胪连中3弹,倒在血泊中不醒人事。常玉清见已击中“目标”,便示意撤退,此时华克之已令孙凤鸣掷出烟幕弹撒出战斗,无异于掩护了常玉清。常玉清还在乱中丢下事先备就的“栽赃物”,后来据报,在排除该物时伤了三四人。
事后,宋子文自己谈的情况与实际情况大体一致。他说,“尽管高而未受丝毫之伤,殊属不可思议”。他哪里知道,“醉翁之意”根本不在于他,而在历来同他肩并肩下车的人。他又说,“予先曾屡得警告,谓广州方面将不利于予”,岂不知开枪的不只是“广州方面”,同时还有“友好公使”方面的人。
重光葵大曝“遇剌”内幕
退出现场后,常玉清也不知道这次行动为什么会如此顺利,连个蛛丝马迹也未败露,待他到了虹口东华纱厂内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见到在那里坐镇指挥的田中隆吉,才知道王亚樵“掩护”了他们,而他们击中的是唐腴胪,根本不是重光葵。
田中隆吉非但不给事先答应的2万元,反而要找他的麻烦。常玉清不敢违拗日本主子,只好答应另外挑选谋刺对象以挑起“中日冲突”。
后来,他果然带人化装成三友工人,杀死日莲宗和尚,制造了“一·二八”事变。
王亚樵布置的人虽多,亦无一人被捕受伤,但他以为唐腴胪是被自己人误伤,埋怨郑抱真、华克之不事先通知他。同时他也怀疑过:常玉清从不抛头露面,这一天怎的偏要去北站?自己的人只顾同卫士抢战,怎的唐腴胪会中弹?带去烟幕弹已经用完,怎的站外会有未响的炸弹?他一面吩咐行动人员去香港避风头,一面托人暗中送唐家1200元,以宽内疚。于是,这一谜案就“将错就错”传了下来。
但是,侥幸身免的重光葵很快就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当天,他去宋子文和唐腴胪府邸慰问,就满怀着“替我受难”的感激情意。过后不久,发生了“一·二八”事变,田中隆吉在反华得手后竟然得意忘形,向林出贤书记官透露了那次行刺的内情。
战后,田中隆吉又亲口对重光葵说了实话,向他道歉。这时重光葵才知道“同这一计划会合到一起的,还有田中隆吉的阴谋,他们打算是要把致力改善日华关系的自己和与他共事的宋子文一起杀害”。他的《外交回忆录》中阐明事件始末。
至此,这幕国际性的“错中错”行刺疑案的真相终于大白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