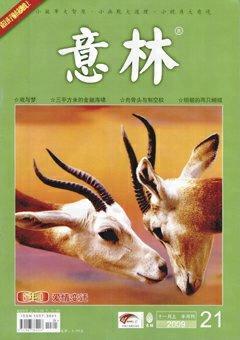超短篇三则
2009-05-14 16:48朵拉
意林 2009年21期
朵 拉
窗外有光
是呼呼的风声把她吵醒,坐起来,房里一片黑暗,只窗口边有一点光。“真是风声吗?”她怀疑。而且她已经忘记,临睡前,是否曾把窗关上了呢?
每次她疏忽了,男人也会帮她关上的。他一直是那样照顾她,疼爱她。
因为窗口的一点光,反而令她感觉害怕。那是什么光呢?是不是坏人半夜作案时,拎着手电筒发出来的一丝光线呢?
她再也睡不下,睁大眼睛,侧着耳朵,静静地听。
窗外似乎有人影在晃动。
“不!”她喊起来,想转身去摇醒身边的男人。
这时,她才蓦地想起,男人已经搬出去两天了。
于是,她就哭起来,不管窗外是否有人,是否有光,她像个耍赖的孩子,大声地哭泣。
迟来
团员纷纷懊恼地埋怨:“早一点就好了。”
深浅浓淡的红密密麻麻铺了一地。
“好丑。”他心想,一脚踩上去,毫不怜惜。
树上的樱花零零散散,风一吹,又再一点一点地飘落。
他远远地看她,隔着许多花落了以后的秃枝,她和另一个他微笑地观赏树上剩下的数串樱花。
初识,还在念书,爱慕和热切像朵花蕾,未绽放,已经毕业。
再重逢,竟是多年后的今天。
风吹,花落,一切都无法掌握。
“咦,你看,落在地上的花,也有它的漂亮呢!”太太什么也不知道地唤他。
占有欲
她手上戴有一个男装手表。
“是她丈夫的。”
“就是那个建筑业大亨。”
“是的,他已经去世三四年,她还一直戴着。”
“她很爱他吧?”
“也许。不过,听说这手表是另外一个女人送他的。”
“啊!婚外情!”
她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说:“是的,是我去世的先生的。是的,我爱他。”
她低头看手上的表,脸色阴冷,声音坚决:“无论生前死后,他所有的时间,都是属于我的。”
记者一看,手表上的长针和短针,都已经停止跳动。
(明月摘自《文汇报》2009年9月3日图/郑钧)
猜你喜欢
儿童故事画报(2021年4期)2021-08-03
中学生数理化·七年级数学人教版(2017年9期)2017-08-15
金色年华(2016年23期)2016-06-15
火花(2016年7期)2016-02-27
少儿科学周刊·儿童版(2015年11期)2015-12-17
故事林(2007年18期)2007-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