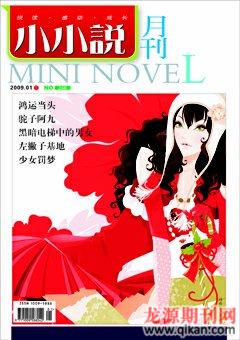驼子阿九
刘吾福
一九七二年,我下放在葫芦坳。
葫芦坳有一个放牛倌叫驼子阿九。驼子阿九光棍一条,人长得矮小,又是驼背,做不得田里的功夫,加上他祖辈三代全是贫农,生产队就照顾他,让他放牛。
因为我当时下放的时候才十五岁,身子骨单薄,又不会做农活,生产队就安排我跟着驼子阿九学放牛。
放牛其实不需要什么技术,只是早晨把牛从山里吆喝回来。惟一操心的是要紧盯着牛们,不许它们跑到田地里偷吃庄稼,如果不小心,让牛们偷吃了生产队的禾苗或者玉米叶。那是要扣工分的。
驼子阿九放了一辈子牛。很有经验,他叫我一起把牛们赶到野猪垅,野猪垅三面是山,悬崖峭壁,再调皮的牛也爬不上去,另一面靠着国道,国道上汽车来来往往,吓得牛们也不敢过去。
这样我们就很清闲,也很舒服。
我们把牛赶进野猪垅,然后驼子阿九就带我爬到山上摘野果子吃。或者躺在大树底下聊天,或者听驼子阿九唱山歌。
最有味道的是听驼子阿九唱山歌,驼子阿九似乎只会唱一首山歌,就是《十二月选郎歌》:
正月里来好选郎,
一选选到个癞子郎,
好像那石灰打秧塘,
哎呀我的娘——不喜欢!
……
三月里来好选郎,
一选选到个跛子郎,
好像那锥锤进碾房,
哎呀我的娘——不喜欢!
……
我问驼子阿九为什么不唱“二月里来好选郎”那一段。驼子阿九说,那一段呀,难听死了,所以就不唱呗!我又追问“二月里来……”那一段歌词到底怎么个难听,驼子阿九便支支吾吾不说了。
有时,驼子阿九还叫我猜谜语,驼子阿九的谜语也不多,而且很土,比如,“天上掉下一扇磨,皇帝老子也不敢坐。”
我猜了老半天也没有猜出来,驼子阿九就笑,还是个知识分子呢,连这个谜语都猜不出——牛屎呗!
看着盘在地上那一堆堆黑咕隆咚的牛屎,果真像一扇一扇的石磨,我忍不住笑了。
到了中午,驼子阿九拉着我的手说,走,到供销社喝酒去!
听说有酒喝,我很兴奋,跟在驼子阿九的屁股后头就走。
我们到供销社门口,就看见倚门框站着一个约摸七八岁的小丫丫,脸色惨白,驼子阿九问那个小丫丫,小麻雀,你爸呢?
小麻雀说,在屋里头。
循着驼子阿九的声叫着,小麻雀的爸就出来了。
驼子阿九高声叫着,老曹,老曹!
老曹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白净的脸,很文静,像个知识分子。
看见驼子阿九进来,老曹白净脸闪出一片红晕来,老曹说阿九来了?喝酒,喝酒!
老曹就手脚麻利地从柜台后面的酒坛子里舀出两大杯散酒来,又抓了几碟子麻花根,狗耳朵瓜片,还有红姜,萝卜丝。
驼子阿九也不客气,端起酒杯就往嘴里灌,然后用手撮起碟子里的麻花根扔进嘴里,就听见驼子阿九的嘴里发出“嘎崩嘎崩”的脆响来。
驼子阿九一边吃,一边招呼我,吃吧,吃吧!好像是在他自己家一样。
不大功夫,驼子阿九的杯子就见了底,老曹又给他舀了一杯,驼子阿九“咕噜咕噜”把它喝干了,一抹嘴巴说,多谢了,咱还得招呼牛去,不然的话,灾牛鬼跑进田地里吃了庄稼,生产队扣我几天的工分,你这顿酒就是等于是“牛婆嚼胎胞,嚼到自己的白喝了”。
驼子阿九便红着脸歪歪斜斜地从供销社出来了,我说,阿九叔,那顿酒还没找钱呢!
驼子阿九说,找什么钱?在老曹这里喝酒不用找钱!
我便问,你跟老曹是亲戚?
老曹摇摇头。
我再问,驼子阿九就说,老曹哇——他欠我的。
驼子阿九说,有一次,我在野猪垅放牛,我正在一棵林树下睡觉,突然听见不远的树从中发出响声,开始我以为是一只野猪或者麂牯什么的,我捡了一块石头走过去,那声音就没了,后来从树丛里钻出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就是老曹……
女的呢?我急切地问。
驼子阿九摇摇头,没有回答我,驼子阿九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其实,老曹这人过得也不容易啊——老婆患肺痨病躺在床上,那个女的呢,二十几岁了还像一只小麻雀……
那怎么说老曹欠你的呢?
驼子阿九又不作声了,驼子阿九钻进一丛树棵子里,我听见那里发出“哗啦哗啦”的流水声。我知道那是驼子阿九在撒尿。
我把这件事跟生产队的阿华说了,阿华告诉我,和老曹在树丛里睡觉的那个女人就是葫芦坳的寡妇春柳,而驼子阿九一直在追着寡妇春柳呢!
哦——
后来,我和驼子阿九还去供销社喝过一回酒,这一回,驼子阿九连喝了五杯酒,醉得十分厉害,是我搀扶着驼子阿九回到野猪垅的,临走的时候,驼子阿九对老曹说,你放心吧,以后我再也不会来你这儿喝酒了。
到了山上,驼子阿九没有睡觉,他站在高处,扯起嗓子声嘶力竭地唱“十二月选郎歌”,突然唱出了“二月里选郎”那一段:
二月里来好选郎,
一选选到个驼子郎,
好像那畚箕扑上床,
哎呀我的娘——不喜欢!
我终于听到驼子阿九唱出了这一段,驼子阿九唱这一段的时候,好像在哭,他的眼睛不断地往山下的小路上张望,我顺着驼子阿九的目光往山下的小路看去,我看到一个穿着红花袄的女人正朝着供销社的方向走——
那就是葫芦坳的寡妇春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