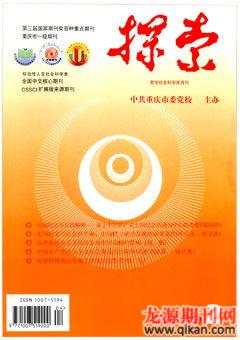社会疲态下的暴力危害与民主救治
任剑涛
摘要:近期中国出现了局部的社会动荡现象,这是中国社会显现疲态的表现。如何解决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个人群体与国家之间的暴力冲突现象是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有必要深入解析导致社会不安的诸种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分析这些事件,凸显出民主救治方案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社会疲态;暴力事件;群体;国家;民主
中图分类号:D089;D621;C912.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2-0052-05
2008年我国发生了多起群体性暴力事件,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湖南湘西事件、广东深圳事件和甘肃陇南事件。这些事件大致都由几乎同样的原因导致:政府与民争利、执政水平较低、社会公平失衡、群体心态扭曲。
这些群体性暴力事件加上一些零星的暴力事件,比如上海刺杀警察的事件,此前发生的邱兴华、马加爵杀人事件等,足以让人震撼。而非暴力的群体性事件也频繁出现,如辽宁的蚁力神事件、北京的抗议不公拆迁,三亚、大理、重庆、广州的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也使人浮想联翩。难道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暴力事件频发时期?改革开放的中国为何呈现这样一些不安定的状态?这是一些不足以让人判断中国局势的偶然事件吗?抑或是中国进入一个危险的、不安全时期的信号?显然,这需要解读,理应分析,亟待疏导,必须救治。从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宏观历史处境审视相关事件,我们可以从中获得理解当代中国状况的重要信息。
一、社会:从活力进发到显现疲态
求解频仍的群体暴力事件,需要从中国社会状态的结构变化人手。
1978年以来的中国,是一个依靠改革开放提供社会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缓解社会矛盾和促使社会凝聚的国家。改革使人们看到了告别贫困状态、迈向丰裕生活的希望。心怀的希望鼓舞人们坚毅地前行。所以,1980年代的中国人才敢于、乐于接受改革的种种挑战——农村承包责任制就此登上改革舞台,城市居民以个体户的谋生抛弃了依赖国家和集体的僵化生活模式,国家权力以高度的自信推动着总体改革进程,中国社会体现出鲜明的发展态势和蓬勃的上升气象。人们的社会体认无疑是积极的:GDP持续而迅猛地增长,为人们感受财富的价值提供了强劲的刺激;各种改革举措的出台,为人们向上流动提供了强烈的希望;国家力量的强化与公民个人生活质素的改善,为人们积极谋划未来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开放,使中国处于一个八面来风、应接不暇的活力四射状态。活力给人们以“明天会更好”的激励。中国的发展一时被认为是世界总体进步的机会。中国的无限商机和社会的蓬勃朝气,既让中国人自己受到空前的鼓舞,也使发达国家对中国侧目相看,更使发展中国家受到激励。对此,我们可以从“中国机遇论”、“中国威胁论”到“中国模式”、“北京共识”这一类国际流行的、关于中国的主流词汇的演变上,捕捉到一些信息。只有在改革开放促成的发展奇迹中,国际社会才会对中国具有如此的热情,不论这样的激情来自负面的刺激,还是来自正面的认知。
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处于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性局面,因此改革的一波三折也就在情理之中。1978年启动的改革,在1980年代遭遇了1986年的动荡和1989年的重大波折。1990年代后期以来,改革开放的一些方面就一再处于钝性迟滞的状态——改革开放依然还是社会政治号召最强有力的辞藻,但全国上下对于各项改革的共识逐渐减少而分歧逐渐加大。各项改革的关联程度愈来愈低,人们很难捕捉改革的整体思路。1980年代那种势不可挡的改革气势和冲击力也逐渐软化,维护稳定成为政策的优势选项。曾经积极地从总体上谋划改革的行为主体不得不愈来愈被动地应付各种社会事件、群体骚乱,对于改革本身的谋划似乎缺乏时间和精力。一些改革处于散打的状态。曾经给改革开放以最大精神动力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不再充盈社会。相反,市场经济的普遍牟利取向,成为人们计算改革还是不改革的标尺。改革的深度问题被掩蔽起来:从经济体制肇始的改革似乎就停留在经济领域,难以向社会、政治领域的纵深推进;即使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在产权问题、用人制度、体制激励等问题上也少有作为。改革的回流现象为人们所悲壮地体会:因为深层次的问题难以触动,因此经济体制在一些方面愈来愈集合起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共有缺陷,国家带动的发展在一些方面越来越成为寡头的主宰。一些国有垄断的市场巨无霸,甚至开始挑战主导市场的政治巨无霸。人们眼看着改革在不少方面的软化而无能为力,对于改革的未来期待也就越来越软化,以至于改革无法积聚起足够的社会动力。
由于上述原因,一度活力进发的中国社会日显疲态。一些人对什么都抱以一种无所谓的态度,生活处于一种懒洋洋的状态。于是,民族精神的积极力量在很多地方无所表现,而民族精神的消极涣散力量则开始发酵。各阶层集团开始区分为并自主地为自己谋求社会空间。几十年的物化引导,将人们的高尚感消磨殆尽,日益低俗化和向下看齐的精神状态出现了,人们关注的是自我。除开偶发性地以网络暴民的形式发泄一下国家感情之外,实际的政治生活是人们难以参与的事情。同时,社会消耗人精力的日常生活手段的陈旧单一,使人们无从发泄剩余精力。这个时候,慵懒的生活状态更使人们缺乏关注一己之私以外的社会公共事务的情绪。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多方面都呈现出疲态:经济上,内外动力耗散而进入困难时期;政治上,缺少国家认同的感召而出现不少散漫的族群;文化上,各行其是而缺乏共有的精神家园;社会领域,被各种民生问题所困扰的人群容易出现茫然行为……
二、社会疲态下的暴力危害
从现实生活状态上来看,社会的疲态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方面,精神上凝聚、鼓舞人心的观念缺乏。当代中国以改革为自己画像。但当改革共识流失、改革效果递减的时候,改革已经不足以整合起刻画中国形象的资源。因此,改革曾经提供给人们的激越感正演变为人们对一些改革进行“讨伐”的不满。本来改革是当代中国的宿命,从国家当局到社会大众围绕改革才足以凝聚起来。但一些改革被认作中国相应社会问题的导因之后,改革就成为人们发泄不满的对象。这时的一些改革措施反而变成错误的政策选择和糟糕的社会状态。于是,眷恋改革前的社会状态者大有人在,他们理直气壮地以这种眷恋作为号召人们抵制改革的精神资源。但是,这些抵制改革的情绪只不过给人们提供了替代令人不满的现实的手段。即使如此,人们精神上并没有改革初期那种向往未来的满足感,精神上的空虚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国家意识形态的号召力与感染力不足,加上国家意识形态人格载体的老化,它对人们精神空虚的治理效力就大打折扣。现代主流意识形态被排斥,人们以对其进行“隔山打牛”的批判为快,这使它实际上难以发挥积极效用。各种非主流
的现代意识形态与传统意识形态纷纷登台,以争夺人们的眼球为目标,它们对于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实在没有阅读其文本具有的快感那么有效。真正紧扣中国社会改革需要的精神建构尚待时日,这使得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虚无情形愈加严重。
另一方面,制度上公正的政策供给明显匮乏。经济体制改革是以敢字当头推进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两种效应。国家的分配政策一度是让公平屈从于效率,社会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改革开放推动中国迅猛地发展,同时却形成了三重意义上严重对峙的“两个中国”:一是农村“中国”与城市“中国”,农村的故步自封与城市的惊人进步好像二者不在一个国家;二是西部“中国”与东部“中国”,使人觉得被区隔为发达国家和贫穷国度两个世界;三是富裕“中国”与贫穷“中国”,其鲜明对照让人想起杜甫的著名诗句。国家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是制度改进的严重障碍,因为制度改进大都只能在公众相对一致地赞同这一改进的基础上才能有效进行。正是在这种制度运行的平台上,当代中国日常生活对紧张和松弛的模糊,严重消磨着人的斗志,造成人们对什么都怀抱一种无所谓的消极态度。这就更进一步消耗着改革的社会心理资源。
再一方面,从中国社会的活动主体来看,中国社会的疲态也明显地显现出来:由于深度改革的客观困难和改革者处于改革自身的艰难情境,这样的主客观状态,使得一些地方和基层的官员群体不思进取,陷入既不主动改革也不被动投入的疲乏状态。改革者在改革初期那种迅速凝聚社会改革资源的“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冲劲,在他们身上似难再续。在这些地方,曾经使官员群体叱咤风云、引领国家发展的改革精神退隐到稳守官位的看客心理之中,而宽容改革者失误的领导哲学也让位给不容分说的责任追究,曾经激荡中国的改革共识首先在这些群体中丢失了。于是,像当年马胜利那样冒险承包国有企业的创新性企业家没有多少,而享受及至吞噬国有资产的人倒是多了起来;像胡福明那样撰写文章吁求改革的学者没有多少,而谋求个人名利的学者教授倒是多了起来;像当年的下岗工人那样积极谋求出路即使干个体也敢当的没有多少,伸手向国家和社会索取且不感到任何羞愧的人倒是多了起来;像当年的被征地农民那样积极支援国家建设的明显减少,向政府讨价还价的“钉子户”,与一些严重侵害被征地农民利益的“政府行为”倒是共同多了起来。不是说国家没必要改善制度和增进福利,这里申述的是一个疲态显现的社会的活力缺失,以及这一缺失带给国家深度改革的消极影响。
疲态显现的中国真是缺乏刺激人神经的人与事,但社会不是不需要刺激,因此暴力活动就会在疲态严重的地方成为号召人们行动起来的刺激因素。更为严重的是,在各种暴力事件发生之际,人们对于暴力活动的谴责显然弱于对暴力活动的欣赏。这是社会的悲剧——连杀十人的恶性杀人犯邱兴华竟然博得广泛同情,受害人家属没有一个人给寄上慰问金,而邱兴华家居然收到很多慰问金;而马家爵砍死四位同窗,没有受到应有的道德谴责,反而一下子被人们推向了制度问题。这是一种社会疲态下缺乏道德判断能力,而仅仅只能在刺激中满足浮浅议论导致的必然结果;这是一个社会缺乏正义感而加重人们是非不分、对错不明的失范状态的必然后果。当单纯的同情取代了公平正义的道义感的时候,暴力就受到人们的礼赞。因为这中间生活着的一些人发现不了和平地实现正义的途径,因此横刀立马、揭竿而起、杀富济贫,居然成为他们认为的天经地义的“选择”。至于真正安定社会的法治秩序,这种真正有助于社会建立起道义状态的制度保证,在这些人看来已经成为特权阶层压制普通民众的工具。这个时候,暴力既危害着人们的道义神经,也危害着社会的法治取向,更危害着人们的社会认同,进而瓦解着人们维护社会正义的人心秩序。一种颠覆性的社会心理获得了影响整个社会的契机。当这些人看不到社会活力、社会改善的希望时,对现实的不满聚集起来的失望与绝望,就会逐渐吞噬他们改变现状的耐心,就会逐渐走向社会的群体暴力反抗,进而演变为不约而同的暴力发泄,这就必然使得人心秩序混乱的同时,社会秩序被瓦解,改革发展被搁置,而反抗所寻求解决的问题依然得不到任何解决。
三、疏导群体暴力的三种选择
我们绝对不能简单将这些似乎不相关联的偶发性群体暴力事件视为个案,而忽略背后的相关性导因。只有理性处理这些暴力事件背后的共同社会导因,暴力事件才不至于以不同的方式和面目不断地出现。审视中国近期暴力事件一个优先的视角是,暴力的集中累积途径有哪些?其次一个视角是,有效解决这些暴力事件究竟有些什么制度选项。
从第一个角度看,明确群体暴力事件的累积状况,需要先行明确群体暴力的表现形式。群体暴力表现的方式有硬暴力和软暴力两种,而暴力的表现主体可以区分为国家的与民间的两种暴力载体。国家的硬暴力就是国家使用军队、警察、法庭、监狱这些高度组织起来的暴力机器,对社会进行刚性控制。对于现代国家来说,硬暴力是国家之成为国家的刚性制度保障,但如何将硬暴力使用得当,则是一个难题。在法治秩序缺乏保证的情况下,社会出现无序反抗的情况,基层政权就可能借助于国家硬暴力来对付。这时,警察就被安置到了对抗的位置上,参与群众乃至社会舆论对于国家硬暴力的对抗情绪也就相应强化。一旦矛盾激化,对于军警的攻击就成为平常对之无可奈何的情绪激奋者的选择。此时,打、砸、抢、烧的情况就会出现。
在官僚主义盛行、官商勾结存在的地方,会出现官方软暴力:一些官员借手中握有的强制权力,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群众,不但体现为不屑与群众对话的颐指气使,更体现为遇事就指责群众素质低下而从来不自我反省的定势。这种软暴力,使得其地方政权与社会、与群众之间处于一种隔绝的状态,彼此之间的了解趋近于零。因此在日常隔绝之外发生短暂的冲突性接触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彼此埋怨的状态。群众不知道怎么将自己的冤屈向政府诉说,政府也不知道怎么将自己的意图传达给公众。当没有什么因素足以激发公众采取群体暴力的时候,大家就这么彼此不理解地相处着,忍受着彼此的软暴力、活折磨。一旦彼此的积怨只好借助群体暴力的形式得到舒缓的时候,硬暴力便不请自来。
由于硬暴力与软暴力不时错位地浮现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因此暴力因素难以得到有效缓和。这就使得暴力逐渐有了一个累积的过程。这种过程的一般趋势是从软暴力到硬暴力的演变。这样的状态日积月累,会使政治商议和妥协的可能性荡然无存。这时,硬暴力现象就可能出现。硬暴力现象本身也有一个累积过程:从零星表现到偶发性群体表现,从偶发性群体表现到恶性社会暴力事件的出现,从个案式的恶性社会暴力事件演变为经常性的规模化暴力活动:如果说改革开放在其前20年显示的活力消解了社会的暴力倾向,因此注定了暴力的零星性,那么,近10年由于社会处于转型的艰难时期,社会
矛盾的日益浮现与国家治理的艰难跟进突兀地结对出现,因此,群体暴力事件的规模性爆发,也越来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频繁地出现。群体暴力具有示范性——人们在群体暴力中既发泄了不满,又舒张了身心,更逃避了惩罚。因此,群体暴力常常伴随社会困难一起出现,两者携手,将给社会带来明显的动荡,既使国家治理艰难无比,也使公众缺乏安全感,更会使社会进步成为泡影。
因此,从第二个角度即从有效疏导群体暴力的角度看,今天中国已经到了必须慎重选择疏导群体暴力的关键时刻。如果任由群体暴力从零星绽放到规模爆发这样的趋势蔓延开来,那么改革开放所形成的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局面就很可能被断送,中国的发展就会在经济增长的高企阶段夭折。为此,分析并清楚把握疏导暴力的诸种形式就很有必要。一般而言,现代国家疏导群体暴力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消极对付,二是积极治理。
消极地对付群体暴力,是一种国家治理中“击鼓传花”心态必然的产物。这种心态使各级官员与社会公众怀抱一种轻松快意的心情看待群体暴力行为,以为这些暴力行动仅仅是零星的,不足以引发规模化的社会反响,因此作为绝对个案来处理。这种心态驱使当事官员掩盖事件,促成上级官员误判局势,引导公众沉溺于满足现实的乐观情绪之中。当社会矛盾尖锐时,会使得群体暴力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
积极地救治群体暴力,是一种现代社会诊治群体行为暴力病症最值得提倡的进路。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因此国家治理与社会安顿需要高超的平衡技艺。能够达到国家、社会与市场之间的平衡状态,社会就得到安宁,市场就实现繁荣,国家就必然昌盛。这就需要国家承认社会总会存在令人不满的现象,承认社会是需要随时关注、疏导和治理的,任何掉以轻心地对付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社会就会翻转过来给国家安宁造成威胁。于是,国家建立起制度化的民主法治框架,以制度功能化解社会不满,以民主建制疏导群体暴力,就成为积极应对群体暴力最有效的举措。民主法治的国家不是没有群体暴力,但其发生的频率不会太高,出现的范围不会太大,社会危害程度受到控制。
四、以民主机制对治群体暴力
为了维护中国得来不易的发展局面,在改革开放处于十字路口的当下,面对频繁发生的群体暴力,应当抓住根本,真正建构起从社会基本制度上救治群体暴力的机制。这一机制,就是最有利于疏导和治理群体暴力的民主机制。在今天,中国人已经共同意识到群体暴力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面对群体暴力,缺乏的不是认知,而是行动;应对群体暴力,缺席的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治理群体暴力,缺少的不是举措,而是制度。归根结蒂,除非建构起民主法治的健全制度,群体暴力就总是处于潜蜇和爆发的两极状态,无法将群体暴力消融在社会的正常制度安排范围内。
为什么民主成为对治群体暴力的根本制度选项呢?这需要从现代两种国家制度的比较效果,以及民主自身具有对治暴力的双重功能上加以说明。
现代国家的制度选择可以有多种,但大致是在极权与民主之间。一个国家选择民主制度,多半基于两种情况,一是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或决断时刻自然而然步入民主的轨道,二是一个国家在非民主的制度轨道上实在走不下去,因此非成功实现民主转轨不可。现代比较政治学表明,在维护国家基本秩序的制度功能方面,极权政治一时所显现的统治功能甚至优胜于民主政治。极权政治以高亢的道义煽动为集纳政治资源的基本方式。因此,在一个社会亟需热情以对治萎靡的时候,极权政治比民主政治优越。纳粹的上台,就是因为它利用了当时德国萎靡的世风。但纳粹并没有兑现它对德国人民的承诺。因为极权政治是无法长期维持其干嚎式的道德热情的。只有民主政治在国家长期的稳定和持续的发展过程中所显现的绵延功能,才足以适应化解社会暴力郁积以及建立张驰有度的秩序的需要。进入近现代历史的五百年时间,民主制度被证明为最适应现代大型复杂社会以及民族一国家需要的制度形式。它确实没有极权制度那种让人亢奋的政治动员能力,但它使国家在秩序的轨道上向前滑行,虽无激情,但有稳定;虽无亢奋,但有秩序;虽无激越,但有安宁。这样的社会,可以给人们缓解暴力和维护秩序以足够的观念与行为动力。
至于民主自身的社会治理功能,也可以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积极的治理功能,一种是消极的应对功能。从前者看,民主国家运行着一套行之有效的经济一社会一政治制度。它的精髓就是让国家内部的所有公民都能参与到他们愿意参与的社会组织与公共事务之中。因此,公民的诉求可以在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知识、智慧与财富的前提条件下,诉诸自己理性的决断,并在社会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务决策过程中,使自己为自己负责、自己为组织负责、公民对国家负责的责任精神贯穿到日常生活之中。公民们的积极性可以在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不同空间发挥,而他们心中的怨恨也可以在相同的空间里舒张。普遍选举、社区组织和公益行动,将人们的高昂热情有序疏导。多元的社会政治行动促使公民怀抱不同的动机参与其中,国家不会因为结构缺乏改变、社会缺乏组织和公民缺乏参与而成为全面疲软的结构。它总是让公民们在自己的积极行动中感觉到国家与社会的改善或向好。他们很少趋同地认定只有借助于普遍的群体暴力,才有希望满足自己的要求,或者足以使人们重视他们的基本诉求。从后者即从民主的消极应对功能上看,民主提供了消耗公众剩余精力的政治渠道。这些渠道足以刺激人们钝化的社会政治生活神经。一方面,它可以用制度安排的方式疏导人们的不满。它因此尽力将人们不同的诉求导入讨价还价的日常生活轨道。这使人们形成妥协的政治生活习性,不至于任由自己形成全输全赢的零和游戏心理。另一方面,民主政治容许公民们合法地发泄他们的低级趣味,让人们的剩余精力不至于积聚到危害公众安全和国家安宁的地步。民主政治不以单纯的德性为取向,除开必须维护的公共道德规则之外,不合德性的规则尽管被社会谴责,尤其是被保守的教会组织和公民机构严厉批判,但社会宽容这些失误,容许人们偶然犯下可以矫正的错误。因此,民主社会即使出现罕见的群体暴力,那也是可以迅速得到诊治的事情。民主社会不是美仑美奂的,但民主社会可以有效引导公民热情,舒缓公民暴力。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频仍的群体暴力事件需要安置到民主制度选择的高级平台上寻找对治方略。仅仅是埋怨政府与民争利,苍白地呼吁加强官民对话,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与其治标,不如治本。正如一些论者指出的,对治今天中国的群体暴力事件,关键的是还权于民。让民众能够在民主与法治的条件下自治,也就意味着民众自己对于是非对错的理性判断,当然也就意味着民众个体与个体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乐意寻求理性合作。唯有致力于发展民主政治,“民有、民治、民享”,人们心中才能怀揣希望前行,对于一时的不利处境和不公遭遇不系于怀,才愿意诉诸时间相对漫长的理性妥协和谈判,放下暴力解决问题的思路,秉行协商的合作态度。倘非如此,群体暴力事件当下弹压愈是有效,长期郁积瞬间爆发的可能性就愈大,国家的安危问题也就愈令人忧心如焚。
责任编辑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