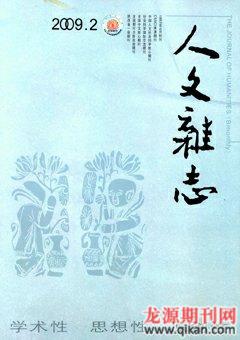“体不可说”及其对策
夏 静
内容提要 作为人类思想认识活动中的一种普遍性体验,中西哲人都意识到,对于终极的真实无法作出陈述或者判断,由此形成“体不可说”的见解及相关问题。不同之处在于方法的选择,道家以“无”为“体”,从方法论角度反面说无,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多从概念范畴立论,从认识论角度正面说有。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反形而上学和“语言的转向”,一些西方哲学家更加关注语言的有限度问题,而在中国哲学家的形上学建构中,“以负代正”和“遮诠”,成为代表性的表述方式。
关键词 “体不可说” “以负代正” “遮诠”
〔中图分类号〕B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2-0042-06
一
说到“体”,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体”是否可知、可说的问题,在现代知识语境中,又不免牵扯到知识论、认识论与本体论的问题,也涉及到对形而上学的认识与定位问题。作为哲学意义上“体”的纯正意蕴,是指万物之共同本质和存在根据,或者世界之最高本体(本原)及其认识路径。对此,熊十力(1885-1968年)先生揭示很明确:“体字有二义,曰体认,曰体现。”(注:熊十力:《原儒》下卷,《熊十力全集》第六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70页。)第一义涉及到认识论与价值论,第二义则涉及到知识论与本体论。对于终极性本原的探索,是人类形上追求中一个永恒的话题。自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年)、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以来的西方认识论传统,囿于主客二分模式和自我中心主义,除了使问题层出不穷外,并不能推进知识论、本体论的进步。熊先生就曾批评过西方的旧形而上学,认为它们把本体视为现象之外、与现象毫无共同之处而不可沟通的另一重世界,而现代哲学则只谈知识论,不谈本体论,这又陷入另一偏向。对此,他认为:
因为哲学所以站脚得住者,只以本体论是科学所夺不去的。我们正以未得证体,才研究知识论。今乃立意不承有本体,而只在知识论上转来转去,终无结果,如何不是脱离哲学的立场?凡此种种妄见,如前哲所谓“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③
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0-251、678-680页。)
熊氏认为研究知识论、认识论的最终目的就在于认识和达到最高本体,离开本体证悟,孤立地研究知识论,实际上只是“量智”的认识论,也即经验的认识和逻辑的推理,只能认识现象界,不能认识本体界。东方哲学家注重“性智”,这是一种直觉认识本体的能力,只有通过“性智”才能认识本体。
③正是针对西方哲学只重视向外认识客观世界,而不重视向内认识人的心灵,不懂得人的心灵是与宇宙的本体相通的种种不足,熊氏提出“反识本心”,也就是要认识宇宙本体,必须返观人的本心,而不能向外探求。
但是,问题的难处在于,作为哲学最高存在的“体”,正如王弼(226-249年)所谓“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老子注》),已经完全脱离了形与象的具体联系,遁形于万物之中,蕴涵在道器、隐显、动静、常变之间,那么,如何达致“体”呢?这在中西学术传统中,有着不同的思想特质与衍变历程。
纯观念形态的“体”,往往隐微难察,唯一可以把握的是其种种“化迹”,即在“用”中显现,离“用”无从识“体”,识“体”必依其“用”。从西学的角度看,作为本质的“体”和作为属性的“用”,有似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年)《范畴篇》中“本体”与“属性”(包括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等九个范畴)的对举,“本体”是“体”,是其他范畴存在的根据,其他范畴都是表述它的,不能和它分离。对于“体”的认识,中国古代哲人也作过许多精微的研究。孔子(前551-前479年)少有形上思考,因为对孔子而言,本体是不可言喻的,只能诉之于个体的直接体验,所以他以“无言”的方式来表述天的存在,故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不可言,但并不意味着天不可知,只是知的方式不是通过言的方式,而是体验地知,意会地知,朱子(1130-1200年)《集注》释云:“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在儒学看来,“体”之最根本特质,还在于个体不同的体验。
比较而言,老庄对于“体”的思考,更为精深。在老学思想体系中,道是最高本体,整个思想系统都是围绕道展开的。何谓道,老子(前580-前500年)开章明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在老子的思想中,作为终极存在的道具有如下特性:不可言说、不可命名,且“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抟之不得”(第十四章),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第五十六章),因此道是不确定的,人的耳闻目睹言说,对于体道,均是无效的,正因为无法肯定它是什么,所以只能说它不是什么,此之谓“正言若反”。那么,如何体道呢?老子是这样描述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第十六章)所谓“守静”、“知常”、“归根”,是老子体道的途径,这是一种将个人体验完全融入天地万物的意会感知方式,这与尔后庄学通过“心斋”、“坐忘”、“忘言”体道,路径大抵相同,均以为语言的知识形态与表达方式,无法达成对本体的理解。诚如有的研究者指出,道家的无名理论在西方哲学中没有十分准确的相似物,它源自古人一种独特的观念:语言相对于本体论的理解而言并不是完全可有可无的,但是,为了达到对这样的本体论理解,语言又必须废除。本体论和语言是不能并立的,它们分别属于人类经验的两个层面。(注:〔美〕成中英:《易学本体论》(Theory of Benti in the Philosophy of Yijing),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0页。)
接受过道家思想熏陶的金岳霖(1896-1984年)先生,从元学的对象,认同庄学“万物齐一,孰短孰长,超形脱相,无人无我,生有自来,死而不已”的思想。他认为,研究知识论可以站在知识论对象范围之外,可以暂时忘记自己是人,用冷静的态度去研究;研究元学则不同,虽然可以忘记自己是人,但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因此不仅在研究方法上追求理智了解,而且在研究结果上追求情感的满足。(注:金岳霖:《论道•绪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7-18页。)金先生早年接受过英国分析哲学的知识论和逻辑学的训练,在他看来,形上的世界,是超经验知识的世界,是说不得的世界,他在《势至原则》中论述“名言世界与说不得”问题时认为:
治哲学总会到一说不得的阶段。说不得的东西就是普通所言名言所不能达的东西……说不得的东西当然说不得,若勉强而说之,所说的话也与普通的话两样……因为治哲学者的要求就是因为感觉这些名言之所不能达的东西,而要说些命题所不能表示的思想。假若他不是这样,他或者不治哲学,或者虽治哲学而根本没有哲学问题。(注:金岳霖:《金岳霖学术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39-340页。)
金氏通过文法主宾词与逻辑主宾词的不同,来说明为什么形上本体说不得,在其形上学的建构中,“能”就是说不得的,因为“能”根本无所谓,不是个体,也就不在“名言范围之内”。值得赞赏的是,金氏的思想体系虽然吸取了许多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用以确定概念、范畴的明晰含义,但其内容形式却是民族化的,诸如理、势、性、情、太极、无极、正觉、意念等,由此建立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本体论、逻辑论和认识论系统,为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世界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体”是超验的、不可言说的,正是在不可说的地方,通过“无”的境界,才能领悟存在的真谛,才能达到人与万物的整体合一,庄子(约前355-前275年)所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庄子•天地》),王弼所说“以无为本”(《周易•系辞》注引王弼《大衍义》),庄子通过“心斋”、“坐忘”达到与道合一,王弼通过“言不尽意”、“得意忘言”体“无”,大抵都是这个意思。针对今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偏颇,有学者反省认为:
我们一般都把这种以“无”为最高原则、承认有不可说的思想贴上神秘主义的标签……其实,这是由于不懂得把握人与存在合一之整体正是哲学思考之第一要义,不懂得只有在不可说的地方,通过“无”的境界,才能真正把握这种整体的意义。这种观点片面地以为人对世界万物的唯一态度和关系就是主客关系式,因而认为哲学的最高任务只是把握客体或对象性事物之本质,而看不到对上述整体之把握;这种观点还在于片面的理性至上主义,以为最高、最真实的只是可以通过概念,通过逻辑来认识的,只是可以言说的,而看不到正是在不可说的地方,在一般所谓神秘的地方,有着最真实、最深刻的意义。(注: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7-58页。)
进一步言,“无”虽然不可说,但不能认为不可说者就没有,只有超越“无”这一最高原则,人才能把握与存在协调合一的整体性。
二
作为人类思想认识活动中的一种普遍性体验,中西哲人都意识到,对于终极的真实无法作出陈述或者判断,由此形成“体不可说”的见解及相关问题。不同之处在于方法的选择上,道家以“无”为“体”,从方法论角度,反面说无,而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多从概念范畴立论,从认识论角度,正面说有。
从西方哲学的历史渊源来看,哲学研究的主体有一个不断转变的过程。传统形而上学秉承理性至上的原则,一般认为凭借知识与理性,没有不可说的、没有不可认识的。这虽然是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但也不乏被斥为神秘主义的异端思想存在,这就包括了从古希腊后期延续到中世纪新柏拉图主义的许多思想家的观点。譬如古希腊后期的普罗提诺(Plotinus,204-269年),他视“太一”为最高的统一体,它无感觉、无思想、无区别,是超越“有”之上的“无”,不可知、不可定义,是语言文字不可名状的,是最真实的无所不包的整体。普罗提诺将“太一”置于柏拉图的“理念”之上,明确认定有超出理性思维的不可说的领域,要把握“太一”,无法借助抽象思维及概念,而要靠“出神”的一种“心醉神迷的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中,人才能与“太一”合一。(注:参考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卷3,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87-188页;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册,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363页;《古希腊罗马哲学原著选辑》,北京大学翻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463页。)又譬如中世纪的爱里更那(John Scotus Erigena,810-877年),他认为最高统一体超出名言,不可说,人只有在忘我的精神状态中直观它。黑格尔(Hegel,1770-1831年)认为,像爱里更那那样被称为神秘主义的哲学家是“虔诚的、富于精神修养的人物……在这里人们可以找到纯真的哲学思想”,他对此表示赞赏,并与中世纪的正统经院哲学比较,谴责后者的“彼岸性”,欣赏前者的现实整体性与反彼岸性。(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卷3,第319、323页。)
自柏拉图以来的传统逻辑认为,概念是思维中最基本的要素,由概念而判断而推理,通过概念、判断可以说尽形而上学。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年)对此提出挑战,他从认识论的角度,认为思维中运用的概念、范畴,不是先于判断,而是由判断力发展而来的,他以“二率背反”驳斥传统的理性至上,主张有不可知的,有一般概念不可言说的最高存在。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反形而上学和“语言的转向”,一些西方哲学家更加关注语言的有限度问题,其中,英国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年)的“过程哲学”,德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ng Wittgenstein,1889-1951年)的“逻辑哲学”,值得我们注意。
在谈论哲学的目的时,怀特海认为,哲学的困难源于语言的失误,难以表达自明的东西。人类的日常语言虽然变化万千,但均不涉及到哲学自明性层面的揭示,且语言处于直觉之后,我们的理解超出了语汇日常应有的范围,因此,这种理解“主要不是以推理为基础,理解是自明的”,但囿于我们直觉明灭不定,清晰性有限,因此,推理虽然是达到理解的手段,但哲学中的一切推论都标志着一种不完满。有鉴于此,怀特海认为哲学与诗相类似,不仅代表了文明的最高理智,而且哲学的努力体现在从诗人的生动词汇中创造一套可以与其他思维联结的语言符号,同时,“二者都力图表达我们名之曰文明的终极的良知,所涉及的都是形成字句的直接意义以外的东西。”(注:〔英〕怀特海:《思维方式》(Mode of Thought),刘放桐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5、152页。)(这与我们熟知的黑格尔看法相似,艺术、宗教、哲学所要把握的目标一致,但形式却不同。)
维特根斯坦早年的《逻辑哲学论》,旨在说明语言与世界之间的逻辑结构,划定思维的界限,在他看来:
凡可思者都可以清楚地思,凡可说者都可以清楚地说。(4.116)
哲学中的正当方法固应如此:除可说者外,即除自然科学的命题外――亦即除与哲学无关的东西外——不说什么。(6.53)
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必须沉默。(7)(注:〔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名理论(逻辑哲学论)》(Logisch-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张申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9、88页。)
质言之,他表述了一个重要命题:凡是能够说的,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就应该沉默。所谓可说的东西,是符合逻辑语法的经验事实命题,它包括日常经验命题和自然科学命题;所谓不可说的事项大致包括:逻辑形式、形而上主体、世界的意义和人生的意义、与世界的意义和人生的意义有关的伦理学、美学、形而上学和宗教等等。在他看来,“诚然有不可言传的东西。它们显示自己,此即神秘的东西”(注:维特根斯坦:《名理论》,第88页。),不可说的“神秘”、“应当保持沉默”的东西,“只能显现”。他认为语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和世界的界限,界限之内是可说的,并且可以说得清楚,界限之外是不可说的神秘地带,这个领域没有自身的正面性规定,是言语无法达到的地方,只能通过可说的领域显现出来。维特根斯坦此论的目的,在于运用可说与不可说这一界限,把伦理和美学排除在哲学之外,因此结论是否正确,倒也不必深究。
这种对语言遮蔽性特征的认识,与稍后的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年)是一致的,他们都在极力地表明语言的限度,有许多东西用抽象的、概念的语言无法表达,“沉默”才是一种真正的理解。在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中,对“语言――存在”有深入的思考,在《语言的本质》演讲中,他以《词语》为例,企图“从语言中获得一种经验”,他认为,语言知识无涉于我们从语言身上获取一种经验,相反语言知识掩盖了真相,颠倒了人与语言的关系,因此只有弃绝言说,所谓“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惟有如此,世界才能是本来的样子。(注:〔德〕海德格尔:《语言的本质》,《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061-1067页。)在《形而上学是什么》中,海德格尔认为,科学以一种高傲的无所谓的态度对待“无”,把“无”当成“不有”的东西牺牲掉了。“无”并不是在有存在者之后才提供出来的相对概念,而是原始地属于本质本身,是我们与现实存在物作为整体相合一时才遇到的,也就是他所说的“在‘无中”的意思。在他看来,把握“无”从而真正把握人与物合一之整体,乃哲学思考的第一要义(注:海德格尔:《形而上学是什么》,《海德格尔选集》,第139-146页。)。
所谓的“不可说”,只是相对于有限的“人言”而论的,对于隐藏其后的“道说”而言,却是生生不息的。对此,师从海德格尔的熊伟(1911-1994年)先生认为:
“不可说”乃其“说”为“不可”已耳,非“不说”也。“可说”固须有“说”而始“可”;“不可说”亦须有“说”而始“不可”。宇宙永远是在“说”着。无非“它”“说”必须用“我”的身份始“说”得出,若由“它”自己的身份则“说”不出。故凡用“我”的身份来“说”者,皆“可说”;凡须由“它”自己的身份来“说”者,皆“不可说”。但此“不可说”亦即是“它”的“说”;“它”并未因其“不可说”而“不说”。(注:熊伟:《说,可说,不可说,不说》,载国立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1942年第一期。)
“可说”和“不可说”同出,乃“说”的两个方面,必须有“可说”和“不可说”才能构成“说”的世界。这和“有”和“无”的关系一样,不能全“有”,也不能全“无”,宇宙本一,“有”“无”相成而宇宙。
三
对于形上学,中国现代哲学家大多怀有浓厚的兴趣,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和冯友兰(1895-1990年)先生的“新理学”是两个典型的形上学体系。譬如冯先生认为,在中国哲学史中,先秦道家,魏晋玄学,唐代禅宗,恰好形成一个形上学传统,他创建的“新理学”就是在这种传统的启发下,“接着”宋明道学的讲法,借助现代新逻辑学,以建立一个完全“不著实际”的形上学
④冯友兰:《新原道》,《三松堂全集》卷五,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7、154页。)。对于形上学中不可说的领域,他们的解决之道各不相同。冯先生接受过逻辑实证主义的训练,受到过维特根斯坦的影响。相对于维特根斯坦的“沉默”,冯氏选择“以负代正”的方法。熊先生偏于经验世界与本体世界的区分,他借用佛学“遮诠”方式,遮拨一切法相,破相显性,达致本体,建构了极具学术原创性的体用论。
首先,冯先生辨明了科学与哲学对“物”的不同理解。科学和唯物论中的“matter(物质)”,有物质性,可名状,可言说,可思议;哲学上的“matter(物质)”,本身无性,不可名状,不可言说,不可思议。冯友兰:《新理学》,《三松堂全集》卷四,第47-48页。)其次,在“新理学”的形上系统中,四组主要的命题都是形式命题,理、气、道体、大全四个主要观念,就是从四组命题中推出来的,其中“理及气是人对于事物作理智的分析,所得的观念。道体及大全是人对于事物作理智的总括,所得的观念”
④。在他看来,真正形上学的任务,就在于提出这一类观念并加以说明。再次,在通过中西形上学方法的比较后,冯氏指出,西方哲学家讲形上学用的方法是“正的方法”,即“逻辑分析方法”,但无法用于“新理学”中四个形上概念的解释,譬如“道体”和“大全”之“不能讲”,在于“道体”是一切的流行,“大全”是一切的有,二者都是外延至大、无所不包,所指均超出了逻辑的范围、语言的范围。
在此基础上,冯先生总结出“正的方法”讲形上学的局限性,就在于用理性在天与人之间划定了一个界限,因此不能真正把握形上学的对象,更不能使人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有鉴于此,他从道家哲学和禅宗思想中总结出“负的方法”,也即直觉主义的整体把握方法。“负的方法”也即所谓“烘云托月”法,是讲其所不讲或画其所不画,说气,不说气是什么,而说气不是什么;画月,则画云彩留白。在他看来,对于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形上本体,只能采取“负的方法”,而非“正的方法”。(注:冯友兰:《新原道》、《新知言》,《三松堂全集》卷五,第151-152、231-232、169-174页。)在“新理学”形上建构中,“负的方法”极为重要,超过“正的方法”,故而“以负代正”,居于上位。同时,两种方法又是相辅相成的,在冯氏看来:
一个完全的形上学系统,应该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的顶点。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它就缺少作为哲学的实质的清晰思想。
在使用负的方法以前,哲学家或学哲学的学生必须通过正的方法;在达到哲学的单纯性之前,他必须通过哲学的复杂性。
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三松堂全集》卷六,第305-306页。)
冯氏的“新理学”,源于思之说,止于不思不说。冯氏的“沉默”,类似于理学家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后突然达到豁然贯通,直接面对已然完整呈显出来的形上对象,同天、同万物浑然一体,此时,对于我们领悟不可言说的境地,语言已成多余。
不同于冯氏“以西释中”,熊先生更多地从传统思想资源中寻找解决之道。他认为,“体”是超越一切事物的至理,没有差别,没有封畛。言说所表达的,是有封畛的,体无封畛,非言说能及,而“用”是有形状的,是千差万别的,故可说。他是这样认为的:
我们要谈本体(体),实在没有法子可以一直说出。所以,我很赞成空宗遮诠的方法。但是,我并不主张只有限于这种方式,并不谓除此以外再没有好办法的。我以为所谓体,固然是不可直揭的,但不妨即用显体。因为体是要显现为无量无边的功用的,用是有相状诈现的,是千差万别的。所以,体不可说,而用却可说。
③④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第301-302、300-301、302页。)
那么,哲学家又如何达致本体呢?熊氏认为,哲学家不应该定义本体是什么,因为这样只能引起人的误解,而是应该引导人们摆脱关于本体的种种误解,返观自识,自悟真理,虽不能用语言表达,但心知肚明。那么,如何才能借助语言,摆脱误解而心知肚明呢?熊氏认为,哲学上的修辞,最好用“遮诠”的方式:
详夫玄学上之修辞,其资于遮诠之方式者为至要。盖玄学所诠之理,本为总相,所谓妙万物而为言者是也。以其理之玄微,故名言困于表示,名言缘表物而兴,今以表物之言而求表超物之理,往往说似一物,兼惧闻者以滞物之情,滋生谬解,故玄学家言,特资方便,常有假于遮诠。熊十力:《新唯识论》(文言文本),《新唯识论》,中华书局,1985年,第66页。)
在他看来,古今讲哲学而善用“遮诠”的,莫过于佛家,佛家中尤其以大乘空宗为善巧,因此,他特别欣赏空宗一往破执的“遮诠”言说方式。
所谓“表诠”、“遮诠”,乃佛教体认和传播佛理的言说手法,“表诠”是从正面作肯定解释,“遮诠”是指无法直接表达,只好针对人心迷妄执着的地方,想办法来攻破它,令人自悟。对此,宋初永明延寿禅师释云:“遮谓遣其所非,表谓显其所是;又遮者拣却诸余,表者直示当体。”(《宗镜录》卷三四)凡是不便明说或者难于明说的地方,通过“遮诠”的方式,把该说的隐去,借已说的使人联想,使人领悟,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与反诘、旁敲侧击、棒喝等方式类似,都是禅宗觉悟佛性本体的方式。“遮诠”的解释方法,其基本特征在于否定一切由理性知识所定义的本体观念,使人们认识到对象化思维的局限性,其基本的方法就是不作任何肯定的陈述,而是通过不断地否定别人的意见,指出别人的错误,使人认识到日常语言的限度与有效性,最终认识本体。遮诠的句子具有“既是又否”、“既不是又不否”的形式。熊氏本人就常采用这种说话方式,如“本体既是空的又不是空的”,“本体既不生又不不生”,等等。
熊氏认为,“遮诠”之法可以破除一切人的知识与情见,涤除世俗知见,破除一切法相,达于豁然澈悟,深入真实本性,即所谓“破相显性”:“他们的言说,总是针对着吾人迷妄执着的情见或者意计,而为种种斥破,令人自悟真理。”
③熊氏论及此一问题时,深有感触,认为有许多奥隐曲折的意思,广大精深,很难为一般人说得,惟有与他有相同见解的人,才知个中甘苦。在他看来,用“遮诠”方式讲体用,可以避免把“体与用截成二片”。因为体用高度统一,不可分割,“体”虽不可说,“用”却是可以说的,因为“用”总是“体”之用,“用,就是体的显现。体,就是用的体。无体即无用。离用原无体。所以,从用上解析明白,即可以显示用的本体”④。故而对“用”的言说,都可以显现、烘托、反映出未说的“体”的境界,并且使我们更接近“体”。
从方法论上看,无论是“沉默”、“负的方法”或是“遮诠”,对于我们思考“体”的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所谓“不可说”者,在一定意义下仍然是可说者,“不可说”本身是一种言说方式,是一种无须语言的意会体悟,它在知识论与认识论上的意义,已经不同于旧形而上学的看法,而进入了一种新的境界。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