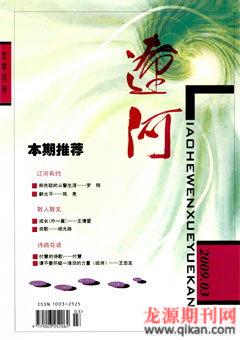木槿花
姜煜暄
我千方百计摆脱了父母的阻挠,毅然决然地去了大西北的一个偏僻城市的师范学校。其实我满可以报考离家近的,条件好的师范学校,或者其他专业,但我却离经叛道,与父母的意愿背道而驰,竟鬼使神差地报考了这所学校。
高二时,新来一位班主任老师,是个女的,教我们数学。她叫“穆锦花”,她的名字和校园那片盛开的木槿花谐音同名,同学们就称她为“木槿花”。她长得就像木槿花一样美丽鲜艳,苗条婀娜的身姿,秀气迷人的眼睛,温柔白皙的笑脸,整齐洁白的牙齿,活泼可爱,尚未脱去纯洁女孩的稚气。
虽然称她为老师,其实比我们大不了一二岁,然而却很沉稳而矜持。
记得她第一天给我们上课时。以我为首的几个调皮鬼,想给木槿花一个下马威,把她轰走。换个男老师。以前有位女老师,被我们捉弄得哭哭啼啼地走了。便想出一个损道,将一盆水顶到门框上,木槿花轻轻一推门,“哗”地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底,水在木槿花的身上像瀑布一样流泻。引得同学轰然大笑。课堂顿时乱作一团。好像闹市场似的,乱哄哄的一片嘈杂声。
木槿花立刻惊愣了一下,脸色一阵儿红一阵儿白。旋即,莞尔地笑了:看来同学们很欢迎我这个新来的老师啊,感谢同学们的最高的礼节……同学们顿时愕然,大眼瞪小眼,哑口无言。我心里偷偷地乐,心想,这老师有病吧?怎么没急眼发怒呢?
须臾,木槿花甜笑着问道:你们知道傣族人家待贵宾的礼节吗?同学们鸦雀无声,几十双眼睛定定地盯着她,连我这个最操蛋调皮的也张口结舌了。
傣族人家的最高礼节是泼水节,那是一种吉祥的象征,一种最美丽的祝福。木槿花滔滔不绝。津津有味地讲述着。同学们的目光刷地扫向我,我霎时脸火烧火燎,滚烫滚烫的,浑身像无数条小虫在撕咬吮吸着。如果不是木槿花亲口说的,真不敢相信她是傣族人。
有一次,我把一个同学打得鼻孔出血,木槿花一把抓住我的衣领,问我为什么打人?我不服气地一把将她脖颈的项链撕断,散落于地上,我突然发现项链的鸡心里镶嵌着一个男人的照片。她突然发疯般将我打倒在地。事后,体育老师哈哈大笑说:木槿花在学校学过柔道。我有些胆怯了,总是躲避着她走。然而心里还是很敬佩她的。
学校开运动会,她训练我们五公里长跑,我这个号称长跑冠军,竟然没跑过她这个丫头片子。运动会前日,木槿花给我一包巧克力,是一块绣着木槿花的手帕包的。她说:巧克力可以增加热能量,国家运动员的必备品。从而木槿花的影子在脑海中缠绕,挥之不去。那次我没有辜负她的希望,一举夺魁,并打破学校纪录。
说来怪异,从此我开始专心致志地学习。班里再也没发生古怪的事情。然而内心却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幻想,甚至会在梦乡中反复闪现那块精美的木槿花手帕。
有一天正上自习课时,木槿花突然去收发室接一个电话,回到教室双眼红肿红肿的,眼角还挂着泪痕。我想她一定哭了,而且哭得很悲痛,很伤心。我一直以为她是个刚烈的女子,想不到她也有伤感的时候。
半个月后,校园里的木槿花开得火红火红的,木槿花突然走了,去了大西北。
我办好一切报到手续,便急不可耐地给木槿花支教的学校打电话。是位男人接的,我兴奋地说:我是穆锦花的学生,想拜见一下穆老师。
那位男人沉默了好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好吧,我一定转达到。似乎很不情愿的口吻。我有些纳闷、迷惑不解。
蜡烛映照出柔和的光彩,我静静地坐在咖啡屋,等候木槿花的到来,望着窗外万籁寂静的星空,突然有种空旷孤独之感,不禁浑身打个寒噤。不经意间,我忽然发现墙角处有一盆木槿花,盛开着艳丽的花朵,飘着淡淡的清香。油然而生一种忧伤的心绪,便沉默地遐想着。
你是术槿花的学生吗?一位老人慈祥的话语。扯断我的思绪。
我点点头。他递过一块木槿花手帕。我霎时懵懂了,疑惑的眼神怔怔地盯着老人悲痛的脸膛。我跟随老人默默地来到一片萋萎青草的坟墓。
老人眼圈湿润了,噙着浑浊的泪水,哽咽地说:我是木槿花老师支教学校的校长,穆老师她在头几天走了,山里发洪水,泥石流爆发,穆老师为了救护学生,被泥石流卷走了。
我疑惑地发现墓碑刻着两个人的名字。老校长凄然地说:那是她的男朋友,去年患病死了,木槿花为了完成男朋友的遗愿,才到这里支教的。
瞬间,我脑海一片空白,手里紧紧攥着那块木槿花手帕,涔涔汗水浸透了美丽的木槿花手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