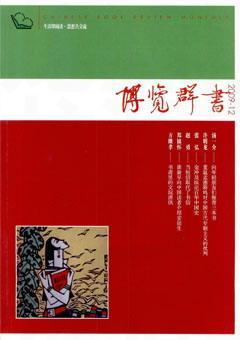用“博览”之钥开启“研究”之门
范伯群
为了建构多元共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近年来我致力于现代通俗文学的研究。探索新文学之外的一个过去所不熟悉的“世界”,阅读了大量过去教授新文学史时所没有涉猎过的通俗小说,它的长篇数量之多恐怕要数倍于新文学同类作品。其中也不乏优秀或较好的纪实性很强的“存真”小说。我常感到这是一座富矿。经过提炼,是能成为多元共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当我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完工之后,我的“大阅读量”也能算是一笔可观的精神财富,我可以对其进行“二度开发”。我往往将昔日的“存真”小说对照今天的若干社会热点,思考些可作为参考的经验与教训。
前一个时期的社会热点之一是大家热议“乡下人进城”的问题。许多作者在写这一题材,若干评论家在评论这一题材的作品,有些民工也写小说来诉说自己的切身感受。我所阅读的现代通俗小说中就有许多写乡下人进城的长篇,不乏真实而相当深刻之作。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海上花列传》的第一回“赵朴斋成瓜街访舅”就是写的“乡下人进城”。这一题材其实是具世界性的。当农业自然经济过渡到资本工商经济时,许多大都会的建成就是靠移民们的“双手”与“心力”。中国的现代通俗文学也顺应这个客观的铁律,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写“移民潮”。但我以为,说“乡下人进城”固然很是通俗,可是也颇有点“城里人”踞高临下的蔑味。因此我喜用“移民题材小说”的名称。它既包括了民工为主的大流量,也包容了跨城居的投资经商者等各色行当。现代通俗小说从《海上花列传》开始描绘多种移民——投资经商者、为官为吏者、文人清客、流落娼妓等等的形象后,移民生活就成了现代通俗小说的一条文字漫游热线。上海这个中国特大的移民城市就成了描写这一题材的首选目标。据1885年前后统计,6个上海居民中有5个是外来移民。因此这条文字热线的形成决非偶然,它说明了通俗小说的“存真性”是极强的。继之出现的是吴趼人的《发财秘诀》,写广东人到上海。过去清朝只允许广州一口通商。南京条约五口通商之后,1843年上海开埠。广州的洋大班们携中国买办来上海开辟淘金场,这部小说又名《黄奴外史》,顾名思义,读者就能知道作家要反映的是一种过去上海还没有的“新移民”的特殊品种——康白度(买办)。
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平襟亚的《人海潮》与包天笑的《甲子絮谭》是写苏州人来上海。《海上繁华梦》写苏州人到上海观光游览。苏州昔日是江南商业聚散中心,国宝级的《姑苏繁华图》(原名《盛世滋生图》)就是明证之一。而上海开埠前只是仅有10条街的松江府治下的一个县城,它不能说不旺发,故曾有“小苏州”之称。但是经过太平天国时的拉锯战,苏州成了满目创伤的破落大户,而上海开埠半个世纪之后,竟成了往昔见过世面的苏州人想去大开眼界的繁华之都。《人海潮》则是写江南大水灾后,苏州乡民到没有田亩的上海柏油马路上去找粮食吃,涉及的是灾民生活。而《甲子絮谭》是写1924年江浙军阀混战时的江南“难民流”。以上三部作品虽同是写苏州人进上海,但视角不同,各有千秋。姚鹉雏的《恨海孤舟记》是写京师大学(北京大学前身)的学生南下上海办报办刊,通过此人带出了一批当年的革命者,如章太炎、陈其美、柳亚子、叶楚伧等人在上海的活动,连带记录了宋教仁和陈其美在上海的被刺,又顺势写到蔡锷在云南高揭反袁义旗。而吴趼人的《上海游骖录》和欧阳钷源的《负曝闲谈》则臧否移民中维新派的种种行径。严独鹤的优秀通俗长篇《人海梦》是写宁波人到上海求学,并以此为跳板到日本与欧美留学,从中反映了国内外相互策应的革命活动,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培养了骨干力量。姬文的《市声》是写扬州和无锡商人进上海,是一部与外国资本展开商战、发展民族工业的重要题材。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则是写外乡女子被带到上海,从事淫业卖笑,过着一种特殊的“人间地狱”的生活。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是全景式地展示上海这个既是“文明之渊”又是“罪恶之薮”的都市,提醒移民们,在那陷阱遍布的都市里要处处有自卫性的警惕与防范。
上海是个国际性大都会,通俗作家们扩宽视野,也关注国际移民的若干生活画面。孙玉声的《黑幕中之黑幕》是一部非常有意思的小说。由于“黑幕小说”这个名词被中国的某些作家搞臭了,因此看到这个书名读者就会摇头叹气,不敢领教。其实这部于1918-1919年连续出版的3卷本的小说是具有相当超前意识的长篇。它主要反映上海开埠之后,有的骗子运用租界的法律来对中国的法盲们进行诈骗。例如先用女色诱人,发展到赁屋同居的热度,买了高档家具,骗了首饰珠宝;然后她的“丈夫”出现了,在法庭上当场拿出“结婚证书”来,女骗子又保留了购物的种种发票向法官出示。租界的法律素重证据,于是骗子满载而归,老实的崇明移民却受牢狱之灾。接着就再骗他要不要办“取保候审”,又得花一大把钱,事情当然不会替他办成;于是再进而联络了滑头医生,劝他办“保外就医”……如此的“黑幕之后还有黑幕”的连环骗局,几乎使不懂法律的移民大吃其亏。而更严重的骗局还在后面呢,为了开珠宝行,怂恿崇明老板请外国人做“出面东家”,可以仗着外国人的势力做“保护伞”。谁知那把“伞”仅是个高鼻子的无国籍浪人,事成以后就来“鸠占鹊巢”,把中国老板逐出店门。最后还是靠着有正义感的外国商人争回了部分损失。可见这是一部既超前又有一定现实感的小说。而《海上大观园》则是写上海首富、英籍犹太商人哈同(小说中名罕通)及其夫人罗迦陵生活的小说,有一定的纪实性。
上述琳琅满目的11部长篇和3部中篇小说,一旦用“移民题材”这根红线将他们串起来,就成了一串珍珠,粒粒闪出它们特有的光芒,即使某些颗珍珠还有这样那样的瑕疵。但就这一题材的整体丰富性而言,新文学作家的同类作品无法望其项背。这些通俗作家开始也许是不自觉地接触这一题材的。可是当这些作家渐渐各展才能去“漫游这条文字热线”时,其自觉性就会有愈来愈强的体悟。当我读到平襟亚(网珠生,又名沈平衡)的《人海潮》中的一段对话时,我窥见了他们已经自觉地在挖掘这一题材中的宝藏。在小说中,他是通过两位农村小知识分子——也是一对恋人的对话表达了作家取材的自觉性。少女湘林称赞迭更司的一支笔就像显微镜,能将一针一芥放大几千倍,刻画得入木三分。由此说明写社会小说的作家应该有阅历,有胸襟,有文采,脑藏千卷书,脚行万里路。她认为乡村街坊上有三处小说材料批发所:小茶馆、小酒店和燕子窝(小鸦片馆)。湘林毕竟是在上海读过中学的女青年,颇有见地。可是他的男友说出一番更令人钦佩的见解:
我有一处人们注意不到的小说资料,要比你说的三处地方来得有趣味、有统系,写出来一定有刺激性,能够哄得人笑啼并
作。……这块地方小虽小,却是流动的,普遍在各乡各镇,便是一条驳船。这驳船每天清晨开往塘口(属苏州的一个乡镇——引者注),接上海小轮上的搭客,驳送到各乡镇;垂晚又把各乡镇往上海的搭客,驳到塘口小轮,每天满载一船。这其间,男女老幼,哭的、笑的、叹的、忧的,千态万状,哀乐不齐。哭的,无非夫妻勃豁、母女口角,一时气愤,遁迹海上(当时苏州四乡的妇女到上海做佣工成风——引者注);笑的,赢获巨金,衣锦还乡;叹的,入得宝山,赤手空回;忧的,身怀私货,中心彷徨。这是现面的事,细究内幕,更不少伤心黑暗的资料。(第8回)
这部《人海潮》一共50回,前10回写苏州农村,后40回就写这些乡下人到上海后“哭的、笑的、叹的、忧的”移民生活。用根红线将同类小说串起来,就可从中研究许多问题,从而去吸取昔日的若干经验与教训。在这“二度开发”中,我从新的角度给自己出了几个思考题:
首先思考一个有关文学创作上的问题。为什么通俗作家能如此集中地反映这一题材,而新文学作家虽不与此种题材绝缘,却无法与通俗小说中的这一题材的丰富性比肩?例如平襟亚是常熟农村人,因生活无着,21岁闯荡上海。可是新文学家中移民作家也有的是,上海籍的新文学作家不多。相比之下,为什么对这一题材缺乏应有的关注?这是不是与他们的生活圈子不同、而探究的问题又各有所侧重相关?
第二,据历史学家的研究,19世纪中叶来上海的移民主要是富商、士绅、官僚、技术工人和冒险家。20世纪初的移民主要是破产农民、城市贫民。这是由于1860年太平军进攻苏杭一带,难民流中更有许多是江南“上等士绅”。以后天灾人祸连年,又使许多破产的农民到上海出卖劳力。虽写各色人等,但通俗小说绝不套用“城恶乡善”、“洋恶中善”等等模式。生活是怎样就怎样写。在孙玉声的《黑幕中之黑幕》中,既有外国流氓,但也有正直的外国律师,也有正义感的外国商民。这使我们联想起李伯元的《文明小史》中写了一个很能救民于困的外国传教士的形象。文艺理论中常说,要艺术的真实,而生活的真实是低层次的真实。通俗小说的存真度很高,这是它低层次的表现吗?
第三,在清末民国时期上海一直被视为逃避战乱的“净土”。太平天国时上海人口增加了11万,抗日战争时期租界里拥进70万难民,而解放战争的3年中上海人口净增208万。通俗小说中很关注移民的流速、流量、流幅与城市病的加剧之间的关系。这种非常态的人口激增在包天笑的《甲子絮谭》(民国甲子年即1924年)中反映“难民流”时就有精彩的描绘。一座单开间两层的石库门房子里要住11户人家,简直匪夷所思,流落上海的人甚至羡慕蜗牛,带着自己的“住房”;抢劫、绑票等凶案频发。那是因为流速太快,流量太猛,流幅太宽,都向着上海、向着上海租界的弹丸之地而来。不像现在的移民潮,从西部向东部流动,虽然有可观的流量,但可选择的富庶的地域较宽,呈等量的分散加压,压力在可控范围之内。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新移民,主要是乡民的文明程度目趋改善,使其迅速地融入市民社会。“乡民市民化”应是一个现代化的系统工程。历史学家赞扬通俗小说等通俗文化是使“乡民市民化”的“启蒙教科书”,是“乡民转变为市民的又一座‘引桥”(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5卷P387、P394)。我们应该如何吸取这些通俗小说的成功经验?
第四,过去的难民与灾民,流落到大城市后,很少有人再能回去的了。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是农村的破产者,无家可归。而有些人又觉得上海这花花世界太可爱了,即使在上海吃辛吃苦,也不肯离开。《海上花列传》中的赵朴斋沦为黄包车夫,被舅父派人押上回乡的航船,可是押送者前脚走,在航船将开的刹那问,又一跃跳上了这上海滩。正如沪谚所说,“走尽天边,不及黄浦两边”。因此,过去城市文明的信息往往只能靠通俗文化的畅销与流行,辐射到内地城镇或农村去,常常使人半信半疑。难道是这样的吗?而现在的民工,来城市打工是为了赚钱回乡去改善家庭的生活。因此一部分虽然成了移民,然而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在城里学到了新技术和经营管理的手段以后,就返乡去创业,这种亲身“辐射”比以往的间接辐射的效力优胜万倍。我们今天的辐射强度与过去的间接传播对比,其优越程度是一个值得探讨并大大发扬的问题。
由于篇幅关系,我不能在此写长篇论文,这些思考题仅是我想“用‘博览开启‘研究之门”的入场券。至于进门之后,如何深入堂奥,我当然要去进一步探索,同时我也求教于高明的读者们的集思广益。这就像过去新文学家与通俗作家都热衷于写“问题小说”一样,只提问题,不交答案。那么我今天交卷的是一篇相类似的“问题杂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