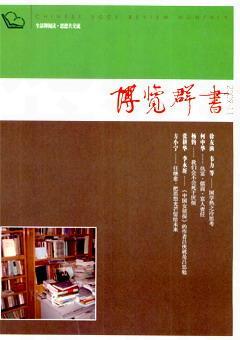我们会不会死于厌烦
杨 钧
一天,美国布朗克斯的一名公共汽车司机开走了他的空车,直到好几天后才在佛罗里达被警察抓获。他解释说,由于厌倦了每天在同一条路线上行驶,他决定来一次这样的旅行。这个消息见报之后,他成了布朗克斯轰动性的人物,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到机场欢迎他的归来,公司也决定不对他进行处罚,而只让他保证以后不再做这样的短途旅行。
这是《罗洛·梅文集》里的一个小故事,其中的意味让人难以释怀。为什么这个司机的异常举动能获得社会大众普遍的同情?罗洛·梅认为,司机的行为代表了美国中产阶级某种相似的空虚感和无效感。人们之所以能够忍受这种千篇一律的生活,就是因为他们可以偶尔地爆发,或者至少认同他人的爆发。但这种爆发,凸显的正是人们生活的无意义与荒谬。
作为一位精神分析学派的心理学家,罗洛·梅虽然曾受教于弗洛伊德的弟子阿德勒,但是他的思想资源更主要地来自于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保罗·蒂里希等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焦虑与绝望、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此在、保罗·蒂里希的非存在与勇气等概念,都成为罗洛·梅心理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在罗洛·梅看来,心理学和心理治疗作为科学,它主要关注的是人,而且它并不仅仅关注心理上有问题的人,而是应当关注人本身。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物,他并不像橡树籽长出橡树那样完全依靠自然本能,而是首先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能力的主体而存在。在罗洛·梅那里,自我不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那个处在动物本能的“本我”与道德约束的“超我”之间饱受压抑、苦苦挣扎的自我,而是在原始生命力的驱动下,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有勇气为自己承担责任的存在。罗洛·梅认为,弗洛伊德将自我看作是一种个体发展的机能,一种抵御外部世界的压力和身体内部的力比多冲动的防御机制,这实际上是将自我降低到了技术的层次,而自我本应在本体论的层次上来加以对待。因此,罗洛·梅的存在心理学,就试图将心理学建立在以存在概念为核心的哲学基础之上。存在心理学并不否认研究人的各种驱动力以及特定行为模式对于心理治疗有重要意义,但是这种研究必须要在个体的存在结构这一背景中加以理解。尽管罗洛·梅也承认由于存在概念的模糊与深奥,使得存在心理学自诞生之日起就饱受争议,甚至遭到许多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和正统精神分析学家的排斥与反感,但是他仍然认为,存在心理学对于丰富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依我看,罗洛·梅将存在主义哲学与心理学成功嫁接在一起的关键,是“存在感”概念的创立。海德格尔认为“此在”(即“人”)总是有情绪(德文stimmung,英文state ofmind,又译为“心境”)的,但是这种情绪又并非心理学研究的对象,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情绪,是情感、感觉尚未分化的状态,此在就总是处于这种有情绪的生存之中。海德格尔用于描述此在生存状态的一系列概念,如“操心”、“沉沦”、“畏”等,都有这种情绪体验的性质。罗洛·梅结合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发展了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认为人的存在就是一种“我在”的体验,即“存在感”。用罗洛·梅自己的话说,“存在感指的是个人的整体体验(不仅包括意识的体验,还包括潜意识的的体验),而且它绝不仅仅是意识的动因。……我的存在感并不是我看待外部世界、估量外部世界的能力;相反,它是我将自己看作是一个在世存在、认识自己是能够做这些事情的存在的能力。”(《存在之发现》,P105)存在感不仅仅是一种心理格式塔,而且还是一种价值观与人生观。罗洛·梅创立“存在感”这一概念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去重新发现自己内部力量和完整性的根源。因为他发现,无论在个人身上还是在社会中,没有哪种价值观是始终有效的,除非个人身上存在进行评价的先验能力。也就是说,要积极地选择和确证他据之以生活的价值观。
然而,让罗洛·梅深感不幸的是,他发现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宗教的式微,当今世界已经处在一个韦伯意义上的“祛魅”时代,人们的存在感正在面临日益丧失的危险。在《人的自我寻求》一书中,罗洛·梅给我们展示了人们在丧失了存在感之后那种内心世界极度空虚、无聊、焦虑和绝望的状态。他还不无风趣地说:“生活在一个焦虑时代的少数幸事之一是,我们不得不去认识我们自己。”他为我们描述了一个60多岁的一辈子过着循规蹈矩生活的老头死于心脏病,罗洛·梅却怀疑他是不是死于厌烦。这让我想起了美国诗人奥登的《无名的公民》:“他被统计局发现是/一个官方从未指摘过的人,/而且所有有关他品行的报告都表明:/用一个老式词儿的现代含义来说,他是个圣徒。”这样一个标准的良民安然死去,诗人却在最后追问:他是否自由?他是否幸福?这种追问其实和罗洛·梅对于存在感的分析有同样的意味,那就是:未经内心省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自我对于意义和价值的寻求应当是个体获得存在感的主要方式。所以罗洛·梅引用戴维·里斯曼《孤独的人群》里的一个分析,对“外部导向的人”进行了批判。里斯曼认为,当今典型的美国人是“外部导向的人”,他不是寻求出人头地,而是寻求“适应”,他的生活好像受到了一个紧紧固定在他头脑中并且不断告诉他别人期望他如何做的雷达的指挥。这种雷达型的人从他人那里得到动机和指导,就像那个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多面镜子组成的装置的人,他能够作为反应,但却不能进行选择,他没有自己有效的中心。这样的“外部导向的人”缺乏内省的能力,整个世界的面目在他那里都变得模糊不清。他丧失了对自然的观察力和欣赏自然美的审美力,丧失了“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那种在自然中看到我们心境的能力,也丧失了将自然作为具有丰富维度的对象而加以体验的能力。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很难再出现像华兹华斯、叶芝那样终生以描绘自然之美为己任的艺术大师。这种情况在现代艺术上的表现之一,就是我们正在失去悲剧感。在罗洛·梅看来,悲剧表明的是一种对人类存在的深刻尊重以及对个人权利和命运的信仰,人们在失去这些人们最为尊崇的价值与信仰时,就会产生悲剧感。然而,大规模的工业化、国家机器的庞大力量以及集体主义观念的日益强大,使得个人变成了无足轻重的原子式个体、宇宙中的尘埃,人们对于生存的体验,更多是荒谬与滑稽,而非严肃的悲剧感。由此人们就会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焦虑在克尔凯郭尔那里被视为一种自由的可能性,是“自由的晕眩”,就是人对可能性既欲求又恐惧的紧张不安。而在罗洛·梅看来,焦虑是一种被困住、被淹没的感觉,是我们面对非存在威胁时的一种反应,在焦虑中我们的知觉会变得模糊,而不是变得更为敏锐。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说,焦虑就是我们存在感的现实状态,也就是说人的存在总是与焦虑如影随形。
罗洛·梅承认,他对于这个时代产生混乱根源的描述,总体上来看是一种“黯淡的诊断”,但这并不必然是一种“黯淡的预兆”,即人类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在他看来,神经症以及人的种种心理疾病,表面上看是对环境的适应不良,而其实质,却是一种逃避,是人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特性、企图逃避来自现实的或幻想的外在环境的威胁,其目的依然是为了保持自我的完整性。因此,存在治疗的目的就是让患者重新获得存在感,这成为一切心理治疗的前提。那么,如何能重新找回存在感呢?罗洛·梅开出的药方并不新,那就是自由。在罗洛·梅那里,自由不是像罗尔斯或以塞亚·伯林所说的那样一种人身和政治权利,而主要是指人参与自己发展的能力,它是我们塑造自己的能力。自由是自我意识的另一面,随着人所获得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多,他的选择范围和自由也会成比例地增加,两者是相互成全的。在强调自由的同时,罗洛·梅没有忘记,自由与责任是不可分割的。他说:“如果一个人没有自由,那他就是一个机械的人,显然不存在诸如责任这一类的东西,而如果一个人不能对自己负责,那我们就不能把自由给他。但是当一个人已经选择了自己,自由与责任这种伙伴关系就成了一个绝好的观念。”“人类的目标在于自由、诚实、富于责任心地生活于每一个时刻当中。”(《人的自我寻求》,P233)但是,这种与责任捆绑的自由会不会一样令人厌烦,就像陀斯妥也夫斯基小说中的人物所说的那样,赶快找到能将自由这份礼物移交给他的人,自由这份礼物是人不幸生而有之的。
(本文编辑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