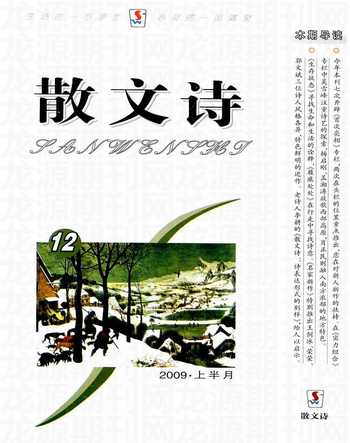木匠的锯子(外二章)
向 迅
隔一段时间,父亲就会用钳子把它们的牙齿一颗一颗拨正。一颗朝左,一颗向右……他对付这些小问题,就像对付孩子口中的虫牙和生活里的地雷。
父亲还会用锉刀把它们磨得尖锐,咯吱咯吱的,整个院子都在磨牙,把天空磨蓝了,灵魂的声音从父亲的手中闪出。时光,也被这些锋利的嘴巴轻轻咬伤。
父亲锯木头的时候,就会有一支调子单一的儿歌跳出来,迎合着他额头跳跃的汗珠,即使是大雪天,我也会看见穿着背心的父亲,在雪地里拉起一道阳光。
偶尔碰见木头里藏着一颗钉子,父亲要么绕开它,要么用斧头把它劈开。父亲怕伤了锯子。每次使用完,他都要给锯面打上青油,他说生锈的锯子不是锯子。
即使多年不用,父亲的锯子,依然闪着寒光,在那一排整齐的牙齿里,听得见木头的欢叫。然而,对于时光这把锯子,父亲却无能为力,只能跟着感觉走。
煤油灯
那些小小的神光,总在某一时刻闪现,赐予我灵感和面对黑暗的勇气。这些忽明忽暗的光,只有青铜铸造的灯盏才配拥有。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瓷瓶外加一根布条捻成的灯芯,它也能吐出春天的火焰,照亮穷人一揭见底的米缸和不屈的脊背。
这小小的亮光,精致,古老,唯美,为我嵌上第三只眼,好让我在窗下读书,画画,纠正错别字,为我引路并扶正我走路的姿势。
现在提起这些小小的英雄,仿佛念叨起一些陈谷子旧芝麻,可是,它们的光亮和温暖,始终在我的身体里储存着,并持续燃烧。
犁铧
我的犁铧与我背道而驰,二十多年,我也没有学会犁地的本领,只有父亲的犁铧沉睡在雨天,靠着发霉的墙壁。在春天醒来。
有人在春天的田埂上题诗作画,有人在秋天,用月光打的镰刀,反复练习收割。
父亲的犁铧,在黑夜里醒着。
这块混合着钢和铁的金属,在父亲优美的吆喝声里,一路欢歌,追一行行牛蹄,鞭子的歌声呼唤起阳光的热情。
在黑夜中醒着的犁铧,拉着越来越瘦削的父亲,飞奔过一个又一个水火不容的春天和秋天,他们有着怎样惊人相似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