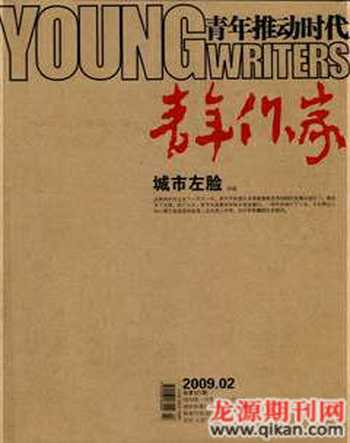表老·佛门
人狼格
表老是虔诚的佛徒,他的生命只是一个成就信念过程的载体而忽略了作为物质形式存在的肉身。他一生都内视深心地活在自己的信念里,年轻时曾到寺院受过戒,三十六岁时正式守戒修行。
他的母亲是我妈妈的姑奶,论辈下来他便是我的表爷爷,我们叫他表老。表老叩开空门后,我外婆家族的一个叫蒋宴的小外公给他磕了三个响头后便带走了他婀娜灵慧的妻子此里楚姆。表老和妻子此里楚姆在1932年生有一个叫天禧的弱智儿子,他不愿让妻子拖泥带水、步履沉滞地跨进她新的家门,于是把倍需关照的儿子留在了自己身边。
其实小外公蒋宴是能把生活打理得滴水不漏的汉子,他挑得起风雨、担得平苦乐,只是缺天缺地缺日月家里太穷,一直娶不上老婆。他也曾外出讨过生活,甚至想到过横刀立马、出没山林与土匪为伍,但目睹了土匪生活的血腥细节后彻底地收住了尚未迈开的步子。他曾看见了首先结束弱女子的性命再取其财物的毫无人性的打劫场面;也曾看见了土匪窝子里整夜都搂着刀枪只敢闭半只眼睛睡觉的匪首。他终究没有走上在刀刃上甜蜜的激荡生涯。此时,此里楚姆在这个生性沉默、壮实刚毅的男人身上看到了一种柔暖的光芒,她觉得这种光芒异常轻敏而又不可抵御地穿透到从未感觉存在过的生命潜层中去了,随之听到了自己在命运的泥泞中凝结而成的硬壳在碎裂、剥落,在似痛非痛的灼热里她突然含满了女人的全部柔软。她在这个瞬间感悟了女人真的是水,男人是河床,水在没有河床的时候只能是茫然一片,只有进入河床的水才能流淌成女人的定向,才能成为秋波与春水。她已经知道这个男人就是最后连骨头也会和自己朽在一起的人了,但是现在要离开这个她们姐弟两象风中的羽翼飘零的时候给了她们温暖的家和让她在天塌地陷的惊恐中感受了比大地更宽厚的曾经的丈夫时,此里楚姆还是感到了锥心捶肺的疼痛。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甸到处是云水苍茫、林荫蔽日,自然保持着对人的巨大庇佑力。日月炳天、江河行地,山水一片清华,所有的村庄都被神山圣水封存在自己巨大的臂肘里,葳蕤的古木和重叠的山崖隔绝了人对人的雕凿,被世事打磨成锋刃的人极少,更多的时候人们是拙补天成,顺行于道。但还是有许多事情在揭示着人心嗜血的本性,这片幽深寂然的土地只要用记忆的长矛随意挑开几下表象的土层,我们就会看到净土或乐土都是由泥土、尘土积聚的真质。此里楚姆和那杰姐弟俩本来是中甸安南藏族山村的黛峰翠峦间编织着藏家小孩的彩梦,她们毫无知觉灭顶的灾难像黑云已经遮天蔽日地从半空像鹰一样飞速地扑向她们。据说是东旺和安南两村因牧场、牧群的争端而结冤。在一个深夜里,安南村遭突然袭击,家被打冤仇杀的火光血光淹没了,父亲在慌乱中出逃。她们姐弟俩只记得跟着母亲一村又一寨地寻找父亲。每到一个陌生村庄,母亲都要爬到一个能够俯瞰村庄的坡顶去唱山歌,父母约定了用歌来进行联络,但母亲总是一次次孤苦空落地从坡顶上忧伤无助地下来。就这样,不知不觉已经千仞绝壁万仞峰,她们就像崖顶落下的流水离故土越来越远了。云雾苍凉、藤蔓牵衣,在惊悸不止中他们母子三人走白水过哈巴穿虎跳,一路沉沉烟霭、迷惘滞重地逆金沙江而上来到了里仁村。这一天,他们又爬到了村顶的一个庙子前,母亲向着山脚下的村庄又开始唱起了山歌。两个孩子虽然说不清但明显地感到母亲的歌声里多了一种苍悲、凄绝、直指内心的痛楚。
烈日当空的正午,衣着褴褛的姐弟俩在村子里一棵大垂柳下的凉粉摊边停了下来。柳绦丝丝缕缕从高空向大地垂挂下来,一条涓涓的细流从树底流过,大片的树阴下刚好是一些可供人坐卧的巨石,姐弟俩便在石头上坐了下来。此时还未到中午收工的时间,摊边无人,卖凉粉的妇人聚精会神地弹着口弦。一曲过后转身时妇人才发现两个紧盯着凉粉的藏家小孩,她一眼就看出流落中的小孩正在饥饿难耐,于是把口弦收进吊在胸前的小竹筒里,然后切了两大碗凉粉给小孩吃。妇人用纳西语问了一些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家在哪儿、为什么流落异乡等一些事,但姐弟俩一句也没听懂,只是对妇人满含感激地笑了笑。这时田里的人陆陆续续地收工,打凉粉的人也开始来了,柳树下的人多起来,姐弟俩让到离凉粉摊稍远的地方坐了下来。
妇人卖完凉粉收摊的时候,看到姐弟俩相互靠着睡着了,满脸的污垢里透着深深的疲倦,小小的躯体被一种厚厚的苍凉凄苦紧箍着。妇人心中顿生悲悯,于是走过去把他们摇醒后,边比手势边用纳西语说:“到我家去吧。”姐姐此里楚姆懂事地站起来帮着妇人收拾东西并抱起一个较重土陶盆跟在妇人的身后。
就这样,姐弟俩来到了住在村顶山脚下的表老家。
表老家被称为“多克郭”,意即坡脚下的那家。表老家田地多,一直到我记事,许多大块大块肥沃的水田都还在称为“多克格里”意即“多克家的田”。姐弟俩帮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四月的风暖暖地吹着,整片整片的蚕豆地在风的抚弄下把绿中泛白的叶底向天空一翻一翻的。姐弟俩在庄稼的绿波里一次一次地向生长五谷的厚土俯下身去,与他们年龄相仿的表老不喜欢到私塾读书,而更愿意和他们一起到田间几乎是在帮倒忙的劳动。在劳作的过程中因不会小心,总是把禾苗搞得一片狼藉,往往是“贡献”甚微而“损失”惨重,这种劳技方面的笨拙是伴随了表老一生的。因上山让人担心下地让人揪心,所以年轻时曾让他试着到私塾上课,但语言表达又极差,好像要讲出来了,可又咽了下去,似乎咽了进去,可又像要说出来,这种不吞不吐的表达状态使所有的学生都掉进了八千里路的云和雾里,故此也无法当私塾先生。据说表老其实是很有些肚才的,只是茶壶里边煮汤圆,无法倒出来。表老的优点似乎就是长得高大,心地善良。
碧绿的金沙江水在岸边茂密的柳林中隐隐闪闪着,天空里白雪皑皑的玉龙雪山倒映在明净的江面。江流如梦,姐弟就已经是一口纯正、流利的纳西话了,思乡的疼痛也渐渐被时光的纤指抽淡了。里仁为美,水天一色,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与这片土地融为了一体。
鸿雁掠影间,此里楚姆就已经出落成流光盈盈的小美人了,长得虽然不是很高,但浑身都鼓荡着生命的热浪。此时,表老的母亲发现儿子和此里楚姆总是形影相随,爱意绵绵,而自己也早把自己带进家们的姐弟视为己出,她们也把自己当成了母亲,于是索性给她们办了事。翌年,儿媳就给她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孙子,这使她喜不自禁。本来一直在柳树下摆着凉粉摊,但村里的人搞恶作剧,窜唆傻子阿德说她一直在用口弦 “阿德五德五雷故”地在骂他,所以傻子阿德就不能见她弹口弦,后来甚至就不能见她的凉粉摊,一见就砸,多年的凉粉摊不能摆使她的心空落落的。现在抱着孙子比抱着金砖银砖还舒坦,也就不再挂念凉粉摊了,并且逢人就乐滋滋地夸孙子是要把她家顶起来金柱银梁。
当然,孙子天禧一直没有向着奶奶所期望的成长,到了十来岁都鹿马不分,半天才挤出来的几句话也是含糊不清,直到她离开人世,已经成人的孙子也只是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啥也靠托不了的人,她是念挂着这个憨包孙子走的。老人去世后,里里外外都基本要靠此里楚姆操持。表老不善活计,重活轻活也得她去扛大头,日子是过得苦累一些,但家里田地多,只要手脚不停,吃穿是不愁的,总比那些要靠打工换粮吃的人家好多了。儿子是憨了些,丈夫也太厚道了些,但他知书识礼,春秋在心,所以时光在她的心里是踏实有序的流淌着。但是表老的内心却斗换星移,新的天地正在他的生命中定格。他一直对佛教经典中的那种博大但又平实得像土地一样的哲理着迷,现在突然悟到了“空”的真正含义,也突然明白了老子“贵大患若身”一语所含的大智慧。认识到自己不是自己的,那么,什么是自己的呢?儿子?妻子?房子?银子?是的,有、无、得、失都只是一个短暂的因果,包括自己的身体。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缘尽之时,一切皆散,一切皆幻。他觉得自己走过了贪瞋痴的沼泽,获得了一种只有进入简单的生存方式和干净的心念之下才会得到的清风明月的大自在,这是大舍之后的大得,他相信只有对短暂的舍弃才会获得永久的恒定,他相信只有看透今生的色、声、香、味、触的幻相,才能真正修正自己的行为,才能脱离生生世世的轮回之苦。他明白了 “天”所以是至私的,因此才做到了“用之至公”,这是佛门所言的“空”同理。所以,他虽然只是受了居士戒,但三十六岁那一年正式修持了沙弥戒,并说服妻子给她找了一个新家,开始了在俗人看来是虚幻而艰辛的佛徒达磨实践之旅。从此,直到一九七八年左右去世为止,在整个绝对压制个人信仰的 “阶级斗争”岁月里,表老沉默而坚韧地坚持着自己的信念,这在当时的八亿神州也肯定是屈指可数的,当然这和善良的村民们“斗争”得不太彻底有关,但我想无论如何他是看见了彼岸之永恒的。
妻子此里楚姆改嫁后,一生未婚的弟弟那杰依然住在表老家,但表老素食,并且食用的植物油也往往是有一顿缺十天,更多的时候是开水下菜,那杰过不了那样的生活,只有分灶了。直到表老去世后房子破烂得不能再住了,他就搬到了生产队的保管室去了,后来成了生产队的五保户。他是全村公认的柳哨吹得最好的人,清明节前后,油菜花金黄金黄的,麦田、绿柳、碧水都像晶莹的翠玉,大地弥漫着一种绿色独有的淡淡的牵心的忧郁,我觉得这时节故土的色彩情感是最具切透人心的柔软之力。我是有一年的清明,坐在坡上父亲的坟前俯瞰着故乡田园的满目碧玉,突然明白中国的古典文学为什么总是用绿色作为别离伤情的铺底之色。这时我才真正读懂了“寒山一带伤心碧”“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等句子里只有绿色才托得起的那份心碎,也突然明白了古人为什么总是在灞桥边折下柳枝来表达惜别时已经无法说出的心语。记得那杰爷爷总喜欢在这个时节,折下柳枝随手做成几个音色不同的柳哨,独自一人,在江边面江而坐,聚精会神地吹各种各样的纳西民歌。特别吹到“谷气”调时,他是已经进入了“谷气”里的那种忧郁、坚韧、一叹一顿、一扬一息的哲学层次的悲悯中,他不是用柳哨而是用心灵在表达了。我不知道已进入孤鳏暮年的他,此时的心海里是否又在涌动着一生多舛的浪迹。我会呆呆地坐在他看不见的地方,久久地沉落在他柳哨吹出的“谷气”里,品尝着对一个少年似乎是来得尚早的忧伤。
妻子走后,身边只有一个傻儿,表老作为佛徒,已经是无挂无碍做到了更彻底的放下,到解放前夕田地已价格低廉地基本卖光。这使他因祸得福,在后来的阶级划分中,已经是标准的贫下中农了。我七、八岁的时候,表老家成了我们小孩翻江倒海的乐园,那时正房的楼顶上已经没有片瓦了,梁柱都已腐烂,用泥土冲筑的墙体已大部分倒塌。表老、傻儿天禧、那杰爷爷三人都住在被称为“耳房”的小平房里。现在想来那是一个非常浪漫、诗意的古典家园,整个家园不用围墙,而是用密密的金银花树围栽而成,花藤的相互缠绕形成了自然的护院墙体。随着花墙的树根,一圈地引流着一股四季不枯的清水,这小股清流既用来浇灌园中的蔬菜,又作为饮用之水,护院的金银花树因水分充足而发得异常茂密。院子没有大门,入口处对竖着两根凿有几个碗口大小方洞的方木,方洞里穿着长根的圆木,用以遮拦出入的牲口。离入口处二三十米开始的小径两边直到里面的整个房前屋后的园子里都种满了各种鲜花,房后的花丛中长满了高大的梨子、海棠、李子、苹果、桃子等果树。艳阳高照的时候,表老喜欢坐在院坝里的草地上,脱下衣服内里朝上地晒着。不一会儿,藏在衣服皱褶里的虱子们就会成群结队地出来享受阳光,表老就不停地把它们捉了丢在草地里,他不忍心掐死,只是把它们抛弃掉而已。因为视力差手也笨,所以他永远也捉不完,故此一年到头只要天气好,这是他最繁忙的干不完的一项活。一到秋天,这里就成了孩子们的天堂,我是这个天堂里最严重的入侵者之一。我们不敢在院坝里停留太久,有几次在院坝里流浪的虱子爬到了几个小孩的身上。因表老年迈,眼差耳笨手脚也不灵,所以常常被孩子们捉弄,他当时是属于要打倒的牛鬼蛇神之列,自然也被孩子们欺负。有些时候,表老就坐在树下捡虱子,我们就悄悄从背后爬上树吃饱了果子才下来,在跑之前大叫一声表老才发现自己又被偷袭了。等表老笨手笨脚地穿上衣服,拿起石头、木棍吓唬我们的时候,我们或者早已翻过花墙溜之大吉或者躲进花丛,表老是怎么也奈何不了我们的。但也有吃亏的时候,又有一次我们慌慌忙忙从花墙上往外跳的时候,所有跳下的人都被一根扣状的金银花藤把脚钩了一下,全部都脚朝天地跌了下去。我摔在地面的时候,胸肚砸在一个大石头上,因而呼吸不得,手脚瘫软,表老吓唬我们而丢出来的石头不断地砸落在我的身边,从尿槽里舀了泼出来的溲尿天女散花般地洒落在身上,我是匍匐挣扎着挪出危险区的。也有一次,大叫一声后猛地躲进花丛时,一屁股坐在一抓锋利的三角刺上,屁股被扎成了马蜂窝,特别糟糕的是一棵毒牙般的长刺断进了屁股肉墩里。妈妈本来就对我们在表老家的捣乱行为感到非常生气,所以“活该!活该!”地大骂之外,对我的哭诉置之不理。直到睡下很久了,我都只能扑卧着并一直疼痛地哭闹,最后是姐姐起来帮我挑掉了屁股上的刺。又有一次在表老家闹得实在太离谱了,至今想来都还内疚。那天我们六、七个小孩又闯进了表老家,当时家里无人,小平房的门锁着。记不得是谁最先从隔板上边翻了进去,不一会儿,全都翻进了屋内。因为母亲威吓的余威还在,我是犹豫了一下,但最终还是身手敏捷地翻了进去,并飞快地加入到饿狼般抢食的队伍里。当时全村人都吃不饱,但是表老更饿,他是五保户,分到的粮食很少。现在表老节食留为下一顿的小半锅面块被无数只脏兮兮的小手一抓而空,甚至在热灰里烧过的几个干辣椒也被几只小手闪电般地抢走,最后连神龛前几个干瘪了的供品水果也一扫而光。这次行动不知是被谁出卖的,没过两天我们就被老师罚站在全校的同学面前,并且我还被冤枉说硬是生生的吃掉了表老的一个小南瓜。这是胡诌,谁都知道生南瓜是不能吃的,老师也似乎不太相信,所以没有深究这“生吃南瓜”的事。这好像是我最后一次在表老家干的坏事了,倒不是我突然长大懂事了,而是接下来发生了一件母亲和表老共患于难的事,并且严格说来是母亲连累了表老的。
有天夜里妈妈做了一个恶梦。她梦见自己死去的母亲得了重病,而且是睡在一片阴风惨惨的地里,她醒来时觉得自己母亲的呻吟还留在耳边。恰巧,早上出工到田里不久,一头久久都无法驯化为耕牛的烈性黄牛在架犁的时候,从犁架下挣脱出来愤怒地把一个人顶在田埂上,差点要了那人的性命。于是人们把它拴牢后,用三五台拖拉机拉来一堆石头,一群强壮的男人从拖拉机的挂兜上往下砸石头,把牛砸得口吐鲜血,直到活活砸死。这使母亲坚决认为这头牛就是她母亲投生的,把牛砸死的地方也就是她梦中自己的母亲病卧呻吟的大致方位。妈妈在极度的悲痛中,毅然地请表老念经超度。但是这个秘密的法事活动还是被村民们雪亮的眼睛发现了,于是两人被一同抓去开批斗大会。召开批判大会的那天,全村人吃的是一大锅先煮着一种草根,最后再搅进去一点粗糙玉米面的叫做忆苦思甜饭的稀粥。那天许多人都好像没吃饱,我也是只吃了几口,觉悟低的人还悄悄地回家拿点盐撒上再吃,甚至有一个人公开地说他不能吃这种没有盐的草根稀饭,一下肚就胃疼,所以五七、五八年饿得两眼只见星光的时候都不敢吃。那天,觉悟高一些而稍微多吃了一点的人,确实大部分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流涎、恶心的现象。因为表老一生吃素,母亲也不吃牛肉,所以对他两“特殊照顾”,让他们吃用牛油炒的包谷饭。他们是搞迷信活动遭批判的,我觉得很丢脸,所以没有向前靠近他们,只是远远地看见母亲披着一件蓑衣和表老一起在革命群众中间,并排站着在用餐。表老吃一嘴吐三嘴,在不断“哦哦”的呕吐声中完成着用餐任务。母亲回家后对我说牛油炒饭基本上是被她狼吞虎咽了,只给表老留了几嘴。母亲好像对遭不遭批判倒不是很在乎,但表老遭到逼着吃牛油很使她愧疚万分。我看见母亲烧着香,跪在香案前反复祈祷说吃牛油的罪过不要让表老承担,请菩萨把全部罪过都加在她自己的身上,因为这是她连累了表老。后来表老来家里时,她还不断地自责是自己连累了表老。表老倒是反而安慰母亲说这是他自己前世的业障,所以是必须承受的,只有经历了它们,自己的功德才能圆满。并且说所有外在的持修形式都只是给内心搭建一个清净的空间而已,关键是修心,修一颗清净心。其实表老和我家是亲缘加法缘,关系是深厚一些。母亲是表老的侄女,父亲在去世前的几天里,也在表老家里皈依佛陀,拜表老为师,所以,我家到现在还留有几本表老手抄的《心经》《观音经》《日光经》《月光经》等经书。后来我长大一些的时候,曾有人对我说父亲是被表老的迷信害死的,但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其实父亲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后来甚至发展到精神分裂症,整夜整夜都恍恍惚惚,似睡非睡,不断出现幻觉……。当时没有医疗条件,父母在无奈的情况下,期望皈依佛门来躲过这一劫。但是父亲还是在一个精神出现重度分裂的深夜里,在不断的幻觉里跳进了金沙江。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表老的身体已越来越差了。他每天都会拄着手杖走走停停地从山坡脚下的家里下来,到村子中间的商店门口坐一会儿,然后又走走停停用很长的时间才能回到家。他的身上总会背着一个用旧布自己缝的口袋,他会把每一张有字的小纸片都捡进口袋里,到家后把有字的纸片都烧完,灰烬就倒进干净的溪流里,他曾多次对我说不要糟蹋文字。母亲用微薄之力照顾着表老,每当家里做一点凉粉、豆腐之类的东西,她都会让我送去。不管人们信不信,表老也会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为村民指点一些迷津。有一次他从商店门口回家,途经和钟义老师家时,他家正在打灶,表老拄着手杖闭目而立。过一会儿就说今天不能打灶,今天打灶是冲伤了在锅边转的主妇。 和 老师不以为然,但打灶之后的第三十天,妻子在山路上滑跌倒后被沉重的背子勒在脖子上,等亲人找到她时早已断气,这使 和 老师对表老的星相学很是折服。
大概是在一九七八年的秋天里,表老去世了。有一天,我们曾一起在表老家里翻江倒海的好伴跑来告诉我说表老坟上的墓门石裂成两半了,他说表老真可能是上天了,还忧心忡忡地说表老会不会原谅我们这帮“穷凶极恶”的人。天禧已四十多岁,他喜欢和我们十多岁的小孩一起到处跑着去看电影。有时跟着“谎报军情”的电影消息跑上一二十公里是常有的事,到这个村说是下个村放,到下个村时又说是再下个村放,最后一个个沉在黑暗深处的村庄都只会在寂静里对我们发出几声狠狠的犬吠来表示“歉意”,等筋疲力尽地回到家时往往已过午夜,并且要在饥肠的咕噜声和母亲的责骂声里入眠。这样的夜晚,天禧是我们从未空缺过的最忠实的铁杆队员。他以一颗浑蒙的心和我们小孩一起品味了所有那个年代独有的电影赐予的酸甜,每当看过一部电影他都要用数天的时间来进行手舞足蹈地重复讲述着电影里的情节,过分激情澎湃的叙述使本来就结结巴巴和吐字含糊变本加厉,人们谁也没有耐心完整地听完他的一句话。所以,他常常只能对着比他更傻的阿戈得讲述,但奇怪的是一个傻子从来对另一傻子更不感兴趣,当天禧过分地手舞足蹈时阿戈得还拿起石头或木棍恶狠狠地发出威胁的低鸣,天禧本来就有些惧怕阿戈得,所以只得赶紧悻悻地逃离。故此更多的时候是只能自己对着自己“演出”。小小年纪的我也是很不应该地萌发了希望被女人的某种柔暖深裹的欲恋之心,确切地说,那是一场朝鲜电影《一个护士的故事》之后开始的。当时在我小小少年的眼里,电影中那个护士是足以彻底唤醒男人对女人的亲情、恋情、性情等全部欲望的完美女人。当她在战火的硝烟里猛然倒地时,我男人的天性轰然觉醒,我第一次勃发的比自己的年龄大比自己的身体重的爱顷刻间便失去了目标。至今记忆犹新,她牺牲后我整整一个星期不思茶饭、神情忧郁。在那个岁月里,我就这样苦涩与甜蜜、艰辛与快乐交织甚至绞痛中激情燃烧地成长着,当然,天禧也是激情燃烧地老着。
去年,我无事就爬到高山上表老闭关修行的仙人洞里去了一趟,在洞口往里倾斜的遮风避雨处,表老写的那副“似洞非洞仙洞,有门无门佛门”的对联还清晰可辨,字虽不算好看,但很有些道骨神气暗藏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