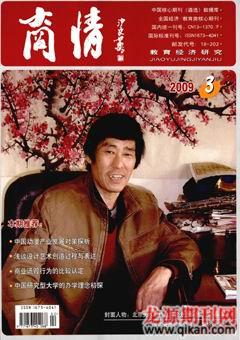女性生命意识在苏醒
冯红岩
【摘 要】80年代,李昂创作的《杀夫》成为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她以锐利的眼光扫视着依然处于封建枷锁下的“饥饿”的女性人群;从“性”的暗孔探视着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热切的关注着她们坚强的从男权强压下的弱势阴影走向生命意识苏醒和人格独立的过程。
【关键词】生存状态 精神状态 性 生命意识
一、从陈林市母女看女性生存困境
提到生存困境,我们不免能想起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几乎面临一切生存困境的阿Q:基本生存欲求不能满足的生的苦恼(《生计问题》)、无家可归的惶惑(《恋爱的悲剧》)、面对死亡的恐惧(《大团园》)等等。《杀夫》中的陈林市母女就是这样挣扎在“黑暗的坑”( 曹禺《雷雨》序:宇宙正象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号呼也难脱这黑暗的坑。)中任如何挣扎仍不免绝望的女人。即使有最终的反抗,采取的方式也是极端的、绝望的和以牺牲自己生命为代价的。
《杀夫》通过两条线索勾勒出两代人的命运。陈林市与母亲,因孤儿寡母被家族夺走财产,赶出家门,以乞讨度日,又因饥饿难忍母亲被诱奸,后被家族惩处,从此失踪。陈林市在叔叔家做尽各种苦差事,象保姆一样在饥饿中长大,却又被叔叔以可换得长期吃饭不要钱的肉票嫁给凶残暴虐的屠夫陈江水。从此陈林市便受尽百般的肉体折磨和精神凌辱以及惨无人道的性折磨。这是一对悲剧的女性,是在封建父权、夫权制度摧残下的牺牲品。在女性毫无经济地位的社会状态中,女性只能是苟延残喘的生命躯壳。
对基本生存欲求的渴望时刻贯穿在陈林市母女两代人身上。李昂曾把《杀夫》比作“吃不饱的文学”,把之后创作的《暗夜》称作“吃得饱的文学”是有其根源的。在《杀夫》文本中:母亲身上体现出的“吃不饱”:母亲为一团白饭与军人交媾:“阿母嘴里正啃着一个白饭团,手上还抓着一团。已狠狠的塞满白饭的嘴巴,随着阿母唧唧哼哼的出声,嚼过的白颜色米粒混着口水,滴淌满半边面颊,还顺势流到脖子及衣襟。”因饥饿而变得贪婪的形象让我们目不忍视;在族人发现并踹开军人时,母亲“仍持留原先的姿势躺在那里,裤子褪至膝盖,上身衣服高高拉起,嘴里仍不停的咀嚼着。……哭起来,断续的说她饿了,好几天她只吃一点蕃薯签煮猪菜,她从没有吃饱。” 女性的尊严和人格在此时是无从谈起,更无任何价值和意义的,甚至对于女性本身来说仍是一种对自身的认识的无意识。陈林市身上体现的“吃不饱”:只因每天陈江水带回家的肉,陈林市让自己充当性具的角色。在丈夫放弃为自己提供经济资助时,她因饥饿去养鸭,以期通过鸭子下的鸭蛋换点粮食。愿望破灭后,曾去讨要过饭,甚至冒着对鬼神的畏惧偷吃了祭拜用的面线。
对神灵等迷信观念的极端敬畏,是陈林市陷入绝望困境的精神要挟,也是她生命最原始的状态迸发和苏醒的关键威胁。封建社会非人道的野蛮的精神氛围恐吓了毫无生命意识的女性人群。“信仰和祭拜仍是必要的”, 阿罔官时刻提醒陈林市。“兽魂碑”的存在,普渡和打醮的祭拜,在神权的威慑下人的灵魂变的惊慌与无助。神权下人的精神危机在女性无意识的状态中实质上对生命自身的恐惧。这种畏惧与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对神权的畏惧如出一辙。“然而饥饿抵的过任何心中的恐惧。”生存的恐惧掩盖了所有精神的信仰。所以才有陈林市为填饱
肚子不顾一切的挣扎。
二、从阿罔官及金华看女性欲望需求
阿罔官是《杀夫》中又一重要的女性角色,若不是陈林市最后对陈江水绝望的反击,代表了
封建主义桎梏下女性自我意识反抗意识的觉醒,仅从本文的人物塑造上,阿罔官其形象的丰富性甚至更甚于懦弱、卑微、谨慎的陈林市。
第四节中,儿媳和彩对阿罔官鄙夷的叫骂:“如不是你这老查某,手弯向外拐,”“谁不知你守的是什么寡,守到阿吉的眠床上去,谁不知你三天两头就得跑去给他干才会爽……”在陈林市身上体现的“性”是林市作为丈夫发泄私欲的性工具而存在的,是兽性和血腥的男权强制下的“不得已”,是封建婚姻制度、夫权制度的牺牲;而“性”体现在守寡多年的阿罔官身上,则是女性自身本性欲望的需求。阿罔官可以自觉地去找阿吉,以寻求性的满足,这个时候,性具是不存在的,正如陈江水在金花身上能寻求到的性满足一样,人作为人,这是本性的最原始的流露。但是阿罔官生活的时代却是三从、四德等贞节烈操传统观念钳制人的时代,封建社会的妇女观,如传统强加在妇女身上的枷锁,妇德观念的恪守让女性在眼睁睁瞅着男人纵欲行天下,而女人卑怯的谨守妇德,谨小慎微的铸造着妇女天经地义的贞节牌坊。所以才造成:陈林市经常会在夜半发现阿罔官“躲在隔壁紧邻的矮土墙角, 脸缩皱在一起展现出一个笑容,却十分诡异,眼中漾着一层水光,咄咄逼人”。一个因“性”欲不能满足而扭曲心灵的悲剧人物。同时,也因为儿媳无情的揭露,使得不得不采取上吊的方式来“殉礼”“明志”。在女性经济地位获得提升的同时,才是性解放、性自由的的开始。而此时的阿罔官只能享受偷来的欢愉和满足,在此“偷窃”的过程中最终导致自己产生作为一个女性的变态性心理和卑怯心理。这类人物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其实很多,诸如朱湘的《渌竹山房》中变鬼的姑婆等。但这毕竟是女性的生命意识流露的最初形态。其实之后到达性解放、性自由的时代时,无论是女性作家还是女性文学,以女性为代表的群体坚定的、毫不畏惧的通过千百年来只有男性随心所欲的“性”自由改变了自己的地位,从身体上的某种解放最终获得精神上的胜利解放。
金华是陈江水的情人,不仅能满足陈江水的身体需求,同时能满足陈江水的精神需求,但是这样一个人物,却注定只能是“后车路”上的“攒食查某”。女性处在不可避免的边缘地位无所依附。刘保昌在《启蒙传统下的经典戏仿》中,也曾提到“从小说本文来看,造成陈江水与陈林市生活不幸的根源,乃在于性生活的不和谐。”不过这个观点来自于陈林市和金花在陈江水的性需求度的比较中得出。在文本中,金花是作为女人形象出现,而陈林市是作为女性具形象出现的,而同时陈江水对金花和陈林市的身体乃至精神的需求上的对比,致使暴露出陈林市作为女性形象的自身弱点导致部分削弱了陈林市在此过程中所受的凌辱。但这不能改变作品揭示的:男权至上的封建观念才是导致陈林市悲剧的根源。
三、最后
陈林市和阿罔官却真正论断了“食色,性也”人类这两大基本生存欲望。在食与性的交相蹂躏下,封建父权和夫权甚至封建神权的压制下,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注定是最悲哀的。但女性的觉醒和反抗也是最决绝的。
《杀夫》中的几则新闻暴露的文章主题异常明显:谋杀亲夫乃是社会道德问题,岂能以神经患病为由加以恕有;还待当局严加办理此案,以息舆沦,以匡社会风气;为应社会舆论、民俗国情,将谋害亲夫之淫妇游街示众;寄望这次游街,可使有心人士出力挽救日愈低落的妇德。千百年来,中国的妇女在封建礼教的禁锢下,权利和自由备受蔑视。在清晰的点出主题的同时,有行刑前理直气壮的解释向世人宣称:陈林市在此时已经是觉醒后的陈林市,已经坚强的从夫权下从备受凌虐的性具、父权下谨小慎微的弱女子、神权下畏惧神灵的生命躯壳走了出来。当陈林市在恍惚中奋起挥舞屠刀的时刻起,蕴藏在其生命底层的生命意识才陡然苏醒。这正是李昂创作的特别,文章最后的陈林市在神权的惊吓和夫权的性折磨中的确可以理解为精神失常,神志不清。但作者用几则新闻明确了陈林市杀夫后意识的觉醒。似是矛盾,实为巧妙。
参考文献:
[1]古继堂.简明台湾文学史.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
[2]江少川.台港澳文学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王曙芬,程玉梅.从性禁区透视女性生存——浅析李昂小说中的女性与性.辽宁大学学报,1999,1.
[4]李槟.本文的特征及意义生成——重读李昂的《杀夫》.南京晓庄学院,2002,3.
(作者单位: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