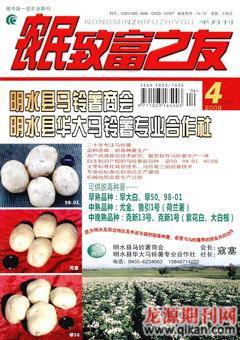巩固人均地“权”,催化人地分离
张 华 尹秀峰
为了加快新农村建设,从根本上破解“三农”难题,需要对现行的土地家庭承包制进行再改革,以利于农村资源有效配置和规模经营。这种改革,就是在坚持家庭承包制不变的基础上,再建立一种促使土地相对集中的制度,克服承包制固化分散经营与兼业等模式的缺陷,使承包制扬长避短。具体改革路径是国家通过对承包地转让收入低于经营收入的差额进行补偿,鼓励农民进行大规模的承包地有偿转让,以实现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即巩固人均地“权”,催化人地分离。
农业是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的产业,如何配置土地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制度,是生产队集体的土地同社员集体劳动进行配置,虽然解决了土改后、合作化前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和土地规模效益的矛盾,但是统一分配的“大锅饭”体制,却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所以,理论上的规模效益被实际中的“大锅饭”体制一扫而空。家庭承包的土地制度改革了“大锅饭”体制,实行了承包土地和家庭劳动的配置,调动了农民“多劳”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有了空前的发展。但是这种配置方式,使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和土地规模效益的矛盾又重新出现,而且越来越突出。这也同样在影响生产力的发展。
这似乎是土地家庭承包和规模经营二者不能兼得,只能互相排斥。由此产生了一种土地私有化的思路。这种思路的理由是,土地私有化了,一方面可以克服“大锅饭”中农民不关心土地收益的弊端;另方面又能加速土地集中,解决分散经营和规模效益的矛盾。可是,这种思路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逻辑。在土地私有制中,土地的私有权会加速土地集中,但在土地集中的同时,会使农民出现两极分化。无论如何,土地私有化在社会主义中国是行不通的。
土地不能私有化,土地又不能“大锅饭”式的集中经营,这是不是等于说“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呢?不是的。改革就是扬长避短。改革,不是改掉它能够调动“多劳”的积极性那一方面,而是要改进它限制农民去“多劳”那一方面。那么如何改变土地的分散经营呢?
理论上有两种思路:一是承包制不变,用承包土地的经营权人股,进行合作经营。这种方式,在理论上虽然可行,但在实践(这种形式现在已经出现了不少)中,有两个操作难题,一个是很难适应农民入股和退股的自由变化,另一个这种合作组织需要较高的管理水平,农民很难适应,搞不好又变成了过去的那种“大锅饭”。二是承包制不变,鼓励和引导土地经营权大规模的有偿转让,促进土地向种田能手和有经营能力的农民那里集中。它的组织形式是大小不等的家庭农场。
变土地分散经营为规模经营的土地制度再改革,就是在坚持土地家庭承包长期不变的前提下,鼓励和引导土地经营权的有偿转让和相对集中。土地经营权为什么要“有偿转让”,而不是无偿转让,就是因为土地家庭承包制没变,使土地经营权也没变。所以,土地有偿转让的理论前提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关系不变。但是,只有法律关系不变的理论前提,还不能实现大规模的土地转让,或者说只是有偿转让的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还需要有经济前提。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转让方转让后的土地收益不能比转让前的土地收入少;另一个是受让方经营受让的土地有利可图。
由此可见,这项对承包制的再改革,包含三层逻辑关系:从理论层面看,土地有偿转让的理论前提是土地承包权不变,否则,就不是有偿转让;从经济层面看,土地有偿转让的经济前提是出让后的收益不能比出让前的收入少。否则,就不会发生转让行为;从操作层面看,土地有偿转让的现实性是受让土地的经营者经营受让土地有利可图,否则,就不会受让土地。鼓励和引导土地大规模有偿转让制度确立后,“人均地权”的承包制,不仅没有被改掉或削弱,反而会在制度创新中得到扬弃和巩固。所谓制度创新,就是承包制形成的承包地对农民的制度性束缚在新制度下被解除,促进了人、地分离,合理流动,有效配置。人、地分离,合理流动,一方面。加速了土地集中,使我国农业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实现了规模经营,这样才有其现代化可言;另一方面,受让土地的农民专门种地,转让土地农民专门从事非农产业,专业化取代了兼业化,那时农村的工商业和小城镇想要不发展都不可能,这是经济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