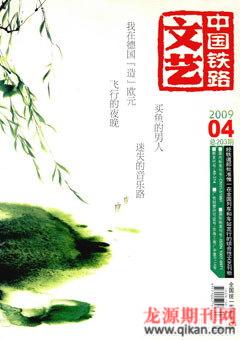旅途花开
屈爱英
由广州至苏州的火车,途经韶关时,视线里的村落和山野多了起来。一路上,铁道两边是低矮房子,古旧的院落,杂乱,长些藤蔓植物。房子不远处,一片丘壑,有太阳的日子里,支一顶遮阳伞,农人就着这点庇护蹲在地里锄草、摘菜。少部分田里种着水稻,绿绿的,齐膝高。荒着的田里,牛站着,不时地晃动尾巴。远处的山不很高,林木稀疏,估计那些大片空缺的位置如今都铺着这脚下四通八达的铁路。不做树木为枕木,怎么说还是树的形象。平静的景象,重复着,重复着。过了韶关也就出了广东,下面就是湖南再就到江西,到浙江再到上海、苏州。想必这路上的景致都不过如此吧,安稳与古旧里透着沧桑的沟壑。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人们……
想这些事的时候,留意到车厢内,那个站在前方的当兵的小伙子,他黑黝黝的脸膛也正对着窗外,眼神凝重。正考虑他会想些什么问题。后面一位干部模样的老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迈着不太稳当的步子往前凑,丝质的长衫划过我的手臂。站在过道里的人都让了让,愣神的当儿,他走到了当兵的面前,“小伙子,你去坐一会吧,你到苏州,要一直站,这样我老人家过意不去。”
当兵的有些腼腆,只重复说:“我不坐,就站着。没事儿,没事儿。”
老干部回座时,衣角又晃荡在我肩膀上。这拥挤的车厢,因为这么一次让座的对谈,竟生生有些尴尬,这站着的坐着的都放低了对话的音量。十八个小时的车程呢。
后来,只听到老干部对着手机讲:“我在车上了,车上有个当兵的,真是不错,给我让位子了。是武汉武装部XXX连X队的,你给我查一下子。真是个好人,我现在很好,你放心。好,就这样。”
这些话音刚落,车厢里有人小声议论着。而当兵的依然怔怔地看着车窗外,没有表情。我随之看出去,这间隙的时间,看到有一堵墙,塌下了一半的残缺的土墙。由于地基高,这墙也显得很高大,墙面上爬满了紫红色的喇叭花,对着太阳正开得蓬蓬勃勃,叶子也都抖擞利落地垂挂着。花开了很多朵,有些三三两两地密密挨着,誓要大手笔地点缀这墙。由于这是一堵弃置的墙,四无依附,这独立的墙面显得异常生动。花叶和藤和墙身,旁若无人的开着、屹立着。一种强烈的和谐,一种短暂的美。匆匆一眼,那墙那花过去了,再回头远远看时,模糊得有如画幅。定格了几秒,我在脑中保存了它,一直开着。
后面路上的景致有些什么,我竞看不太很清。因为,当兵的在接了个电话后,他对大家告辞说:“战友发出邀请,叫我在衡阳一聚,我得先下车了。”在老人万分感谢声中,他背着简单行李下车了。
后来,车厢里不再有尴尬的味道,老人的电话也安静了很久。而我,一直想着那堵花墙。隔日到了苏州站,在出口处,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竞又看见了那当兵的,他也看见了我,挤出一丝狡黠的笑,然后自顾走了。
我发现,那笑,像是开放在干漠里的花,猎猎的,艳艳的,让走在颠簸旅途中的人,多出新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