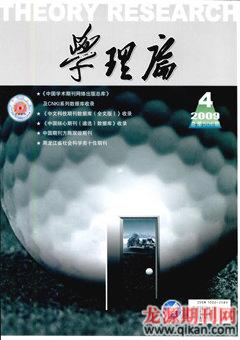解读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的审美价值
周 英
摘要:苏轼在《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中能将审美体验具象化,“迁想妙得”地化虚——审美体验或对某种特殊感情的亲身感受为实——具象化。由“形似”落脚到“神似”,达到了心和物的默契,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关键词:化虚为实;不即不离;心物默契;审美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4—148—02
苏轼贬谪黄州时,其好友章质夫曾写《水龙吟》一首:
燕忙莺懒花残,正堤上、杨花飘坠。轻飞乱舞,点画青林,全无才思。闲趁游丝,静临深院,日长门闭。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
兰帐玉人睡觉,怪春衣、雪沾琼缀。绣床旋满,香球无数,才圆却碎。时见蜂儿,仰粘轻粉,鱼吞池水。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荡,有盈盈泪。
这首咏杨花词写的形神兼备、笔触细腻、轻灵生动,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因而受到当时文人的推崇和赞誉,盛传一时。苏东坡也很喜欢章质夫的《水龙吟》,并和了一首《水龙吟 · 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苏轼将这首词寄给章质夫时,还特意告诉他不要给别人看。章质夫慧眼识珠,赞赏不已,也顾不得苏东坡的特意相告,赶快送给他人欣赏,才使得这首千古绝唱得以传世。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东坡《水龙吟》咏杨花,和韵而似原唱;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才之不可强也如是!”[1] (p208)并脱口称赞:“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2] (p209)步韵填词,从形式到内容必然受到原唱的约束和限制,尤其是在“原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的情况下,“和韵”要超越“原唱”实属不易。但苏东坡却举重若轻,以其卓越的艺术才华写出了这首“和韵而似原唱”的杰作,真可谓旷世奇才。苏轼此和韵能得到王氏如此首肯,主要是因为它有着强大的艺术魅力和极高的审美价值。
艺术家的使命是将审美体验具象化,而“一切审美方式的起点必须是对某种特殊感情的亲身感受”。[3] (p3)因此,这就要求艺术家能够“迁想妙得”地化虚——审美体验或对某种特殊感情的亲身感受为实——具象化。要完成化虚为实这一创作过程的起点,恰恰是对实——外在世界的一种审美方式的切入,也就是另一种的由实为虚,然后才能化虚为实。这种由实为虚、化虚为实的过程看似是一种循环过程,可实质上艺术品正是在这种螺旋状的循环过程中孕育而生的。清代画家方士庶曾在《天慵庵随笔》对此做过形象的阐释:“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虚而为实,是在笔墨有无间——故古人笔墨具此山苍树秀,水活石润,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或率意挥洒,亦皆炼金成液,弃滓存精,曲尽蹈虚揖影之妙。”[4] (p150)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就是“曲尽蹈虚揖影之妙”的典范之作。
《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的起句就不同凡响,“似花还似非花”在对所咏之物杨花切入的同时建立了两个相互平行对应的切入点:细小而色泽平平的杨花一下子就进入了一种模棱两可的难堪。它是否能与花为伍就难以让人说清,现实世界里杨花所固有的外在特征是随风飘舞,同时在词人情感世界里它又恍惚朦胧,像花还是不像花,它是否就是在自己眼前飘来晃去的小生命?这就向我们展示了两层齐头并进的平面:现实中的实物杨花“似花还似非花”;情感中的虚象杨花之生命也“似花还似非花”。作者在切入所咏之物的刹那间,既把握住了杨花的外在特征——实,也“以物观物”,以生命去体会生命,进入了杨花的内在世界(一种生命的存在)——虚。实与虚的平行切入在似与不似间调动起词人的审美体验——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感感受。正如法国美学家雅克·马利坦所说的:“从一开始诗性直觉实际上就整个地包蕴了富于诗意的事物,要求整个地穿越它。”[5] (p111)词人自觉不自觉地建立了一种中国诗学的咏物原则:咏物时要做到不即不离,若即若离,这就使词作具有了一种朦胧之美。所以清人刘熙载一语中的地地指出:“东坡《水龙吟》起云:‘似花还似非花,此句可作全词评语,盖不即不离也。”[6] (p119)紧接起句“也无人惜从教坠”,使杨花进入了一个更加难堪的境地。偌大世界竟没有人怜惜它,任凭它飘来坠去,悄悄地开,悄悄地落,没有谁向它瞥上一眼。从另一个层面看,词人是否已体会到了这飘来坠去的小生命的痛苦孤独。无人怜惜,无人对话,无法在世人面前来展现自己,这可能就是人生最大的悲哀了。词人沉重的感情已默默化在“也无人惜”这四个字上。只有词人向它深情地瞥去一眼,“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杨花就这样抛开了它依恋的枝头——家,在无人问津的路边流浪。此情此景它又多像个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孤独者,一个青春路上的匆匆过客。因此,在词人活跃的诗性思维中,“无情有思”便蕴涵有千种风情。有词评家认为,苏轼在此是暗用了杜甫的《白丝行》中的“落絮游丝也有情”和韩愈的《晚春》中的“杨花榆荚无才思”的诗意。其实不然,这里的“无情”恰恰是以“也无人惜”为其运思的前提。因为杨花面对的是一个无情的、“也无人惜”的冷漠世界,而这冷漠世界就暗示着杨花居住的情感世界的丧失,作为孤苦伶仃的杨花不得不“抛家傍路”,即使“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具有一种难以诉说的“有恨无人省”的悲哀,故曰:“无情”。同时,就是这种无情又恰恰孕育着它生命中所固有的对失去了的情感世界的企盼,所以它“抛家傍路”流浪在外,这就有了最深切的痛苦情感体验,故曰:“有思”。“无情有思”这看来是两两相悖的命题,也就形象地传达出杨花乃至词人最为炽热的感情。因此,词人生命中的杨花越发多姿,更为动人:“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细细的杨柳枝条,细细的愁思,痛苦地翻卷萦绕,青春的柳眼,娇美地张开,又困倦地闭上。它在痛苦和企盼、现实和希望的双重焦灼里徘徊。这时的杨花是花还是人,是情还是景,都难以说清了。花和人、景和情,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这正是苏轼所追求的“求物之妙,如细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7] (p5)的那种境界,也是英国诗人柯尔律治所激赏的“使无生命的东西具有生命,也就是观察者将自己的生命注入了他所观察的事情之中”[8] (p79)的那股生命涌动的激情力量。就在这激情涌动的节律中,词人“随物宛转,与心徘徊”(刘勰语),小小杨花已被词人纵宕放飞:“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炽热的生命企盼,殷殷的情感寄托,孤独的痛苦存在,此时都凝结为这一千年梦幻。杨花灵光一闪,梦魂神魄,便随风飘得很远、很高,去寻找它生命和情感的归宿,去寻找那位让它梦绕魂牵的翩翩少年。可惜,无情的现实世界——叽叽喳喳胡乱鸣叫的莺,最终击碎了它春天里的梦,它不得不又回到了冷漠的现实世界,企盼和寄托就此破灭。
词的下阕“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是一种似非而是的诗思组合。在“不恨”与“恨”之间,乍看词人情感的落脚点在“落红”之上,好像词人在为“落红难缀”而深深遗憾,故曰“恨”;杨花飞尽,好像无关痛痒,故曰“不恨” ——好像词人的感情发生了旁移。“似花还似非花”的杨花,经过一番追求和失落的生命轮回之后,受到了词人的冷落。其实不然,词人在情感的涌动中突然插进了两句市俗的“画外音”:小小的杨花能算什么,谁为你的飞尽遗憾了,别自作多情,我们遗憾的是西花园里花枝招展的鲜花的凋谢,遗憾的是春天的走失。这爱憎分明的“画外音”,就好像给词人炽热的情感劈头盖脸泼来了一盆冷水,也是无情的世俗世界对杨花的公开遗弃。世态炎凉、人生冷暖可以从这两句读出。请转过脸来看我们的词人如何过活:“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在经过了一场风风雨雨后,冷风冷雨丝毫没有动摇词人对杨花的一往深情,他关注着经过风雨洗礼后的杨花的命运,面对春天走失的世界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呼唤:杨花你在哪里?世界静得可怜。春天消失了,杨花消失了。在词人湿漉漉的目光里闪现出一池浅浅的积水,积水上飘来飘去,无处扎根的细碎浮萍。此时,词人固执地认为那流浪的浮萍就是杨花的化身,就是杨花的托生,他仿佛觉到了杨花的存在,一个小小生命的存在。词人如潮奔涌的情感竟如此平稳、自然地落在了星星点点的浮萍之上。从渺小的形象上可以看出词人情感的高贵;从无华的绘景状物中,可体味到词人生命的绚烂。面对一件艺术珍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观点,不同的审美观点获得不同的审美享受,这是正常的。但是当两件同类艺术珍品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审美价值比较问题,“不容妄为轩轾”是不成立的,必然有个孰优孰劣的评价和选择问题,非此即彼。前面说过,章质夫的这首《水龙吟》形神兼备,笔触细腻,轻灵生动,是一篇难得的佳作。然而,只要与苏东坡的这首“和词”加以比较,章质夫的“原唱”就相形见绌了。大凡诗词,“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因此,只做到形神兼备还不够,必须做到“有境界”。观章质夫的“原唱”,虽然描写细腻生动、气质神韵不凡、“潇洒喜人”,但终归是“织绣功夫”,“喜人”并不感人,因而较之“和词”在“境界”上就大为逊色。苏东坡的“和词”,“先乎情”,“以性灵语咏物,以沉著之笔达出”,不仅写了杨花的形、神,而且写景“言情”,在杨花里倾注了自己的深挚情感,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达到了高超的艺术境界,从而获得了永恒的艺术生命。这是章质夫的“原唱”所望尘莫及的。
《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不愧是苏东坡婉约词中的经典之作。我们不仅从中领略了豪放派诗人婉约风格的一面,体验到诗人感情丰富的内心世界,而且这首词独具的艺术魅力,给予了我们不尽的审美享受。
参考文献:
[1][2]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3][英]克莱夫·贝尔.艺术[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4]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5][法]雅克·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M].北京:三联书店,1991.
[6]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美]艾布拉姆斯.镜与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9][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刘惠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