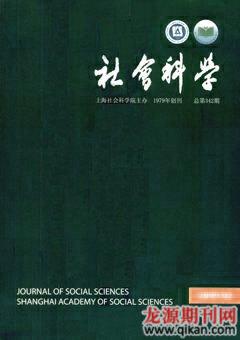一个被忽视的命题:大城市公共组织的传统因素
林 拓
摘 要:大城市治理作为全球性难题,其公共组织是备受关注的关键之一。一般认为,地方政府组织传统已经难以适应当前发展,故而传统因素被忽略乃至摒弃。“大城市改革运动”在欧美一度盛行,但在美国却屡屡受挫;对此,奥斯特罗姆等重新发现了150多年前托克维尔所观察到的美国地方政府组织传统的重要作用,历经一个半世纪城市化进程的挑战与调整,它不仅生命力至今犹存,更将影响美国大城市的治理方向。放开来看,不少发达国家的相关变革在经历表面价值的纷繁变化之后,也逐步深入到所根植的制度、社会与文化传统之中:大城市公共组织的传统因素是影响未来的重要命题。
关键词:大城市;公共组织;传统因素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2-0093-08
大城市发展已经成为城市化进程的重要趋势,世界城市人口从上世纪初不足15%到世纪末接近50%,大城市数量也相应增加,1900年世界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只有40个左右,而2000年已增加到400多个,还出现了一大批千万人口的大都市及城市群,本世纪大城市发展的重要地位将更加显著;与之相伴随的是,大城市治理已经成为全球性难题,其中公共组织是备受关注的关键之一。一般认为,大城市是全球化背景下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其治理的困难在于地方政府组织的传统已经难以适应,故而传统因素时常被忽略乃至摒弃。
实际上,面对这一全球性难题,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相关的种种改革应运而生,各种争论纷至沓来;但在经历表面价值的纷繁变化之后,相关探索逐步深入到所根植的制度、社会与文化传统,它将深刻影响改革成效。美国作为全球屈指可数的高度城市化国家,恰恰经历了这一艰难历程,其经验和教训尤为值得重视。大城市治理一度成为美国面临的最严峻难题,但此起彼伏的大城市改革运动却屡屡受挫。20世纪末期反思“大城市改革运动”的思潮逐步兴起,其中以奥斯特罗姆(注: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行政学家和政策分析学家,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有关美国地方政府与大城市治理等的理论集中体现在《美国地方政府》、《大城市区的政府组织》等著述中。本研究采用的《美国地方政府》是井敏、陈幽泓翻译的,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其中万鹏飞教授所作的“中文版序”对奥斯特罗姆相关理论作了准确把握与阐发,是本研究重要依据之一。)等最具代表性。耐人寻味的是,对于美国地方公共组织的观察,奥斯特罗姆所处1980年代正值美国大城市区快速发展之际,而早他一个半世纪的托克维尔所处的1830年代却是美国剧变之初,就在这两个相去甚远的时间截面,两者的发现却是相通的。不仅如此,奥斯特罗姆反复提醒人们要重视托克维尔关于如何理解美国地方政府传统的忠告,大城市治理不应忽视自身传统,还应从美国创建者们的传统经典中寻求理论支持(注:参见奥斯特罗姆的《合众公共国的政治理论》等著述,有关评论可参见[美]罗伯特·B.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第3版),扶松茂、丁力译,竺乾威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哈金斯在奥氏相关理论的评价中指出,它提供理解当代美国政府结构的分析工具与基本原则,而“源于这些原则的意识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政治文化之中”(注:[美]小罗伯特·B.哈金斯:《<美国地方政府>英文版序》,载《美国地方政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那么,美国早期地方政府组织究竟具有怎样的特征?这一传统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怎样的挑战呢?为了更好地探寻奥斯特罗姆的学理脉络,我们的考察首先从大城市治理的问题情境着手。
一、大城市公共组织变革的困境:寻找潜在逻辑
美国城市化进程处于领先地位,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1940年大城市区(metropolitan area)人口占全国总人口近一半,成为大城市区国家,2000年大城市区人口高达80%以上。对于大城市区最为直观的认识是,大量人口和产业高度集聚形成相互依存的地域整体,因而相应地普遍认为,大城市区的整体化发展必然要求公共组织的一体化安排,才能确保大城市区的协调发展(注:Ostrom,Elinor,“Metropolitan Reform:Propositions Derived from Two Traditions”,玈ocial Science Quarterly,53(1972) ,pp.485-490.);但美国地方政府组织却一直呈现出庞杂而多端的外观形态:在50个不同州的法律下,8万多个县、乡镇、自治市、学区、特别区以及数以万计的准政府组织集合而成美国地方政府组织,大城市区更为纷繁复杂,似乎是杂乱无章的混合体,是历史偶然积累所形成的乱象,不少文献称之为“百纳被”模式(crazy-quilt)。这种复杂的“割据”状态被认为是大城市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资源配置来看,大城市发展必须集中整个地区的充足资源,但辖区的权力分割却导致各辖区资源相对缺乏;从管理效能来看,这种分割既难以拥有先进管理能力和专业人员,又缺乏统一行动乃至责任错乱;从市民选举来看,多种管辖权并存使市民不清楚社区发展的责任主体,导致他们难以履行自己的选举权利;从城郊关系来看,“二战”以后城市与郊区的分裂与冲突,成为美国社会政治的中心问题之一,其城郊之间政府辖区的分割被认为是重要原因之一 (注:[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等《美国地方政府》,第65-68、71页。)。凡此总总,无不触及一个根本问题:美国地方政府组织传统的多样性形态难以适应大城市区的一体化发展。
于是,相应的变革思路是力图将大城市区作为整体建立单一的政府,推行市县合并,克服传统的权力分立等等。例如,当时美国的知名学者威廉·安德森在1966年为经济委员会提交的《地方政府现代化》报告提出如下建议:美国地方政府的数量至少应该减少80%;应该大力削减相互交叠的地方政府层级;普选应限定于决策部门人员的选举,实行“强市长制”的政府行政长官要优于“议会—经理制”;每个地方单位都应该只有一位行政长官,所有行政机构和公务员都要向他负责,等等(注:[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等《美国地方政府》,第65-68、71页。)。对此改革的倡议直至20世纪90年代依然持续,被誉为“美国最热门的城市问题专家”的戴维·腊斯克等就积极倡导重建大都市区政府等主张(注:David Rusk ,獵ities without suburbs,玏ashington D.C.:The Woodrow Wilison Center press,1995.)。据此,地方政府组织多样性形态的重组势在必行。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所谓的大城市改革运动“却正经历着最严重的政府失败问题”。尽管大城市改革运动确实曾取得一些成效,如新兴建筑与外来投资的增加、居民人均收入的提高以及贫困线下的人数减少,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规模化的政府组织及其高度集中的公共服务存在严重的不经济现象,例如,就平均单位而言,公共服务的人均支出、市政府雇员数量等等与规模成正比例;政府单位的合并没有直接带来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接踵而至的是对大城市改革的普遍抵制,根据奥斯特罗姆的统计,1949年至1977年的28次合并选举中仅成功3次,其中印第安纳波利斯与马里恩县的市县合并仍保留了一些独立的服务部门与自治组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市县合并或者说一体化重组。
事实上,美国大城市却出现与一体化重组相反的倾向,即政府数量不断增加、政府规模不断减少。王旭教授将这一趋势形象地概括为“城市地域扩大、政府规模变小”。他的研究发现,20世纪美国地方政府总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二战”后尤为如此,2002年美国地方政府数量多达 8.8万个,且大多数规模很小,2/3的市镇不足5000人,半数面积不足 1平方英里,大都市区内更为突出,平均每个大都市区有 100个地方政府(注:王旭:《城市地域扩大、政府规模变小》,《求是学刊》2008年第1期。)。
显然,美国大城市公共组织变革面临严重的困境。需要指出的是,英国明确依据大城市改革理论进行的地方政府全面改革在1972年立法、次年开始实施,相似的思想也导致了联邦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典、丹麦和挪威等国的改革,尽管这些国家的改革也有不少问题,但是,奥斯特罗姆坦言,类似构建大城市单一政府的改革“在欧洲取得很大成功,但在美国却遭遇了明显的失败”。实际上,这种差别是与美国地方政府组织的传统密切相关的。奥斯特罗姆一语道破,“托克维尔在描述美国地方政府特点时使用的逻辑和在20世纪里一直居主导地位的‘效率和经济改革运动以及‘大城市改革运动的逻辑是不同的”[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等:《美国地方政府》,第76、86页。)。那么,托克维尔究竟发现其自身隐含着怎样的潜在逻辑呢?
二、回望托克维尔:在错综复杂中发现传统
面对大城市政府组织错综复杂的外观形态,奥斯特罗姆认为,当年托克维尔的观察与目前的状况很相似,而早在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就明确指出,“表面上的紊乱外观,起初会使欧洲人认为美国社会处于完全无政府状态;而在他们深入观察事物的本质以后,就会发觉原来的认识不正确”(注:[法]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00页。)。
的确,对美国地方政府组织的分析,托克维尔首先直击美国地方政府潜在的核心原则。他从社会状况把握民主政制,认为民主在美国不仅是一种政制,还是一种观念、情感、民情(注:倪玉珍:《托克维尔理解民主的独特视角:作为一种“社会状况”的民主》,《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人民主权是美国地方政府的核心原则,“人民主权原则主宰整个美国社会”,“要想讨论美国的政治制度,总得从人民主权学说开始”。故而在《美国的民主》上卷考察美国政府、政治制度、司法权、政治审判、联邦宪法等之前专门有一章讨论“美国的人民主权原则”。 正如《独立宣言》指出,“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所应有的权力组织,必须按照人民的意愿,是最能保障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的”。就此而言,公民需求与公民参与是美国地方政府组织的中心问题,而人民主权原则的方向性影响至少体现在:一是政府职权的分配,尽管当时不少国家也有人民主权相似的思想,但是,美国的人民主权原则更多的则是基于对个人的强调,除非个人侵害社会,否则每个人都是自身利益最好的和惟一的裁判者,并由此扩展到政府职权。“在美国,乡镇和县的组织都以同一思想为基础,即认为每个人都是仅与本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最好的裁判者”,“乡镇和县只负责照顾人们向共同利益”,这实际上为美国政府组织的联邦化奠立了基调。二是政府组织的选择,“人民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凡事皆出于人民,并用于人民”,“人民自已治理自已”,人民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政府组织,并广泛参与其中,这实质上为美国政府组织的多样性开启了大门。不仅如此,托克维尔的观察理路并不停留于政府组织外观形态的表面考察,而是深入到人民主权原则所发育成长的基层乡镇。他认为,乡镇“是自由人民的力量所在,乡镇组织之于自由,犹如小学之于授课”,“在没有乡镇组织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虽然可以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府,但它没有自由的精神”,“在各种自由中最难实现的是乡镇自由”,而美国恰恰“在乡镇内部享受真正的、积极的、完全民主的共和的政治生活”;美国乡镇自由与欧洲国家大相径庭,托克维尔这位熟谙欧洲政治的法国贵族对此差别一目了然,他在与欧洲大陆国家的反复比较中认识了美国的乡镇自由,“在欧洲大陆的所有国家中,可以说知道乡镇自由的国家连一个都没有”。“在欧洲,统治者本人就经常缺乏乡镇精神”。可以说,美国地方政府组织的传统也就此分途。更重要的是,乡镇具有极其重要的奠基作用:“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政治生活都始于社会的上层,然后逐渐地而且是不完整地扩及社会的其他部分,在美国,可以说完全相反,乡镇成立于县之前,县又成立于州之前,而州又成立于联邦之前”;当各殖民地还承认宗主国最高权力的时候,“君主政体仍被写在各州的法律上,但共和政体已在乡镇完全确立起来”。简言之,从历史和逻辑上看,基层乡镇是公民参与及地方自治的根基所在,我们暂且称之为“基层本位”(注:值得一提的是,托克维尔还专节讨论“乡镇规模”,乡镇虽然近乎独立王国,但乡镇的规模不大,“没有大得使全体居民无法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地步;另一方面,它的居民人数也足以使居民确实能从乡亲中选出良好的行政管理人员”。可见,实现共同利益与选举熟人管理是确定规模的两条基本标准。托克维尔还论述了乡镇自由在当时美国的地域差异以及乡镇的组织构架与运行特点,囿于篇幅暂不讨论。),而这正是美国地方政府组织传统的基础。
紧接着的问题是,乡镇以上的地方政府组织又是如何构架的呢?按习惯理解,地方政府组织结构在纵向上形成不同层次的等级体系,在横向上同一层次的地方政府边界明晰,行政区域内部的权力中心是单一的。
然而,当时美国却是另一番情景,成长于乡镇的人民主权原则进一步扩展到乡镇与州乃至州与联邦的关系中:在自身范围内的事务是自主的,在共享利益上的事务是服从的,两者发生冲突则诉诸法律;“新英格兰的居民没有一个人承认州可以干预纯属于乡镇的权利”,“对于全州的公共义务,它们非尽不可”。
几乎在美国建国之时,同样的观念就应用于联邦与各州及地方的管辖权限之中,各州在它自身事务方面拥有自主权,而联邦政府作为各州的联合体被授权对各州共有的社会事务负责,故而地方政府组织的层次之间“不存在等级制度”,美国“行政权结构既不是中央集权,又不是逐级分权”。直至今天,在美国人看来,各级政府在法律的授权范围内都是最高的,它们之间不存在行政级别的高低问题。奥斯特罗姆进一步认为,这正是联邦主义的题中之义,也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发展,在宪政法治下“每个人都服从法律,不允许任一种政府变成控制整个社会的永久的、支配性的权力中心”;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语言来表述美国体制中的权力是不适当的,“更恰当的描述是联邦化”,我们称之为“联邦模式”。
与“联邦模式”直接相关的是地方政府组织的“多样安排”,即为了满足不同的利益团体提出的要求而产生大量的履行不同类型服务的地方单位,它们相互交叉并存于同一个地域,并以有限权威实现着治理。例如,为了排水、防洪等专门目的而建立起来的特别区,就有权处理任何跨行政边界的相关任务;于是,兼跨众多管辖地域和分别独立选出的官员共同组成的独特的行政管理体制发展起来了,也就是说,“有多少种职能就几乎有多少官员,执行权被分散到众多人手中”。
当然,宪政法治是确保这种政府组织形态运行的基本条件,囿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同时,多样安排还体现在政府与政府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等关系之中,托克维尔认为,在美国不能仅仅依靠被称为“政府”的这个高度正式化机构来理解地方自治的运作,大量的基层单位和其他组织为公民的参与提供了多种可能,确切地说,地方政府组织并不能涵盖美国地方公共组织的全部内容。托克维尔曾这样描述, “使旅游美国的欧洲人最吃惊的”,“一切都在你身边按部就班进行,但你到处看不到指挥者”,也没有一个支点可以作为“行政管理的中心”,“不存在行政权的半径所辐辏的圆心”(注:多种安排还存在于不同地域之间。美国地方政府组织几乎在形成之初就有很大差别,新英格兰州各镇以直接民主制为主,其他州则以代议制为主,县的建制出于行政的考虑,只有非正规的有限的权力;而实行奴隶制的南方和边疆各州,私人产权管理的种植园相当于乡镇规模,县相应成为地方政府最基层的设置;中西部各州的乡镇也是最小的政府单位,市镇是自治机构,县为州与乡镇的中间单位。)。
至此,我们不难看到,以人民主权为核心原则,以基层本位、联邦模式、多样安排为特征,托克维尔所勾勒的这一美国地方政府组织传统的基本轮廓已经呈现,而地方政府组织错综复杂的外观形态,正是其传统特征的外在表现。
三、在城市化挑战中重建传统
然而,这一传统是在美国城市尚未充分发展的前提下形成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必然使之面临严峻考验。城市发展之于地方政府组织,绝不仅仅是由市取代县的建制转变,更涉及政府关系及其内部结构等诸多方面的变化。果然,不久以后它就受到了冲击。
尽管托克维尔准确反映了19世纪早期美国地方政府组织的状况,但是,正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美国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标志,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新移民不仅仅是土地的开发者而成为产业工人,城市由小城市、中等城市再发展为大城市,新兴大城市成为大型工业中心,等等。正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美国地方政府组织的传统面临着经济政治剧变的严重挑战:从经济结构的剧变来看,大量的公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在城市中涌现,而城市政府作为公有企业的法人代表却有能力利用征税权力来积累资本与私人企业竞争,也可能利用政府权威扼制私人财产,城市政府的自治性在经济竞争中有蜕变成私利性的可能;从政治结构剧变来看,人口的增加扩大了选民规模,在选举中仅凭个人努力的竞选难敌那些拥有良好组织支撑的候选人,成功的组织者在其候选人当选后就相应成为政府的后台“老板”,老板们甚至可以操纵多个权力中心,而公共设施的权力寻租、城市老板与城市政党的勾结等等又可能使城市腐败大行其道,城市老居民对权力可能落入大量新移民之手也忧心忡忡;如此等等,有的甚至惊呼,“城市已构成对美国文明世界的威胁”(注:[美] 托马斯·科克伦等:《企业时代:工业美国社会史》,纽约1961年版,第250页,转引自王旭《美国城市化的历史解读》,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347、348页。),城市政府的性质与地位受到普遍的严重质疑。
在这一背景下,城市政府的自治权力被重新检讨,州的重要性相应突显,具有标志意义的迪龙法则确立,其中心内容是:市仅仅是州的创造物,仅拥有州赋予它的权力,州掌握着地方政府的生死大权。任何由州给予的权力,州都可以剥夺、修改和收回万鹏飞:《<美国地方政府>中文版序》,载《美国地方政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这一法则1903年和1923年两次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认,成为州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法规,城市政府成为州的下属单位,州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等级化倾向加剧。在奥斯特罗姆看来,这开启了一个“掠夺城市”的时代。
不过,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市的独立性是人民主权原则的自然结果”,在联邦主义宪政的前提下自治市的独立性仍沿着自身的逻辑发展,相关努力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地方城市政府自身的改善,为反对机器政治与老板统治的斗争,进步党人等掀起了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全国性改革运动,城市委员制和城市经理制等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则是州与城市政府之间关系的改善,在反对城市老板的斗争中又进一步引发了限制州立法机构权力和扩展地方社区权力的州宪法变革,随后地方自治宪章的纷纷确立,意味着将联邦主义应用到州与地方城市自治政府的关系中,“由托克维尔刻画的19世纪早期美国地方政府的活力和自治性基本得到重建”(注:[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等:《美国地方政府》,第37页。),或者说,美国地方政府组织的传统在日益加剧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挑战中并没有中断,而是在调整中重建。
就在地方政府组织逐步调整之时,美国城市化进程又产生新的重大变化,20世纪20年代从人口和工业向城市的集中转为向郊区的扩展,政府活动的范围和规模大幅扩展;加之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以及美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等等,地方政府内部管理能力的提高与管理成本的控制日渐得以重视,引发了对效率和经济更大的关注,而企业效益提高所积累的经验成为改革的重要参照。于是,一场“效率和经济改革运动”(the Efficiency and Economy Reform Movement)开始了。遗憾的是,尽管这场运动相当程度上是围绕着城市发展的新变化展开的,但它追求的却是以企业效率等为参照的表面价值,实是与美国地方政府组织自身的传统相悖离,奥斯特罗姆认为“它所基于的假设是:通过精简地方政府内部结构而又不分裂和分散其权威,可以提高政府的效率;通过统一行使政治权力和更加倚重一支专业公务员队伍,商业公司的效率特点在地方政府里也会出现” (注:[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等:《美国地方政府》,第40、63页。)。这种思维取向几乎一开始就注定这场改革运动的命运,虽然有所成效,但不少努力却是事与愿违,大致体现在:一是城市政府的体制改革,在传统的弱市长制的基础上,强市长制、议会—经理制、委员会制等进一步发展,大城市大多采用强市长制,而议会—经理制在中小规模的自治市被广泛采用;二是地方政府的合并与联合,为专门服务而设立的特别区的合并与联合,对于城市、郊区和乡村之间正在趋向融合的社会生活具有重要作用,但地方自治政府机构的合并与联合所形成的组织规模化反而带来高交易成本、反应迟缓等弊病,况且自治市合并的动因部分地是由于公用事业企业以及一些利益集团发现对付一个大城市要比对付众多的小自治市更容易;三是公务员制度改革,城市公共事务的日益专业化越加要求公务员专业水平的提高,相应的措施层出不穷,但却抑制了公民在公共服务中应该发挥的作用;四是地方政府的国家化趋势,联邦政府以项目支持与援助等方式不断介入地方城市事务,但地方政府的集权化倾向却越加明显。
正因为这场改革运动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20世60年代成立的曾经是该运动积极推动者的全美政府关系委员会到了80年代以后也逐步发生了转变。不过,就在80年代,大城市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生活的主角,正如奥斯特罗姆所言,“美国人民曾经面对过有关地方政府的适当组织形式和地方政府间关系的适当设置问题。今天,有关地方政府最严峻的问题就是大城市区的治理问题” (注:[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等:《美国地方政府》,第40、63页。)。那么,美国地方政府组织的传统是否依然需要呢?
四、现代大城市公共组织:传统还有生命力吗?
前文所述,美国“大城市改革运动”一度占据主流地位,它具有以下基本主张:一是行政区域的整体化,大城市及周边地区组织成一个政府单位,确保对整个区域作出统一的决策;二是自治政府规模化,地方自治政府的合并联合,尽可能避免权力分割、节制运行成本;三是内部结构的层级化,即大城市行政管理体制形成等级化的垂直构架;四是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最高行政长官由公众选出的议会监督与指导,但行政管理事务都在最高行政长官的指挥下协调进行。与“大城市改革运动”相似的思想曾经在欧美国家颇为流行,引发不少国家相应的变革。
实际上,这一思想拥有公共行政思想与城市空间理论的双重支撑。就前者而言,早在19世纪后期,威尔逊在《行政学研究》这部公共行政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就强调,任何政府都存在一个占支配地位的中心,通过等级体制的单一权力中心可以提高行政效率、强化行政责任;此后,威洛比、古利克等则提倡以统一、层级、分工等原则追求行政的高效率,而怀特在20世纪中期更发现公共组织中存在着行政权力向上一层次政府的集权和向单个行政部门的整合的两大趋势,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在奥斯特罗姆看来,威尔逊政治科学的基本原则是“权力被分解得越多,就越没有责任”,并把自己所处的一代人看作是宪法批判主义新时代的开端,实是与联邦主义传统的决裂(注:参见[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被遗忘的传统:宪法层次的分析》,毛寿龙译,载麦金尼斯主编《多中心治道与发展》,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就后者而言,20世纪30年代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具有深远影响,他认为,城市中心地体系是根据市场、交通和行政最优原则而形成的,中心地有等级层次之分,1940年德国学者廖什发展了中心地理论并提出经济区位论,“二战”以后,中心地理论在美洲、西北欧各国被广泛接受,并在相关规划中应用。至于跨地区城市问题的解决,更是强调建立统一的大城市政府,“每个大城市的各个空间区域是被许多密集的网络连在一起,这些网络几乎穿越所有的个体社区,但它们并没有在更高的政府级别上集中”(注:Downs,Anthony,“The Devolution Revolution:Why Congress Is Shifting a Lot of Power to the Wrong Levels”,獴rookings Policy Brief,玭o.18 (1998))。显然,就两者关系来看,权力中心与城市中心、政府体系与城市体系、行政绩效与城市效率等诸多方面均存在着某种暗合,以一体化为取向的安排似乎成为大城市公共组织改革的当然逻辑。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倘若我们循着当年托克维尔的观察理路,先深入到城市基层,那么,不难发现,在大城市地区表面浮现的所谓整体性之下,反倒是基层邻里或社区巨大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及其动态的交叠变化。邻里或社区在美国大城市内部普遍存在,很多志愿者组织也是以邻里为基础形成的,市民偏好、生活方式及其所面临的社区问题等在不同的邻里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而高度集中的政府却很难对此作出反应,致使效率降低、服务退化以及行政责任的迷失,弱化市民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市民往往指责太大规模的政府“巨大而僵硬”;大城市区内部的小地区比大城市本身更具同质性,况且一般家庭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相似的邻居们,“导致的结果是向具有更多同质性需求模式的服务地区的演变,而不是向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演变”。同时,大城市正在经历着空间模式的巨大变化,从高度集中的单一中心模式向分散的多中心模式转变,这种转变相应刺激了建立新政府和新机构的需求,当居民和商业迁出老的中心城市 ,他们需要多种类型的新服务,往往寻求新的政府组织形式以实现其需求(注:[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等:《美国地方政府》,第81页。)。于是,大城市改革运动受到邻里组织运动的冲击,许多地区在不同邻里建立“小市政厅”、以邻里为基础的咨询委员会等,有的甚至提出“还政于邻里”的竞选纲领。1998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乔治·利伯曼进行大量调查后宣称,“亚地方政府”(sub-local government,指邻里或社区政府)是 21世纪民主真正的希望所在(注:Thad L.Beyle,玈tateand Local Government,2000-2001,玏ashington,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 Books,2000 ,p.166.)。邻里或社区政府的建构在大城市政府组织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这里,当年托克维尔所观察的政府组织传统的“基层本位”隐然可见。当然,托克维尔时代基层主要是指乡镇,而当前更多的则是指大城市的邻里或社区。
如果说,美国地方政府组织如何实现公民需求与公民参与,是当年萦绕托克维尔心中的关键问题,那么,这更是当前大城市所面临的艰巨问题,而公民需求与公民参与的实现方式也直接影响大城市公共组织的构建。
一般说来,在选举社会,投票是公民需求表达与实现的基本途径,服务项目的设立与服务方式的确定等可采用直接投票的方式,但城市公共服务往往是提供给社区整体难以兼顾具体局部与个人;“投票选出候选人也不是表达服务需求的最佳途径”,候选人一般向中间选民的意见靠拢以增加赢选的可能性,“在任何一次选举中,独立的问题越多,在公民的偏好和候选人的决策之间的调和就越困难”,大城市内部复杂多样需求的满足更为困难,即使是邻里内部同样存在很大差异,况且不同的公共服务在不同城市地区具有不同效率,不同公共服务的规模效益边界也相去甚远;这诸多难题无疑加大城市管理与服务的复杂性。因此,解决的途径不仅仅是投票确定服务或选举候选人,而是选择怎样的公共组织形式:所有的公共服务均由一个政府提供并不是理想选择,而对于这一难题的破解,采用的恰恰是根植于美国传统的联邦式组织安排,即“运用许多共存的、相互交叉的政府单位”,不同的公共服务由多样交叠的政府组织分别负责,成为市民实现不同需求偏好的通行选择。奥斯特罗姆认为,多样化的政府格局要比包揽一切的集中单一政府安排更能准确表达市民的偏好,也更能针对不同的服务职能来确定恰当的边界范围 (注:[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等:《美国地方政府》,第92-97;212、213;60页。),美国大城市政府组织的多样安排正是以市民多样需求为内在支撑。在他看来,这并不意味着为人们所诟病的地方组织“巴尔干化”,即完全分化到居民小区层次,而是兼顾不同社群利益之间的相互依赖(注:[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毛寿龙译,载[美]迈克尔·麦金尼斯主编《多中心体制与公共经济》,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至于跨地区城市问题与公共服务,也以联邦化方式探索大城市联邦(metropolitan federation)的构建,由它负责较大规模的服务,而较小规模的服务仍由市政府负责。实际上,多样需求弹性与组织规模的刚性所导致的政府规模困境,也相应地得以很大程度的缓解。在联邦模式中,政府单位的边界和规模不必强求划一,不同的政府组织单位可以根据服务集群需求和服务类型要求相应地作出有绩效的具体规定,从而实现自由活力与统一秩序之间的均衡。
对于公共组织的多样安排,正如当年托克维尔所指出,不能仅仅局限于“政府”这一高度正式化的机构来理解;同样地,“现今的地方政府不能仅仅限于发生在那些作为政府单位的自治法人和机构中的活动”,“它们的运转取决于它们所依托的丰富多彩的以各种志愿性组织形式出现的志愿活动这种制度背景”;而大城市公共组织的多样安排为公民的广泛参与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公民的参与诉诸于更广阔的范围而不仅仅局限于政府单位自身的空间。正是基于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大城市公共组织的观察,奥斯特罗姆进一步在提出的“治理”理念(注:[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等:《美国地方政府》,第92-97;212、213;60页。),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被国际学术界所重视,现今已为人们所熟知。同时,公共服务供应与生产的链接也不局限于政府组织内部,而是扩展到在政府与政府之间、政府组织与私人组织乃至其他之间所形成的更广阔的公共组织空间,而这种关系模式甚至具有产业结构的特征。例如,水几乎是城市的生命线,水的供应从城市郊区的水区到市政府的水资源部门等不同机构,都可以直接为终端用户服务零售部门,也可能与州或联邦的大规模水资源开发部门合作,他们的共同努力合起来可以被看作一种水资源产业,几乎就像私营部门中生产商、批发商和分销商等构成的产业链;这种关系模式仍可以在教育、警察、福利、卫生、消防、交通及许多其他服务领域中找到。在这里,并没有公共权力的层级制,但“每件事情都是有规则地运作,操作者却无处可见”,“这正是托克维尔所观察到的行政管理体制的现代版本” (注:[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等:《美国地方政府》,第92-97;212、213;60页。)。奥斯特罗姆在阐述其地方公共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上述公共组织安排的合理性,对此的评价及中国大城市公共组织变革的可能模式,笔者拟另文讨论。
显然,大城市政府的规模化、行政管理等级化以及权威中心单一化等等公共组织一体化的变革取向,曾盛行于不少欧洲国家,有的也确实取得诸多成效,但在美国却难以奏效;这不仅在于欧洲型与美国型大城市存在显著差别等诸多原因,还在于美国地方组织传统因素的作用使然,这一以基层本位为基础的联邦化与多样化安排的传统在城市化进程的冲击挑战中不断调整,至今生命力犹在,当前具有特色和绩效的美国大城市公共组织形态与之密切相关。应该说,全球大城市公共组织在高效性、灵活性、回应性等基本方向的追求上可能是一致的,但其具体变革的路径、形态与方式等等却具有多种可能性,这除了取决于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与城市类型等变量以及特定的国家情境之外,传统因素的作用尤为重要。尽管奥斯特罗姆试图论证美国经验的普适性,但就像他自己所指出的美国大城市变革要重视美国传统,其他国家也同样不能忽略自身的传统。我国大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不少大城市与城市群正面临着公共组织及其现代治理变革的诸多困难,就此而言,大城市公共组织的传统因素这一影响未来的重要命题,我们仍有很多研究亟待展开。
(责任编辑:周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