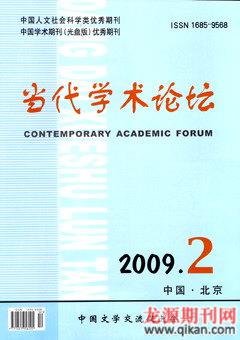精神为“游”
邢红静
摘要:从中国古典文化的原初意义上来说,人类的“精神”参天地万物而在“此在”中实现超越,进而产生文明。这个“文明”指的是本源上亲近自然,实现人类与万物的相互交接与亲密无间的融合,从而达到精神上的高峰体验,人类的物质财富有节奏地、适量地增长。精神的精神性存在也是一种“此在”,它在它的存在中与它四周的存在发生交涉,并在存在中对自身的特质与状态进行领会,决定着自己的生存。是其所是并如其所是,它揭示自己,并把自己交由我们去沉思。精神为“游”。
关键词:精神;精神的本质;精神的可行性
一、“精神”的含义
精,从米从青。青是形声字,表示颜色的丹(后演变为月)为形,生(后演变为)为声,青的本意指东方色,即指蓝色或深绿色。精乃形声字,米为形,青为声,本意指选择米粒。
神,从示从申。示在篆文中是会意字,由二和下部的三竖组成。二表示天地,三竖表示日月星,合起来表示通过观察天上星辰图像,来考察和获知人世间的变化。示的本意是让人了解某种现象、事实或信息。神,形声字,示为形,申为声,本意指传说中的天神,也泛指天神和地祗。
“精”与“神”组合成词的“精神”最早见诸于《庄子》:“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及,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化育万物,不可为象,其名为帝。”(《庄子·刻意》)。《逍遥游》则展现了水击三千、扶摇直上、御风而行的无拘无束的精神状态——精神乃流动的,游动的,赋物成形,随风而化,“精神生于道”(《庄子·知北游》),“精神,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列子·天瑞》);“精神”又具有内在自持性、坚固性与含蓄性,成了一种高妙的行而上存在:“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周易·系辞上》),“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遇行。”(‘庄子·逍遥游》);在外在敞开性与内在自持性的“精神”之间,尚且存在着二者的结合状态,即“精合”(精神与外物相应合):“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荀子·正名)。
二、精神的本质与本源
海德格尔指出了本质与本源的意义:“一个事物从何而来,通过什么它是其所是并且如其所是。某个东西如其所是地是什么,我们称之为它的本质。某个东西的本源就是它的本质之源。”
毫无疑问,从米从青、从示从申(电)的“精神”只能来源于大自然的变幻莫测,上有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下有五谷丰登四时的色彩纷呈,参天地而化育人生,澡雪精神,通过眼耳鼻口舌,通过神经脉冲而抵达大脑中枢这一物质载体。而精神的本源,即其“如其所是”,则有必要进行深入剖析。
从“精神”的含义看来,这一古老的词语中隐现着飞扬灵动的“世界”与雄浑沉着的“大地”意象。因而,精神的生生不息、化育万物乃成为可能,从而“是其所是”并且“如其所是”。那么,是否可以说,精神的本质在于“游”与“自持”,即在其敞开的世界性与返归和凝守的大地性?
在古老的中华典籍里,可以看出精神的自成体系性。精神的精神性使其在本源上亲近万物生灵,在本质上则处于“游”的自由状态(“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逍遥游》;“游心乎德之和”《庄子·德充符》;“游心于淡,和气于漠”《庄子·应帝王》;“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这是一种通天彻地、玲珑剔透的自由,一种活泼泼的超脱,即“一种心灵的审美”,故其四际八荒无所不至,开天辟地无所不能,聚散离合不拘形法,交通于“世界”;但是它并不是如此这般脱离出去,而是牢牢攀系于其“大地性”之上,以一种宏阔辽远的深层内蕴把持住其宁定的单朴,在头脑中掀起重重风暴,大开大阂之际收声养气。“精神”就是外观于自然而自成其心灵智慧体系的大地与世界。
三、精神被援引的可行性
精神的动力在哪里?精神有一个“世界”,在“大地”与“世界”的对抗中精神实现了其澄明无碍。那么,精神可以招致风聚云起的动力在哪里?雅克?莫诺《偶然性与必然性》讲述了这样一段话:“如果在地球上出现了脊椎动物,并且开始了从两栖类到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的奇妙的发展系列,这是因为最初有一条鱼‘想要登陆进行探索,可是在陆地上却又动弹不得。就是这一条鱼由于行为发生改变,结果引起了选择压力,从而产生了四足动物强有力的肢体。”“想要”竟然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它唤醒主体心灵深处的渴望与倔强,攀爬着如丝如缕的成功的希望,在这份幻想与憧憬的支持下,鲲终于变成鹏,绝云气,负青天,水击三千,扶摇万里,脱胎换骨,美梦成真。“‘想要显然属于主体内在精神领域目的性的活动,这是一种意象,一种幻想,一种憧憬。这是一股发自有机体心灵深处的内驱力,促使机体从内部发生变化的原动力。”因为“想要”,故而必须想象那想要实现的结果具有无可辩驳的真理性与无以置疑的永恒性,从内部突破的“文明”因此便具有了进取的力量与源源不断的勇气。
“精神”对于“文明”的意义正在于此。
四、结语:文学揭示精神本质问题的思考
精神的精神性存在也是一种“此在”,它在它的存在中与它四周的存在发生交涉,并在存在中对自身的特质与状态进行领会,决定着自己的生存(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精神的精神性存在,无论是其本质的游还是其本源性的凝守,都在世界性地——从“世界”方面来领会自己的存在。故而,时间的变化对精神的精神性影响仅仅在于,它通过不断地向前“投射”而持续自己的本真意义。
精神对“时间”的领悟,与历史无关。相反,随着历史变迁,精神的精神性存在经由实利主义哲学而逾益物质化时,它用精神大逃亡的方式从严防死守的现实社会里找到另一重心理体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彼得堡幻影——诗文集》(Peterburg vision in verse and prose)讲述了对于“另一个世界”的体验:
最后,整个世界以及世上所有人,不论强弱,不论其住所是乞丐的棚子还是金碧辉煌的王宫,在这薄暮时分,都仿佛一个奇异的、施了魔法的幻影,一个梦,马上会像蒸汽一样消失、飘散到深蓝的天空中似的。突然,一个奇怪的想法开始在我心中涌动。我哆嗦了一下,在那一刻,一种我还不曾体会过的强烈感觉涌了上来,突然冲起一股热血,淹没了我的心。在那一刻,我仿佛明白了此前只是在我心中悸动,却没有被完全理解的东西。我仿佛清晰地窥见了一个新的、一个全新的世界,它是我不熟悉的,只通过隐约的传闻、通过某种神秘的符号得知的。我想,在那些珍贵的时刻,我真正的存在开始了。
精神的精神性存在在幻觉、梦、潜意识、疯癫中保留着其完整形态,如果说梦是未达成的愿望的替代性满足,那么,世世代代遗留下来的集体无意识则提出了“精神乌托邦”的问题。正是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已经被这个社会所排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达成了人类在童年期就已经期盼的某种幸福。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另一个世界”的神秘体验,正是出自于精神世界对物质世界的戏仿与挑战。在这个奇异而陌生的世界里,精神脱下伪装,自由地阐述存在者本身所感受的存在,或许,这些没有形象的形象远比现实世界里涅瓦河边正在消失的景物更加真实。它的“真实”不在于它所展露与表述的情境的准确无误,而是说,此时此刻,精神的精神性存在是其所是并如其所是,它揭示自己,并把自己交由我们去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