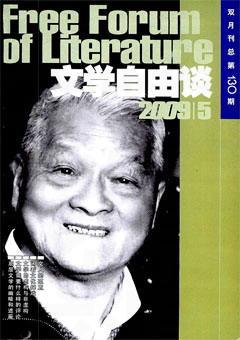“我要和你结婚”
陈歆耕
“我要和你结婚!”
“你说你没想好?我知道你是嫌我长得那个了一些,你看我五官一个也不少,且功能都很正常。哦,个子是矮了一点,但你不了解个子矮的人普遍要比个子高的人聪明吗?鲁迅、拿破仑个子都不高……”
“你居然还是不愿意?唉,真是不可理喻……”
我这里不是在写小说,也不是探讨婚恋问题,而是比喻一种不正常的思维逻辑: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厢情愿”、“强人所难”!如今,一方未得另一方同意而能成婚的可能几乎没有了,婚姻法规定恋爱自由。“捆绑不成夫妻”,大概也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持有“一厢情愿”、“强人所难”思维方式的人,在生活中并不少见。现举近期发生在文坛的一例:
李更先生在刚出版的《文学自由谈》第四期发表了一篇《谢有顺回避哪些问题?》的文章,文章放在“对谈”栏目下,其实只是作者的自说自话。文章的主要内容是说,作者要与评论家谢有顺做一个访谈,或叫对谈。作者设计了一些问题,用电子邮件发给谢有顺。谢有顺在看了他设计的问题后,婉拒了他的访谈要求。作者则三番五次地写信要求谢有顺回答他的问题。在谢有顺婉拒回答他的问题后,作者就在这篇文章中公布了他与谢有顺的往来信件和他设计的采访提纲。看了这篇文章后让我顿生很多感慨,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也借此就教于李更先生——
其一,李更先生想采访谢有顺,无可厚非(且不论在目前体制下,有关部门规定要进行采访须持有新闻出版署颁发的记者证)。但谢有顺先生也同样有权利不接受任何人的采访,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是作者“死打硬缠”式地三番五次说明理由,要对方回答他的提问,这既失自己的尊严,也是对对方的不尊重。其“强人所难”的思维方式,与本文开头的比喻如出一辙。我觉得,谢有顺先生表现得够有风度,够有耐心的了。反复在信件中说明难以回答他问题的理由。其实,他不需要作任何解释,只要说一句“我对你的访谈没有兴趣”即可。
其二,在访谈不成后,作者未经对方同意,擅自在文中公开发表谢有顺给他的信件,这是极不妥当的。不管谢有顺的那些信件是否适合公开发表。同时,公布自己设计的问题提纲,以此告诉公众:谢有顺是一个不敢直面现实问题的批评家。这也有失做人的厚道。其实,看了作者设计的那些问题提纲后,也许读者会得出恰恰相反的印象吧?不是谢有顺不敢直面现实问题,而是那些问题大多都很无聊。
其三,从作者设计的访谈提纲看,问题多多。谢有顺拒绝回答是正常的,如果接受了他的访谈,我觉得谢有顺恐怕就不是现在我们所知的谢有顺了。李更先生提出的很多问题,凡属有正常思维的人,都难以回答。有例为证。且看第一个问题:“……你现在的名气已经远远大过你的老师。有人说,实际上你只是福建长汀一个农民的儿子,没有任何家学,是真正的天才,是吗?”设身处地为谢先生想想,他该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谢有顺在回信中说:“这样的话我听得心惊肉跳,我不知你从何处得出这样的印象,我老师孙绍振的声名之大,非一般人能比的啊。”不管谢有顺和孙绍振比,谁的名气大,但提出这样的问题,一开始就逼着学生“冒犯”自己的老师,是要陷学生于不仁不义的地步,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啊。尊重乃至敬畏自己的老师,大概也算中国人的一个永远不应过时的传统美德。提问者难道连这样的“常识”也没有?另外,我第一次听到中国的文学评论界还有“天才”一说,那怎么还有很多人唉叹中国缺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的批评大家?谢有顺是该顺着对方的提问,承认自己是“天才”,或是谦虚地解释“我不是天才”,呵呵,回答这样的问题实在是风险重重。
再看问题二:“很多人知道你的智商高,其实你的情商更高,在今天的中国文坛,派系林立,不光是同龄人容易有矛盾,不同年龄段的写作者更容易出现所谓代沟,传统上老作家对年轻人的那种传帮带几乎没有了,因为文坛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名利场,相互之间充满敌意,而你独能左右逢源,成为老人和新人之间承上启下的人物,你的秘诀在哪里?”且不谈,李更先生用“充满敌意”,把文坛描绘成闪烁刀光剑影的可怖“战场”,是否有点危言耸听?称一个人“左右逢源”,且要他介绍“秘诀”,这对被访者是一种褒奖,还是侮辱?呵呵,提出此种让你心里感到不快,同时还要你回答问题的人,真是太有才了。
问题四:“作为华语传媒文学大奖的主要推手,你们当初是否有‘另立中央的企图?……”看了这个问题,我也感到“心惊肉跳”。它让我自然联想到了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如此充满“火药味”的问题,简直是把被访者逼到了“刀尖”和墙角。你要不进入访问者的问题圈套,承认自己有此“企图”(谢有顺有此“贼心”和“贼胆”吗?);要不你坚决否认,让人感到你很“虚伪”,说着言不由衷的话。
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举其中还有的一些问题。李更关心的是“文坛八卦”,而不是想与一位评论家探讨文学问题。还有一些他在提纲和信件中所表达的观点,稍有“常识”的人也可分辨出是破绽百出的。如李先生说到因文学杂志编辑水平不高,“几乎所有的纯文学杂志都失去了自己的市场……”只要对文学期刊生存状况稍有了解的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吗?文学期刊衰落的原因,恐怕远远不是如此简单吧?把所有的文学期刊都办成郭敬明的《最小说》那样的东西,大概在中国也行不通的吧?还有,李更在给谢有顺的回信中说到谢有顺老师的名气,甚至连他李更也不如,因为他的一本《李更如是说》发行到7万册,而孙绍振“跟风”出版的《孙绍振如是说》,“发行却遭遇失败”。文学作品或图书与市场的关系,因素非常复杂,至今未有人能说得清楚。按照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观点,在德国普遍认为,一本文学作品发行量高了,肯定是一本低俗读物。当然,他的观点也可商榷。但起码可以说,发行量的大小与一个人的文学成就或名气,并不完全成正比。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是用文言文写成的80万字的巨著,其受众量、发行数或许也不如李更的“如是说”,但两者的学术水准能放到一个天平上去评估吗?李更先生以区区7万册发行量而自炫,不觉得可笑吗?有些80后、90后青春写手写的书,常常发行到几十万、上百万册,如以此论“英雄”,李更先生显然得拜他们为师了。
笔者在文中多次使用了“常识”一词,深感梁文道先生说的这是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确实切中肯綮,指出了一个我们这个时代普遍存在的“病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