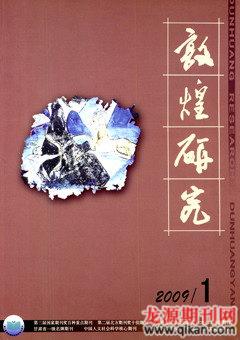《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读后
郝春文
关键词: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出版
中图分类号:G25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09}01-0112-03
由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作为“吐鲁番学研究丛书甲种之二”于2008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学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三个单位的合作成果,三位主编为以上三个单位的代表,参加编纂者也有半数以上出自以上三个单位,另外尚有数位是来自其他单位的相关研究人员。
此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序》、《前言》、《凡例》和《主要参考文献》,第二部分是所收文献的目录和正文,第三部分是索引。《序》由三位主编署名,简要介绍了此书的资料来源、参与整理工作的单位和人员以及成书的过程。《前言》由两篇文章组成,第一篇为《近年吐鲁番的考古新发现》,署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学研究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执笔者是李肖和张永兵。此文分阶段介绍了吐鲁番文献的出土情况,说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出土的吐鲁番文献包括“一九九七年洋海墓地出土文书”、“二○○二年交河故城出土文书”、“二○○四年阿斯塔纳古墓二区出土文书”、“二○○四年巴达木墓区出土文书及墓志”、“二○○四年至二○○五木纳尔墓地出土文书及墓志”、“二○○五年征集台藏塔出土文书”、“二○○四年至二○○五年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出土墓志”、“二○○六年征集吐鲁番出土文书”、“二○○六年阿斯塔纳六○七号墓出土文书”、“二○○六年鄯善洋海一号墓地保管站北区出土文书”。所谓“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指的就是这第三阶段出土的十批三百多件吐鲁番文书、古代典籍和墓志等,这批文献多为汉文世俗文书,其时代始自高昌郡时期,中经阚氏高昌、麴氏高昌,直至唐西州晚期。第二篇是《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概说》,亦由三位主编署名。此文简要介绍了“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的组成和从事文献整理的经过,并对这批文献的重要内容做了概要解说。
第二部分是此书所收文献的目录和正文,正文是此书的主体部分。包括文献图版和文字两个部分。文字部分包括文献标题(名称)、文献说明(解题)和文献释文。文献说明包括文献的来源(出土地点等)、形状、定名定年的依据、被说明的文献与其他文献的关系(可与之缀合者或人名见于其他文献者等)和主要参考论著。为方便读者,此书图版和文字的编排采用图文对照方式,对照的形式以上图下文和图文对开居多,也有一些采用左图右文方式的。
第三部分索引包括《人名索引》(附《神名索引》)、《地名索引》和《文献编号索引》。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所收录的文献具有极为重要的资料价值。就数量而言,《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所收文献要比唐长孺先生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少很多。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是以世俗文书为主,这些世俗文书都是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新资料。其中有很多为以往出土的吐鲁番文献所未见,有的则可以与之互相印证。如洋海墓区一号台地出土的《前秦建元二十年(384)三月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2006TSYIM4:5-1、2006TSYIM4:5-2),是现知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最早的户籍,又如洋海一号墓(97TSYMl)出土的》阚氏高昌永康十二年(477)闰月十四日张祖买奴券》(97TSYMl:5)、《阚氏高昌永康九年、十年(474、475)送使出人、出马条记文书》等一组文书,其内容涉及阚氏高昌时期的奴婢贩运、税役、对外交往及阚氏高昌所属城镇等多方面的情况,为研究阚氏高昌国早期历史提供了多方面的宝贵资料。再如巴达木一一三号墓出土的《唐龙朔二年(622)正月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2004TBMll3:6-1),钤有“高昌县之印”;巴达木二○七出土的《唐调露二年(689)七月东都尚书吏部符为中州县阙员事》(2004TBM207:1-3+2004TBM207:1-7+2004TBM207:1-11g)),钤有“东都尚书吏部之印”;这两件均为此前吐鲁番出土文书所未见。类似例证,不胜枚举。
就资料的出土范围而言,以往出土的吐鲁番文献主要发现于阿斯塔纳和哈拉和卓古墓区,而新获吐鲁番文献除了出自阿斯塔纳墓地的,还有出自高昌城东北巴达木墓地、鄯善县吐峪沟乡洋海墓地、吐鲁番市东郊苏公塔东北两公里处木纳尔墓地和交河故城等处的,显然,不仅出土地点增多了,而且范围也明显扩大了。这些发现于更多地点和更大范围的资料当然比发现于一两个地区的文献具有更高的研究价值。
与此前出版的大型吐鲁番文献图文合集相比,此书无论在印制还是在编纂方面都有很多进步,达到了目前国内外最好水平。
就印制方面而言,此书文献图版均为彩版,特别值得称道,由于吐鲁番文献大多为手写文书,有些墨迹较淡,一些文书还有朱笔标记、朱笔校改或句读,这些信息,黑白图版很难显示。就一般文字而言,彩色图版的显示度也比黑白图版更为清晰,有利于读者正确辨识图版上的文字。但印制彩版,造价高于黑白图版数倍。所以,以往出版的吐鲁番文献和敦煌文献图版,一般都是在卷首选择几幅有代表性的图版制成彩版,主体部分均制成黑白图版。此次《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将全部文献制成彩版,一方面显示了编者和出版者的魄力,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便利。
编纂方面,首先是对被整理主体的命名更为恰当。此前的相关出版物,多将被整理主体称为“文书”,以《吐鲁番出土文书》和《大谷文书集成》为代表,而《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的编者将被整理主体命名为“文献”。王素先生认为书名不称“文书”而称“文献”,当与此“书不仅收入纸质文书,还收入木质、砖质墓表、墓志,以及藏文、婆罗谜文木简”有关。这个推测应该是对的,但我想还应该有其他原因。从《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所收文献的内容来看,虽以世俗文书为多,但也有不少如《急就篇》、《论语》、《孝经义》等古代典籍和《妙法莲华经》等佛教典籍。严格说来,把这些在古代已经成书的典籍称为“文书”是不准确的,但“文献”就可以涵盖世俗文书和典籍等两个部类,当然也可以涵盖王素先生所说的墓志之类。在此前出版的《吐鲁番文书》和《大谷文书集成》,其实也都包含古代典籍和佛教典籍,比较而言,将书名称为“文献”更为恰当。
其次文献的定名恰当、释文准确。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以残片居多,很多文书无头无尾,名称、性质不明,众所周知,对出土手写文书的定名、定性以及文字的释录,是具有很高学术含量的研究工作。通过编纂者的艰苦努力,《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在文献定名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大部分失去原题或没有标题的文书都被拟定了正确的或比较稳妥的名称。文书释文经过
反复核对图版和原件,很多文字经过课题组成员反复讨论才定稿,现在提供给读者的释文是准确、可靠的。
当然,对新出土文献的定名、定性和释文,其准确性只能是相对的。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史来看,一些文书的名称、性质和文字的辨识,要经过长期的研究和反复的探讨才能最终解决。任何个人和课题组都不可能在限定的时间把数百件文献的定名、定性和文字释录工作做到尽善尽美,所以,我们也应该允许《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在文书的定名、定性和文字释录方面存在少量问题,留待将来深入研究,
第三是索引实用。
与此前出版的大型吐鲁番出土文献图文合集相比,《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在索引的编制方面有很大的进步,其中《人名索引》(附《神名索引》)和《地名索引》在同类著作中属于首创。比较而言,编制索引不能算是很难的工作,却可以给读者提供方便,国外同行大多重视在其著作后附有各种索引,所以,《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的做法值得提倡。
第四是整理和出版工作速度相对较快。
新获吐鲁番文献整理小组成立于2005年10月,《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出版是在2008年4月,整个整理和出版的周期是两年零六个月。在此期间,课题组成员坚持每周集体讨论一次,几乎所有假期都是在吐鲁番度过的。应该承认,如果没有全力以赴、争分夺秒的精神,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
对出土文献的整理工作来说,进度太快和太慢都会有问题。进度快了,对保证质量不利;进度慢了,又会影响学术界利用新资料。但快和慢又是相对的。两年多的时间当然不长,十年应该不能算短了吧,但现在确有不少出土资料已经超过十年尚未公布。如果一批重要资料经过多年的整理仍不能公开刊布,为学术界所利用,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出土文献的整理应以尽快公布资料为主要目的,所以应该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快一些。另一方面,如果整理者在整理期间不能做到全力以赴、争分夺秒,或者方法不当,进度慢也不一定能够保证整理工作的质量。
新获吐鲁番文献整理小组所以能以较短的时间高质量地完成整理工作,与整理小组的组成及其采用的整理方式有关,整理小组共有18人,除吐鲁番研究院的张永兵(负责考古发掘和摄影)和汤士华(负责资料工作)外,其他成员大多是荣新江的学生,李肖、朱玉麒、游自勇是荣新江的博士后,姚崇新、余欣、毕波、王媛媛、裴成国、陈昊、文欣则是荣新江指导的已经毕业或在读的博、硕士研究生。孟宪实、史睿、雷闻和张铭心也都长期得到荣新江的指导。所以,荣新江实际是这个课题组的学术带头人和核心。以一个老师为核心组成课题组有两个好处,一是这样的团体效率会比较高。在尊师重道的背景下,以一个老师为首组成课题组,在确定研究计划和方案时会避免很多争吵,在执行计划和方案时也会较少出现推诿的现象,二是这样的课题组同时具有育人的功能。一个课题的完成往往可以带出一支高水平的学术队伍。新获吐鲁番文献整理小组在整理文献过程中所采用的读书班会读方式,其实也是一种教书育人的方法。
当然,组织这样的学术团队从事出土文献整理也有局限,就是不太容易吸收和带头人同辈或比其长一辈的同行学者的智慧和经验,荣新江教授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书稿完成以后,曾邀请课题组以外的相关专家参与讨论和修改书稿,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似乎仍然无法完全避免团队成员结构所造成的缺失。因为出土文献整理已经成为很专门的学术领域,一些靠口耳相传或具体的动手经验很难在短短几天的讨论中倾囊传授。看来,如何使课题组成员进一步优化,还是未来从事出土文献整理应该慎重考虑的问题。
新获吐鲁番文献整理小组还有一个成功的做法值得一提,就是采用了整理与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如上文所述,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包括很多无头无尾的文书,对此类文书的定名、定性乃至文字的准确释读,都有赖于对该文书的深入研究。课题组成员在2005年10月至2008年4月间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有40多篇,这些研究成果为保证《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的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