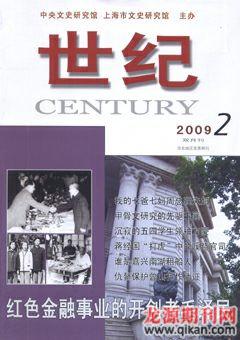我的七爸七妈周总理夫妇
周尔鎏/口述 王 岚/整理

周恩来总理诞辰111周年之际,我在上海拜访了一位和周总理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他就是总理的堂侄,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周恩来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尔鎏。
周教授一生经历丰富。“四清”和“文革”期间,他曾经在纸浆厂、纺织厂、瓷器厂和煤矿跟工人一起劳动过;在河南、山西等地和农民一样干活,有二年时间甚至住在农民存放“寿材”的没有窗户的草屋里;上世纪70年代,在外事口、文化口当过司局长;上世纪80年代组织上安排他到上海,出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或者交通银行行长,进市委委员,他选择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并且已经报到,可是又被组织上调回北京,拟出任对外友协副会长。当时邓颖超是对外友协名誉会长,为避嫌,他应费孝通荐请,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担任“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其间领衔城乡协作发展研究国家重点课题工作,提出“因地制宜,多样模式,随势应变,不失时机”的16字研究方针;曾陪同周恩来总理多次接待外国重要来宾,在工作上和总理有过多年的接触;此外还曾设法促成《邓小平文选》英文版在海外出版;离休后,欧美一些著名大学发来聘书请他去当教授……他总结自己的一生就是:工农商学兵都干过,党政军民学全齐了。周教授还向我表示虽然并无出色的工作成就可言,但始终牢记总理的亲自教诲,尚能一切尽力而为。
周教授是位性情中人,至今走过全国各地以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过世界许多角落。
——整理者题记
总理一辈子叫我的小名爱宝
我是周恩来总理的堂侄。小名爱宝,本是浙江绍兴人,1930年前后生于上海,最初全家住在虹口北四川路(现称四川北路)永安里44号一幢石库门房子里。我的父亲周恩霔是上海法学院早期毕业生,是上海有名的京剧票友,按照总理的指示和安排,长期和梅兰芳保持着密切的个人联系,解放后曾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母亲是大同大学的学生,从保存下来的照片上看,很是温婉贤静,一看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家闺秀。我的父母是自由恋爱,可惜我刚出生母亲就逝世了。所以,我小时候是由祖母养大的,初中以后直至大学毕业就由周总理夫妇直接抚养资助,因为抗战开始后我和父亲即长期分离,甚至我的父亲一度生死不明,与我音信未通。
我们周姓家族在绍兴是个大家族。我的祖父周贻康和周恩来总理的父亲周贻能是嫡堂兄弟,我的祖父在家族里排行第二,周恩来的父亲排行老七,在家族里分别被尊称为“二老爷”、“七老爷”。我童年时,按绍兴老家习惯尊称总理的父亲为“七爷爷”。从我出生到上世纪30年代末,我曾和他在上海、扬州、镇江等地一起生活过。我的祖父因为过继给了大房,所以我也是周家的长房长孙,上溯五代我们的高祖是同一个人——樵水公。我们周家的家风渊源绵延了好几代。我祖父生前曾于清末在各地督抚衙门入幕做师爷,也曾做官系道台衔,民国初年曾担任江苏督军的顾问兼秘书,他的职务似乎相当于现在的省委秘书长,当年随身带了两个最贴近的人,一位是我祖母的亲弟弟程少琴,另一位就是总理的父亲、我的七爷爷。总理在赴日本、英法留学前后,我的祖父恰在在天津、北京、南京等地居住,他都曾到以上各地家中小住并获得我祖父的掩护和大力资助。以后,离开祖国并赴海外留学的的总理经常有信和小礼物寄回来给我的祖父母。我现在还保存着好几件。总理还曾经说过我的祖父是一位忠厚长者并是“学而有成”的长辈。

1927年到1931年期间,总理的父亲、我的七爷爷在我位于虹口四川北路44号的家中住过很长一段时间,为总理夫妇提供掩护和联络。那段时间他为周恩来邓颖超的安全所起的作用,是一般人难以代替的。1931年周恩来邓颖超在上海的时候,因为顾顺章叛变就直接在我四川北路的家中隐蔽居住。就是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总理还让自己的父亲秘密地去和有关同志通风报信,要他们注意安全,相关史料迄今罕有人知,希望不致湮没。那时候中国革命的形势非常危急,周恩来因为工作需要先到了香港,后来转道来到上海。邓颖超1927年在广州的时候,曾经生下过一个男孩,但后来不幸夭折了。她从广州来到上海和周恩来见面汇合,当时他们夫妻怀着深深的丧子之痛,而我当时还是个襁褓中的幼儿,所以他们非常喜欢我,经常抱着我玩。现在我还保存着一张当时勉强坐起爬行维艰的照片。我回忆自那时牙牙学语起长辈们就有意让我叫他们“七爸”、“七妈”了,数十年如一日直至七爸七妈先后不幸辞世未作任何改变。当年七爸七妈赶赴苏区以后,我有时候会从大人那里听到一些他们的消息,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一直到1946年七爸托人终于找到我。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清楚地记得为了躲避白色恐怖,我家仅在上海一地前后搬了不下十处,大多数在法租界。总理生父,也就是我的七爷爷当年听从总理的安排从上海出发奔赴西南大后方和总理汇合前,就住在金神父路(瑞金路)花园坊我的家里。虽然那时我还小,但我记得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七爷爷经常带着我外出散发抗日传单,每逢饥肠辘辘时两人分享一个高庄馒头。
七爸托人找到我,曾想让我去延安
1946年,七爸通过《文汇报》党外人士张振邦经理转送亲笔信给我,叫我去思南路周将军公馆找中共发言人陈家康,并告诉我陈家康知道他什么时候从南京到上海来,要我随时和他保持联系。张经理还给我看了七爸给我的信,信的开头就是“亲爱的爱宝”,落款则是“七爸、七妈”。张经理是我同学贾大勤的舅舅,我从苏北到上海后曾经住在另外一位同学王定武家里,我们三个人曾是很要好的同学。张经理给我看的总理来信,贾大勤(解放后曾经担任农业部办公厅主任)和王定武(解放后曾经担任黑色冶金设计院院长)都看过,他们现在都是有五十年以上党龄的共产党员。
不久,我接到通知,说七爸到上海了,想见我。我很紧张,也有点兴奋,在约定的一天,我感到机会难得就带着弟弟周尔均去了思南路上的周将军公馆。那是一幢树影掩映中的西班牙风格的小楼,看上去很气派。我是第一次去那里,很忐忑,但对那里的街道我也不陌生。因为梅兰芳的家是周将军公馆的近邻,而我小时候经常跟着父亲去梅家。那时家里也很穷,但每次去梅家,大人总给我穿好西装,打扮得像位“小公子”。梅兰芳一直把我父亲看成是他和总理的联系人,对我父亲非常信任。1973年我父亲去北京梅家看望梅夫人,当时梅兰芳已经去世,梅夫人见到我父亲扑地痛哭,她就觉得我父亲是代表总理和我们家人去看望慰问他们一家的。

再说初见七爸时我也有点拘束。七爸很是亲切地招呼着,让我在兵荒马乱、居无定所的时候感觉到亲人的温情。见我带了弟弟去,七爸好像也有点意外,那次没有多谈什么,由七妈邓颖超给了我们一点药。我记得给我的是眼药水,因为尔均头顶长了疮,所以给他的是治疗皮肤的药膏。没有多久我们俩就告辞出来了。后来过了不久,大概一个月左右,七爸又让陈家康通知我,说要单独约见了我。那次是我一个人去的,谈了一上午。七爸详细询问了我的家庭和苏北解放区情况,当问到我继母的情况时,我如实相告,说:“她和我爸爸闹纠纷我并不知道,她把我赶出家门后,祖母让我到上海来找您,但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您,幸亏同学王定武让我住在他家,不然我就流落街头了。”其实,尽管七爸工作很忙,许多国家大事等着他处理,但我们家里发生的事他都知道,所以七爸听我这样讲后就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还当场说我“你真是个老实人”。
那次,七爸指着墙上的解放区地图对我说:“你的父亲就在淮阴、盐城那一带,但具体在哪里我也不太清楚,而且很有可能已经牺牲了。”那天,七爸告诉我将把我带到延安去,在他的卧室,他指着床上的两条被子说送给我,同时他还告我国共谈判有可能破裂,全面内战也可能近期内爆发。我看见床上两条旧的粗花布的被子,一条红,一条绿,里子都是白的,这表明他们的日常生活是非常简单朴素的。这时候七妈邓颖超进来了,她刚巧听见了七爸说的话,当时15岁的我看到她拉拉七爸的衣袖,两人走到外间,把我一个人留在卧室里。隔着一条布帘子,我能听见他们的说话。他们商量了一阵后又回到卧室,七妈建议我留在上海继续读完高中,从此由他们出资抚养我。为此事,七妈邓颖超解放后还对我表示了歉意,尤其强调的是我那时刚考取高中,除希望年幼的我继续留在上海完成学业外,还有就是总理工作很忙,当年她自己身体也不好怕不能更好地照顾我。另外,还有许多烈士子女留在白区必须另作妥当安排,她怕总理和她很难一一兼顾。所以,解放后邓颖超几次对我说过:你做我们的侄儿倒霉了,未受其利,反受其害!

那天在周公馆,七爸兴致很高,到了午饭时分,还带我和一位美国军官共进午餐。因为要见外国客人,七爸西装毕挺,头发一丝不乱。我穿着破旧的对襟衣服,那双破鞋连脚趾都露出来了。七爸并不因此感到为难,面对那位美国军官时他坦然介绍说:“这是我的侄儿,从解放区来的。”那位军官觉得非常奇怪,他大概想象不到共产党高级干部还有这样的穷亲戚,他仔细地打量了我一下,但出于礼貌他什么都没问,只是朝我笑着点点头。我想七爸当时不让我避开或换衣服,主要原因也就是要让外界包括国际人士了解真实的中国共产党,了解真实的中国革命。
和七爸七妈告别前,他们给了我一笔钱,说够我三年的读书生活费用了,看我把钱藏在贴身的衣袋里,他们才放心。七爸并对我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很穷的,是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我身着西装脚蹬皮鞋也是只是为了目前的工作。他还问我看过马列的书没有?我说只看过《大众哲学》。他又问我读过周敦颐的《爱莲说》吗?我回答说小学时读过,他表示满意并说周敦颐是我家的始祖,我们后人都应该以他为榜样。随后还和我讲了“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道理,事后我发现孟子的原话已被七爸有意作了调整,他把“贫贱不能移”放在首句是有意识地针对我当时的贫困处境,他的教导成为了我毕生信奉和遵循的生活准则。出门后,警卫夹着两条被子带着我绕来绕去一直把我送到黄浦江边,说特务被甩掉了,这才把被子交给我,我一个人回到同学王定武家。这两条被子我一直用到上海高桥临解放前夕被一场战火烧掉。
那以后,七爸七妈就不时给我钱把我扶养了起来。解放初有个政策,就是解放前三年由谁出钱抚养,就算谁的子女。所以,应该说我是真正由总理夫妇抚养长大的。但是,我没有暴露亲属身份也没有辜负总理对我的期望,考上南开大学后,我是半工半读,曾担任学生会主席,读了两个专业,一个是外国文学,一个是经济专业,尽管社会活动很多,但我门门功课都是满分5分,可以说勉为其难地保持了这一来之不易的记录。当两位老人家得知我被评为天津市“三好学生”后,曾为此感到很开心。
七爸对我说:美好的金子迟早会发光
我为人向来低调,不愿意张扬,很长时间里从来都不说自己和总理的关系,甚至在档案里也不填,家庭社会关系栏填“父母双亡”,家庭出身填的是“城市贫民”。早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我就因此被称为“傻瓜中的特大傻瓜”。后来,我拟出任上海市社科院院长时,当时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曾对我说过:“老周,你这个人真是不错,档案里看不出一点你和总理的关系。”有一次总理还当着我的面对陈老总说:“他有一颗赤子之心。”我的理解就是夸我心地单纯、善良,没有私心杂念。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沾总理的光,更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给总理带来任何不必要的麻烦。也许正是因为我从不炫耀招摇,难免有人会对我的身份持怀疑的态度,包括我的一些外地的亲戚。他们奇怪,我为什么叫总理夫妇七爸七妈?他们不知道,我从小就是这么叫的。
解放后七妈邓颖超笑着告诉我,我和总理都是AB血型,可谓是不约而同。我想,这大概就是家族血缘遗传的关系吧。我从小遵照长辈吩咐叫总理七爸,叫邓颖超七妈,而我的弟弟妹妹则分别叫他们为七伯伯、七妈或七叔叔、七妈,而总理一辈子叫我的小名爱宝。七妈邓颖超在我小时候也叫我爱宝,到我长大后就比较正式地叫我尔鎏了。
我的名字到底是谁起的现在仍不清楚,我从来没有改过名。有一次邓颖超知道我档案里填“城市贫民”后曾不经意地开玩笑,她说:“城市贫民是没有固定收入的人,尔鎏尔鎏,听上去就像北方人叫的二流子。”七爸在旁听见了,严肃地说:“你怎么能这样和孩子说话呢?孩子有很强的自尊心,他不愿沾我们的光,也不愿影响我们,这是很好的事。”总理还问:“你知道鎏是什么意思吗?”见邓颖超在思考没有马上回答,又接着说:“查查字典就可以知道,是美好的金子的意思。”邓颖超一听马上说:“尔鎏啊,以后不管碰到什么挫折,你都要记住自己的名字。” 我非常清楚的记得总理当即说:“爱宝啊,不管碰到什么困难和委屈,你一辈子要坚持自己的名字,照顾大局行事,我相信美好的金子终究会发光的。”
我一直记着七爸的这句话,无论这一生中遭遇到怎样的艰难挫折,我都会想起这句话,这句话给了我毕生无穷尽的力量和智慧。
我的父辈是“恩”字辈,我这一辈是“尔”字辈。但我这一辈中,坚持用“尔”字的已经很少,其他大多在解放前,由于政治社会的原因,他们的父母选择给子女改了名字。
细微处感受七爸七妈对我的期望和关爱

七爸七妈虽无亲生子女,却有许多亲戚晚辈,他们也都得到过总理的关心,但只有我在解放前就和总理有接触联系,是由总理真正抚养长大的。
我在南开大学读书时属于调干生,只有少量津贴,只是自己一个人用还可以应付过去。但是,总理要求我经常回上海去看望祖母,也就是总理的二婶,这样一来,我的那点钱就显得捉襟见肘了。作为国家领导人,当时总理自己工资才400多元,但平时见面,总会给我20元不等。1963、1964年国家经济非常困难,七爸拿出自己的工资,每月给我大女儿30元,由对外文委保卫部门的同志转交或者就直接给我。
有时候七爸想见我了,会主动叫我去。谈话后见七爸高兴,七妈邓颖超也高兴,就会破例多给我点钱,理由是给我配眼镜。我有时想想好笑,哪会经常配眼镜啊。其实,这是总理夫妇对我的一种无言的特殊照顾,从中我也体会到总理七爸对我的殷切期望和一份浓浓的别样的关爱。在这一点上,连总理的司机都说:“对你真是例外。”
1960年,正是国家处于流年不利之际,自然灾害和工作失误使得全国人民都勒紧了裤腰带。这一年,我和王章丽女士在北京结为秦晋之好。在我们订婚的时候,七爸说:“你们结婚,正值国家困难时期,我不赞成举行结婚仪式,也不适合用糖招待客人,只许吃点花生米。我就送一罐花生米作为结婚礼物吧。”大家都以为总理在开玩笑,再艰苦,结婚喜糖总要有的啊。没想到,当我们大喜的时候,总理真的送了一罐上海产的“梅林牌”花生米给我们作为新婚礼物,而且还要求我们吃完后把空罐头卖给废品公司。我明白七爸的意思是要我们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要与人民同甘苦。
七爸曾经送给我一件他在开国大典时穿的黄里透红的衣服,虽然是布的,但颜色比较亮,尤其在那年代一片灰黑之中显得格外醒目。我因为当过兵,习惯了穿素色衣服,不好意思穿这么亮色的衣服出去,于是没有多想就把衣服染成蓝色,又穿了好多年,看看实在不能再穿就丢弃了。总理去世后,中央警卫团的警卫问起我那件旧衣服在哪里时,我才知道那是件珍贵的文物,可是却被我不知不觉中丢弃了,觉得万分可惜。有了那样的教训,所以我就把那罐头保存了下来,以后无论家搬到那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我总细心地保管好。总理110周年诞辰时,我受邀在大学里向学生们讲述伟人的丰功伟绩,当时大屏幕上展出了那个花生米的罐头,引起了师生极大的好奇,从而对一生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的总理与愈加敬佩。
其实,七爸送我的礼物还真不少,虽然有的并不值钱。我夫人怀孕后,有一次我去西花厅七爸七妈家汇报工作,七妈邓颖超知道我夫人要生小孩了,就把总理的一套洗得干干净净的旧内衣裤交给我,说“生孩子时可以穿”。所以,我夫人在生大女儿时就是穿着总理七爸的这件旧内衣,但感觉却是非常温暖。
总理七爸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但每每想起他对我的关爱,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时移情坚,讲述这些事、这些话,就是为了记住已逝岁月中的点滴历史,为了表示对总理七爸的怀念和感恩之情。
(整理者王岚单位为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
责任编辑 沈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