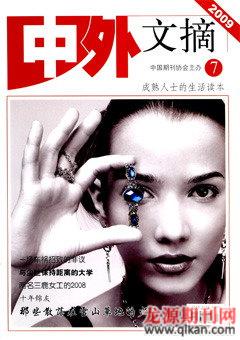布达拉宫里的爱情绝唱
丁立梅
仓央嘉措的情歌,适合在微凉的黄昏听。这个时候,白天的喧闹,一一收敛。一些坚硬,开始变得柔软——太阳不那么烈了,人的脾气不那么大了。暮色温柔得不能再温柔地落下来,爱情终于有了盼头——且等那月下佳人来。今生来世,我要等的,都是你。
“那一天,闭目在经殿香雾中/蓦然听见/你颂经的真言//那一月,我拨动所有的转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那一年,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啊/不为修来生/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这是仓央嘉措的爱情。每天,当夜幕开始笼罩着神秘的布达拉宫,当庄严的暮钟,在晚风中敲响,他欢喜的心,像只仙鹤似的,开始翩翩起舞,他就要见到他的情人仁增旺姆了!他从巨大的无畏狮子大法宝座上走下来,从金碧辉煌里,一步一步,走向俗世凡尘。爱人啊,你才是我心中至高无上的佛祖啊。他脱去僧袍,换上俗衣,戴上假发,从布达拉宫的暗门,悄悄走出,走进民间。那里,玛吉阿米酒店里,住着他的仁增旺姆。她像任何一个盼情郎的女子一样,正倚着门儿,焦急地等着心上人的到来。
夜,天堂一样的夜,充满馨香。花开。虫叫。星星在窗外的天空中,‘眨着眼。多么静谧、安宁!他的手,缠绕着她的臂。她的呢喃,充满了青草的芬芳,呼吸一般的,萦在他的耳际。上天啊,请让这一刻永恒吧!他们仿佛置身在故乡,那个叫门隅的美丽的地方。四季的花,在原野上不息地开着,五彩斑斓。草原上奔跑着牛羊,和欢快的孩子。蓝天碧空下,雄鹰在飞翔。最令他们迷醉的是,身着氆氇服饰的家乡男女,唱着婉转的加鲁情歌。那些情歌,在他们幼小的心里埋下了热爱的种子。自由地相爱,才是人世间最值得追求的事。
他们一起长大,她是他的青梅,他是她的竹马。他骑在马背上,她坐在花丛中。柳树林里,他们一起畅想将来。将来,他是夫,她是妻,他们将在美丽的门隅平原上,生儿育女,相伴终老。
何曾想过别离?他们以为,门隅的山,永远在的。门隅的水,永远在的。门隅的人,永远在的。
1697年的秋天,对于14岁的门巴族少年仓央嘉措来说,真是一个萧杀的秋天。这个秋天,他将远离他的门隅,远离他的仁增旺姆,到千山万水外的布达拉宫去。自从3岁被定为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冥冥中,他的命运,已不掌控在他的手里了。他要去走佛的路,成为西藏最高精神领袖六世达赖喇嘛。
那是怎样的一场告别啊。他为她,在树梢上挂上祈求平安与福祉的经幡,他把他的魂,系在上面了。一步一回头啊,别了,我亲爱的山;别了,我亲爱的水;别了,我亲爱的人。美丽的姑娘仁增旺姆,眼睁睁看着她的少年一步一步走远,她多想拽着他不放手,今生也不放手。她不要他变成佛,她不要,她要他的仓央嘉措!泪水长流中,她铭记了他临行前的一句承诺:我们会相见的。
一年,又一年。布达拉宫红宫的屋顶平台上,已是普惠罗桑仁钦的仓央嘉措,眼光越过一座座灵塔金顶,眺望着他遥远的门隅,心中千呼万唤的,是他心爱的姑娘:“山上的草坝黄了,山下的树叶落了。杜鹃若是燕子,能飞向门隅多好!”他望瘦了风,望瘦了月,望瘦了人。而隔着千重山万条水的门隅,仁增旺姆站在他挂的经幡下,把从未谋面过的布达拉宫,在心里默诵了一遍又一遍。他走后的日子,求婚者接踵而至,父母威逼,舆论谴责,她统统不顾,她要等着她的仓央嘉措,他们一定会相见。
终于等来了仓央嘉措召唤她的消息:“翠绿的布谷鸟儿,何时要去门隅?我要给美丽的姑娘,寄去三次信息。”她一刻也不曾停留,行囊未来得及收拾就上路了。她要飞越高山险阻,飞到她的爱人身边。
他们在布达拉宫重逢了!他是高高在上的活佛,她是万千膜拜信徒中的一个。穿过那些膜拜的头顶,他们纠缠的眼神,早已下过一场甜蜜的雨了,他们在雨中醉了。
她在布达拉宫旁边的玛吉阿米酒店住下来。他们不敢索要未来,只把现在的一分一秒,都紧紧抓在手心里,不肯放过。他把他的日子,分成白天和夜晚。白天,他是住在布达拉宫里的活佛六世达赖喇嘛。夜晚,他是人,是一个被爱情灌醉的凡俗的人。夜真是短暂啊,相聚的温度,还没来得及焐暖心,又要别了。仓央嘉措忍不住对早啼的雄鸡发出恳求:“白色的桑耶雄鸡,请不要过早啼叫!我和年幼相好的情人,心里话还没有谈呢。”
这样的爱,却注定没有指望。其实,自从3岁那年,他被确定为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后,他就失去了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权利——追求自由和爱情。他们的相爱,无异于赤裸着双脚,在荆棘上跳舞。
且看当时西藏的形势:宗教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各方面权力纷争,都虎视眈眈盯着他身下的无畏狮子大法宝座。掌控了他,就等于掌控了整个西藏,权力、土地和财富,就会滚滚而来。在这等恶劣的环境中,仓央嘉措过度的“放浪形骸”,根本就是授人以柄。
风雨欲来。这对苦命的恋人,已经感到乌云压顶的沉重,已经嗅到不远处的血腥味。她躺在他的怀里,他搂紧她的人,不知什么时候一松手,就再见不着了。黄金般的分分秒秒啊。他问他的仁增旺姆,愿否永做伴侣?她毫不犹豫地答,除非死别,决不生离!
好了,还有什么比恋人的这句承诺,更能穿心入肺的呢?佛亦不能够。他脱下身上的僧衣,扔到辅他走上佛路的第巴桑结嘉措的脚下。他决心放弃他的达赖喇嘛的权位,放弃布达拉宫的辉煌,他不要做佛,他要做人,他要和他的仁增旺姆,一起回他们的门隅。
他天真了!现实哪里由得了他?他们先对他的仁增旺姆下手了,他们哪里容得下这个女子,来抢夺他们的权力。某一天,他再去约会,玛吉阿米酒店里,却再看不见她可爱的身影了。仓央嘉措陡地被抽空了心,他豆花似的爱人,永远消失在他的眼眸底。他再无所求,真的四大皆空了。
他平静了。他身边的权力之争,却愈演愈烈。反对派一直拿他的“放浪形骸”做文章。1706年,在权力之争中获胜的拉藏汗,把他从无畏狮子大法宝座上拉下来。康熙帝一纸诏书:执献京师。他踏上了被押解去北京的路。
1707年冬,仓央嘉措在青海湖畔神秘失踪。一说是被杀;一说是病死。这一年,他25岁。
几十年后,有个从门隅来的老妇人,来到布达拉宫,向人打听,去青海湖的路。她衣衫褴褛,白发乱草似的,蓬松在头上。岁月的沧桑,深深印在她的脸上,刀削斧刻般的。有人给她指路,她低声道谢。转身,一个人,朝着落日,踽踽地走远了。
300多年过去了,布达拉宫门前的转经筒,转过一世再一世。多少人事,都被历史的风尘,淹没得严严实实,再无痕迹可寻。然而,仓央嘉措和他的爱情,却如漫山遍野的格桑花,世世代代,盛开在青藏高原上,盛开在人们的心里。
(摘自《文苑》2009年第3A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