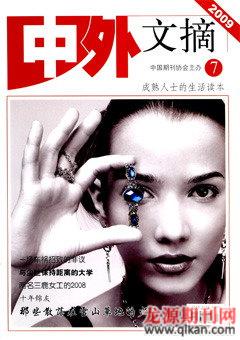打工时代的婚礼
江 子
在深圳某中日合资公司的女工宿舍,我的堂妹默默打理着自己的行装。她的旁边,是她只认识了一个月的四川男友。
在她面前扒开的行李箱里,依次整齐摆放着她的一些衣物,还有证件、一面小圆镜、化妆品、几本简易相册。衣物依然可穿,身份证当然还有用处,但那些诸如暂住证、员工证、剩下的饭菜票肯定已成无用之物,堂妹依然带着它们,不过是为自己的青春岁月留下些许证据而已。映照在那面普通的有些斑驳的小圆镜里的,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青葱、羞涩、双目清澈的小女孩了,她化了淡妆的脸已有了些许细密的不易察觉的皱纹。那几本简易相册里,更是清晰地记录下她漂泊不定的往昔。其中有在深圳的世界之窗、她过去向人介绍称之为“我们厂”的那家中日合资公司的大门前的留影,还有她被公司派到日本工作一年的工作、生活照。那是她最珍贵的记忆,已经成为她生命的奇迹,够得上她一辈子珍藏。在那里,她说着一口因为得益于公司良好的语言环境学来的流利的日语,与来自日本的同事亲密无间,没有人知道她是一个初中才毕业的中国乡村女孩。
她提起行装,在四川男友的陪伴下,向火车站走去——她携带着她的复杂难言的过去,要走向新的、不被她把握的、多少让她忧心忡忡的未来。深圳,即将成为她模糊的远景,恍惚的梦境。几天前,她已向公司辞职,决定把自己嫁给身边的四川小伙。而事实上,她对身边这个一个多月前经别人介绍的、身材瘦高的四川男人所知不多,据他说他高中文化,家乡在离重庆大概四百里的一个小镇,家境称得上还不错……就像她虽然在深圳呆上了十多年,可她对它依然陌生那样。虽然他离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形象相差甚远,可她已经年近三十,深圳这座花团锦簇的城市,已经耗尽了她最好的青春年华,粉碎了她全部的梦想。她没有像许多励志电视剧演绎的那样,得遇贵人相助,成为深圳或其他城市街头闹市的某家美容院、花店、服装店或者其他什么公司的女老板,或者早早遇上如意郎君,一起白手起家,最终过上富足美好的生活。她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妹,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打工妹中的一个。她要过上正常的生活,就必须结婚,生子,成为别人的妻子和母亲。当有一天有人把现在的男友介绍给她,她还是被四川这个词吓了一跳,对她来说,那是一个多么遥远、几乎难以企及的地方。可是她的年龄已经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了,何况,那个瘦高的男孩子看起来还文质彬彬,脾气不错,是一个可以托付的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定下了关系,决定离开深圳这座本不属于他们的城市,回到那个她根本没有到过的四川小镇结婚,生活。
——经过十多年的打工生活后,那个坐在从深圳开往四川的某列火车靠窗玻璃的位置上的年轻女子,她的内心不乏少女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可同时亦怀着孀妇的凛然和老妇的苍凉。
我的农民堂叔有一天梦见一个黑色的燕子突然变得硕大无朋,对他再三眷顾,然后飞起不见。当他回首,屋檐下已是燕去巢空。他醒来觉得纳闷,随口向堂婶说起,不料堂婶竟和他做了一个一样的梦。而当日他门前的大树上,一只乌鸦叫了三声,一只喜鹊也叫了三声。他们不知是吉是凶。接着他们接到了堂妹从四川打来的电话。堂妹说起在四川的种种细节,那里的风俗如何如何,气候如何如何,饮食习惯如何如何,未婚夫家的状况如何如何……她的感觉还不算糟糕,当然许多方面还有待适应,但请父母勿以为念。堂妹在电话里宣布了她的一个重大决定:他们已定于一个星期后举办婚礼,请父母一定亲临参加,由于路途遥远,婚期迫近,不能回来亲自接父母前往,请父母多担待。在电话里,堂妹不免哭了几声。电话毕。
堂叔堂婶开始筹划着去四川。他们先买了带给堂妹的东西,那是一种叫南酸枣糕的家乡特产,是堂妹的最爱,堂妹每年春节回家后返回深圳,都要带上一两袋,但此次,他们一次买了十袋,堂妹此去,不知何时可以回乡,总得多备些才好。他们还给自己各买了一件羽绒服,以免面见亲家自己太寒酸丢了女儿脸面,也为漫长的、冷暖难料的旅途保暖之用。堂叔买的是外套,花去一百,堂婶买的是夹衫,花了五十。他们要在省城工作的堂侄(也就是我)给他们买两张机票,原因是他们平常的生活半径最多不超过百里,而此次路途遥遥,堂婶晕车厉害,恐难以坚持,乘机往返,是唯一的选择,即使花费巨大,但为参加女儿的婚礼,也只好在所不惜。
他们不日来到了省城。从火车站到我的住处正常情况下只要半小时,他们足足走了一个半钟头。我的住址,堂叔知道,几个月前他还来过一次,但这次他还是走错了,其间转了好几趟车,对他们来说,城市就像一座迷宫,对其中方向,他们难以辨别。当我见到他们,他们虽然显得十分欣喜,但脸上的慌乱还没来得及退去。当他们在我家坐定,他们顿时变得伤感。堂叔不善言谈,而堂婶原本是个快言快语之人,这时也多少有些闪烁其词。他们说起对此次旅途的担心:飞机将在今晚凌晨降落在重庆,而堂妹所在的四川小镇,离重庆还有五百里。这对很少出远门的他们来说,要顺利到达终点,无疑是一场十分严峻的考验。他们说起过去自己对堂妹婚事的预想: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只要离家不是太远,行车方便,就可以经常走动,互相照应,他们可以含饴弄孙,一家老小其乐融融。早年堂妹与日本小伙子恋爱,他们极力反对,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而现在堂妹还是远嫁他乡,远超出他们的预想。堂妹已是大龄,还能有什么回旋的余地?这是堂妹的命,没法子的事情。然后他们开始担心堂妹。堂妹孤身一人在异乡,无亲无朋,一旦有啥不周全的地方,做父母的不在身边,如何是好?吉凶好歹,风霜雪雨,只能是她一个人抵挡了!……说到后来,他们不禁嘘唏叹息。开始我在旁边劝说,最后也和他们一起保持沉默,气氛未免有些沉闷。
晚饭后,为防他们不擅办理登机手续,我送堂叔堂婶到了机场。我领着他们在候机大厅坐定,并帮他们换回了登机牌。当我返回,我看到他们坐在一群由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一身时尚打扮的城里人构成的旅客中间,脸上的孤寂和忧心忡忡异常分明,手中紧紧攥着的几个塑料袋显得无比悲怆。那个装了酸枣糕的袋子由于过于沉重提手不堪重负已经脱落。堂婶不得不把它紧紧抱在胸前。仿佛她抱着的是一个襁褓,襁褓里的孩子正在沉睡,对这个让堂叔堂婶惊慌失措的世界,丝毫不知。
……然后是堂叔堂婶通过安检。我看见他们在举着测探器的严肃的安检人员面前,慌乱地把身上的东西悉数掏出:临时借来的手机、钥匙扣、打火机、香烟、用橡皮圈细细捆绑了的一小卷钞票,甚至写着他们将抵达的小镇的地址和电话的纸条等等。他们把双手高高举起,由于毫无经验,其样子显得十分无助,仿佛是缴了械的俘虏。
而在几千里之外的四川省某个小镇,一场婚礼即将隆重举行。在那里,他们理所当然地将获得极高的礼遇。
(摘自《小品文选刊》200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