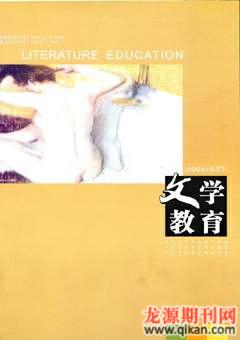巴楚文化与三峡歌舞
汪 青
三峡地区是巴文化、楚文化交汇之地,歌舞兴盛。巴楚文化与三峡歌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巴楚文化的形成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巴楚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由巴楚文化逐渐交流、融合形成的,巴楚文化形成的客观条件是巴、楚之间长期以来的人群往来和族群迁徙。
经专家多方考证,证实:殷周之际,巴人活动中心在江汉之间,与楚(今河南淅川县)、邓(今河南邓县)接壤。巴、楚在西周一代均为周之南国,《左传·昭公九年》载:“自武王克商以来,巴、濮、楚、邓、吾南土也。”但两国间分布有大批百濮群落。到两周之际, 随着濮的衰落和大批远徙,楚人又取得濮地而与巴地毗连,《史记·楚世家》载:“楚武王(公元前8世纪)始开濮地而有之。”巴、楚关系于是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巴、楚关系,有战有和,但多为和睦相处,少有战争冲突。巴、楚关系亲密,不仅结成军事同盟,《楚国编年资料》载:“公元前703年,武王38年,巴楚和好,斗廉败邓、鄾”,而且巴、楚两族还世代通婚。据文献记载,巴、楚公室联姻始于公元前607年,即巴人从楚灭庸之后。《左传·宣公四年》载:“初,若敖娶于郧,生斗伯比。若敖率,从其母畜于郧,淫于郧子之女,生子文焉。郧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之,郧子母,见之,惧而归,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故命之曰‘斗谷於菟。”学者们认为巴人崇虎,呼虎为‘於菟,“若敖(楚王)娶于郧”即是巴、楚两族通婚。《华阳国志·巴志》载:“楚共王立,纳巴姬,巴亦称王。”楚共王娶巴姬之事,亦见于《左传·昭公十三年》:“共王无冢嫡(无嫡生长子)。有宠子五人,无适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神:‘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壁见于群望曰:‘当壁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既乃与巴姬密埋壁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齐,而长入拜。”
巴、楚关系如此亲密,必然互有移民,即使巴、楚交恶,彼此征战,也会促使两地较大规模的人群迁移,杂居。刘向《新序》中《宋玉对楚王》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楚郢都流行有《下里巴人》等通俗易懂的歌曲,这不仅说明巴乐的流行,还说明楚国境内生活着会唱巴歌的巴人。《华阳国志·巴志》载:“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意指峡江以上部分巴地范围内杂居的人群中,约有一半是外来的楚人,说明巴地同样生活着更多的楚人。
巴、楚人群的迁徙、杂居,使两种文化的相互交流有了可能,为巴楚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如果说,巴、楚两国并立之时,文化交流上还会存有巴、楚之别,那么在楚灭巴国占领巴国故地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巴人、楚人关于自身身份认同的逐渐弱化,会使得巴楚文化的互融更加容易,顺畅,从表层的互容,到较深层次的互融。
考古学家在川东鄂西长江沿岸巴国故地所发掘清理出了大批战国墓葬, 不论是巴的墓葬形制还是楚的墓葬形制, 当中大多可以发现有大量成组、群的巴文化因素和大量成组、群的楚文化因素相互结合的共生现象,这是典型的半巴半楚,亦巴亦楚的文化互容景观。
再如,巴地山高坡陡,潮湿多雨,亦多虫蛇,故巴人以干栏为居室。(“干栏”即今所称“吊脚楼”)楚人来自中原,本与干栏无缘,后来则有了“层台累榭”,想必是仿照干栏而造。巴人遗裔——土家族的“吊脚楼”,在鄂西南、湘西北、川东南、黔东北都有,而以鄂西南土家吊脚楼最为出众,缘由应是其地离故楚郢都最近,或多或少都带有层台累榭的遗风。吊脚楼的出现,得益于巴文化与楚文化的双向影响。
“这种物质文化丛的互容, 深刻地表现了巴、楚之间相互的文化认同和文化互融。”[1]
物质文化上的互融,其实在更深的层次上,反映出巴、楚文化在精神文化上的互融。精神文化上的互融,正是巴楚文化得以形成的最深刻也是最深层的原因。
巴、楚文化在长期的相互渗透、吸收与混融,形成了自身的基本特征。段渝在《先秦巴文化与巴楚文化的形成》一文中,将巴楚文化的基本特征归纳为:“第一, 巫鬼崇拜; 第二, 干栏式建筑, 即吊脚楼; 第三, 道家哲学思想; 第四, 性格敦厚, 天性劲勇;第五, 踏歌、跳丧以及其他许多民俗文化因素,多渊源于古老的巴地各族, 秦汉以后又成为巴楚文化区各族共同的民俗; 第六, 神女传说, 是巴楚文化中最富浪漫色彩的精神文化内核。”(部分学者认为称“巴楚文化”,是“把未具共同特点的两种文化硬性的捏在一块去含糊其辞地命名一个“巴楚文化”的新名词”,不宜再使用“巴楚文化”。[2]这一论断,还值得商榷。)
笔者认为,在上述特征之中,崇拜巫鬼的巫文化是巴楚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得以留存的、最明显、最核心的特征。不论是“踏歌、跳丧以及其他许多民俗”,还是“神女传说”,都植根于蕴含宗教信仰的巫文化。
峡江地域是巴文化的起源地[3]。奔腾的长江,险峻的三峡,神秘的溶洞以及虎啸猿啼,这些大自然的现象,对原始巴人来说,奇异莫测。故巴人也像其他初民一样,以浪漫情怀由自然现象幻想出鬼神,多为祭鬼祀神之事,连选定首领这样的大事都要看神灵旨意。《后汉书·南蛮传》记载:“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足见巫风之盛,而且掷剑独中,土船浮水,也带有明显的巫术色彩。
早期,楚人自中原南迁而来,古老的巴文化对新兴的楚文化影响甚大。后来,随着巴土大部分纳入楚国版图和巴人大部分成为楚国国民,巴文化与楚文化共生,互融。其中,巴人与楚人为满足共同的崇巫心理,巴人的巫风巫习与楚人的巫风巫习会容易地合流会融为一体,成为同一文化类型。如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4]。民间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江汉信巫鬼,重淫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楚人以歌舞祭祀的方式与巴人如出一辙。
人类早期歌舞与宗教巫术之间总是有着天然的亲密性。“歌曲是人类表达感情的一种形式。它是多方面的,渗透了一切的形式,……也许歌曲的产生,由于早期的人类察觉到人的呼喊声具有控制动物的力量,以后又发展到认为人的呼声对其他生物和自然界现象有控制力量。……民俗学者关心的是确定歌曲在人的生活中的地位,注意它进入的哪些生活领域,它采用了哪些不同的形式。我们把歌曲和曲调结合起来研究,因为对于文化低的人来说,这两者是不可分的;鉴于自然的音乐和其他模拟的声音与巫术、宗教仪式有密切的联系,对音乐应给予更多的重视。无论是什么肤色的巫师,他的咒语总是韵文。战歌、情歌、摇篮曲、哀歌以及婚礼颂歌,无疑在最初都具有巫术、宗教的意义,带有咒文的性质。”[5]三峡地区巫风炽烈,造成了三峡歌舞的高度发达,巴人乐舞在武王伐纣之时已负盛名,“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并且后世流传甚广,刘向《新序》中《宋玉对楚王》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浓郁的巫风色彩,又会投射到歌舞之中,使得三峡祭祀巫舞昌盛。东汉王逸《楚辞章句》载:“昔楚国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唐樊绰在《蛮书》中谈及巴人葬仪时道:“初丧,鼙鼓以道哀,其歌必号,其众必跳,此乃盘孤白虎之勇也”,“父母死,击鼓踏歌,亲属饮宴舞戏……”唐代刘禹锡被贬郎州,感受更深:“蛮俗好巫,每淫祀鼓舞,必歌俚辞。”三峡巴楚之地的歌舞多带有娱神的巫典性质。
三峡歌舞的这种巫文化特质,从今遗存于三峡土家族地区的跳丧舞中仍可见其“余音”。清《长乐县志》(今五峰县)载:“家有亲丧,乡邻吊,至夜不去,曰‘伴亡;于柩旁击鼓,曰‘丧鼓;互唱俚曲哀词,曰‘丧鼓歌。丧家酬以酒馔。”清《长阳县志》也载:“临丧夜,众客群挤丧次,一人擂大鼓,更互相唱,名曰‘唱丧鼓,又曰‘打丧鼓。”三峡歌舞是体现巴楚文化巫文化特质的活化石。
参考文献:
[1]段渝,《先秦巴文化与巴楚文化的形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12—19页
[2]王善才,《“巴楚文化”的称谓不宜再使用》,《三峡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第20—21页
[3]管维良,林艳,《三峡巫文化初探》,《三峡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30—37页
[4]班固,《汉书·郊祀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
[5][8]李卉,《三峡歌舞源流述略》,《探索》,2006年,第3期,第143—146页
※(本文系2008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鄂西民族文艺与巴文化研究,编号:2008y245;2009年湖北省教育厅社科项目:鄂西民族文学的巴楚文化解读及其发展策略探讨,项目编号:2009)
汪青,女,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