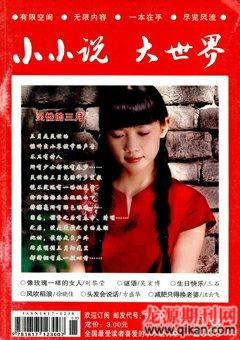风吹稻浪
徐晓佳
秋风还是吹弯了稻子的腰,一摇一摆,像荡秋千。
娘咧嘴笑。
是哩,稻子熟哩,得收哩。
娘就打来电话:崽,回来下呢,收稻哩。
我不情愿:快毕业,找工作投简历忙得焦头烂额,还有工夫回乡做苦力?
又不能回绝:家里只娘一人。
只得收拾下,踏上北归的火车。
到家。前檐屋后找不见娘,却在田间稻浪里发现了。娘朝我笑着说:来了好,来了好,穗沉得要断,正等人割哩。
可我心里满是忧虑:真要割稻?两亩多稻田,单靠两个人两把镰刀,割到猴年马月去?
急啥?娘站在田埂上说,这么些稻,还怕割不完?你爹在的时候,这点东西他一个人一会儿工夫就收拾利索了哩。你爹呵,插秧是只呆头鹅,割稻就是人来疯。
一阵风吹来,稻子窸窸窣窣。
我可受不了——怎叫人受得了?我说:娘,都啥年代了,现在全都机械化,机械化插秧,机械化施肥,机械化收稻,谁还傻不愣登地脸朝黄土背朝天?告诉你,你这叫小农思想,听我的,叫收割机,保管比爹割稻快多了。
娘脸偏一边说:啥叫收割机?我咋没听说过。
这开哪门子国际玩笑!人类都计划登陆火星了,娘竟说不知道什么是收割机!我四下张望,指着远处一台在田里工作着的收割机说:快看,就是那个,那就是收割机,一边朝前开,一边把穗子脱粒装袋。
娘低头对稻田说:娘是啥也没见着哩,崽。
不抬眼去看,怎么看得见?
我终于有点气恼,说:娘,你肯定舍不得那几十块收割费,别顽固了,现在是高科技时代,人该偷懒就偷懒,两亩多地靠人割怎么吃得消?
娘把手放到额头上,说:真的啥也没哩,崽。
存心不想看,怎么看得见!
——娘铁了心不想看见?
我不甘心。如此简单的道理,娘怎么就弄不明白呢。我说:娘,别心疼那几十块收割费了,现代社会几十块钱算个啥?不够领导抽包烟,不够老板吃顿饭,不够学生买双鞋。
娘不作声。
又一阵风吹来,稻浪便汹涌澎湃起来。
娘还是不出声。
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无奈,只得转身朝家踱去。可以想见,我将不得不套上破外衣,戴顶烂草帽,揣把磨得锃亮如新的镰刀,然后龙虾似弓背弯腰流血流汗地劳作。这不是我要的生活!我拼命学习,考上大学,想在城里寻工作,然后买房,买车,娶妻,生子,彻彻底底变成城里人……可眼前竟逃不掉这恼人的活!
我故意拖拖拉拉,磨蹭二十多分钟,才穿了那可恶的行头出门。是要拖拖拉拉,是要磨磨蹭蹭,本来就不情愿嘛。
但我始料未及:老远就看见一台收割机正在我家稻田里挥斥方遒。机器轰鸣,稻子成片消失,惟留下车轮碾过的痕迹。
我走过去,站到娘身边。娘揉着眼睛说:崽,你是不晓得哩,你爹呵,插秧是只呆头鹅,割稻倒是人来疯……
秋风又一次吹来,但再也吹不起稻浪汹涌,只微微撩起娘耳边几根老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