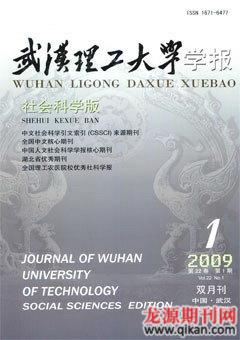党的文艺路线调整与伤痕文学的生成
王 烨
摘要:从新的只是立场重审伤痕文学已成为新时期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但人们多探究伤痕文学与文革文学在叙事形态上的相近性,而伤痕文学摆脱文革文学模式并成为新时期文学序幕的社会原因并未获得充分研究。从文学的社会生产角度看,伤痕文学是党的文艺路线调整的结果,它逐步实现了文学政治意识形态叙事向个人叙事的转型,逐步完成了跟文革文学叙事风格的历史断裂,从而拥有了自我的当代文学史的特质及意义。
关键词:伤痕文学;文革文学;文艺路线调整;文学史特质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1.026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新的知识立场重返伤痕文学这个历史转折时期形成的文学现象,已逐渐成为新时期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人们发现,伤痕文学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先声或序幕,在文学观念、审美特征及叙述形态上,与文革文学乃至17年文学仍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可以说,没有17年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的想像形式,已成为当下重审伤痕文学的历史想象方式。在这种“重审”中,人们多探究伤痕文学与文革文学在叙事形态上的相近性,而伤痕文学脱离文革文学模式并成为新时期文学序幕的社会原因,并没有获得细致、充分的研究。因此,多层次地探究伤痕文学生成的社会外部系统,而非仅是内部“叙事”形态上的解读,已是这次重返伤痕文学历史现场不该遗漏的话题。人们已经发现,有些文革时期的文学青年后来成为新时期文学作家的组成部分,伤痕文学在社会情绪诱导方面的功能跟文革文学也没有多少差异。本文从党的文艺路线调整的视角,探讨伤痕文学在文革后生成的历史动因与过程。
文革期间,文革激进派推行的文革文艺路线,导致文艺社会生产的匮乏与凋零,文革文艺路线的调整成为文革后期党的一个任务。文革结束后,文革文艺路线被视为“四人帮”的阴谋文艺而被废止,党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双百方针”得以恢复,被视为党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达与繁荣的正确路线。党在文革后期调整文革文艺路线的初衷,并不仅是政治路线斗争在文艺上的反映,它也真正蕴涵着革命领袖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渴望。但是,这次文艺路线调整却受到文革后期政治形势转折的巨大影响,文革文艺路线“调整”终于意外地实现了“置换”。可以说,伤痕文学的出现正是文革文艺路线调整及被置换的一个社会结果。
江青主持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其《纪要》,标志着文革文艺路线、纲领的诞生。《纪要》发展了毛泽东1963年、1964年关于文艺两个批示的精神,把建国以来的文艺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黑线,表示要通过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把它彻底搞掉,以开创社会主义文艺的新纪元。在《纪要》的指导下,文革激进派以“灭资兴无”的革命运动,剥夺掉大部分17年作家的写作权力,停止除《解放军文艺》之外其他文学刊物的出版。积极进行“样板文艺”的创造。我们不能否认文革激进派创造社会主义新文艺“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渴求,以及开创社会主义文艺新纪元的政治激情。然而,文革激进派由于实行文艺专制主义以及绝对的文艺意识形态化,结果,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局面不仅没有形成,反而造成了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凋谢”的难堪局面。
到文革中后期,一向支持“文艺革命”的毛泽东开始批评文革文艺路线。他先是发现电影、戏曲、文艺作品比以前少了,1975年又批评文革激进派搞得“百花齐放”都没有了。不久,他就党的文艺问题发表书面谈话,明确提出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而“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1975年7月25日,他对电影《创业》作出重要批示,建议发行此片以利于党的文艺政策调整。毛泽东的谈话与批示。表现出他对文革文艺路线的批评,实际上也成为党调整文艺路线的真正政策“这年的七、八、九三个月中,毛主席关于‘双百方针,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这一系列指示,已经冲破‘四人帮的层层封锁,像春风一样在整个中国的文艺界悄悄地传开了”。
党的文革文艺路线调整,迫使文革激进派努力进行繁荣文艺的工作,也激发了“走资派”文艺家自我的文艺信念与创作热情。文革派1975年10月在上海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加紧实施文艺节目的组织、生产与演出。之后,在上海这座文革运动的一个重灾区,各剧院放映的电影遽然间丰富起来,革命京剧片、故事片、彩色故事片、科教片、新闻记录片等不断上映,旨意不仅是制造文艺繁荣的社会景象,而且是丰富市民日常生活的文化娱乐。不仅如此,文革激进派还积极筹划《人民文学》的复刊,企图把它办成像《朝霞》一样受其控制的刊物。如果说文革激进派执行文艺调整政策是以退为进的政治阴谋,那么,失去政治合法性的“走资派”文艺家,则在党的文艺调整的精神鼓舞下,一方面同文革激进派进行文艺路线与权力的斗争,另一方面也借机恢复“双百”文艺方针,1976年《人民文学》、《诗刊》两个重要刊物复刊,一批“毒草”影片解禁了,一些文艺作品和鲁迅的著作出版了。至此,“文艺界的状况开始好转”。然而,这次文艺路线调整因政治形势的逆转而半途而废,并被文革激进派诬陷为“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来整无产阶级,整掉以革命样板戏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整掉无产阶级在文艺界的领导权,以便他们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文艺”。
文革结束后,文革激进派的文艺路线因四人帮政治垮台而被废止及“肃清”,而“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成为党指导文艺的政治方针。即是说,文革结束后的党的文艺指导方针,以及重返文艺界权力中心的“走资派”文艺家,都渴望恢复“17年”时期的文艺政策与文艺传统,并把贯彻“双百方针”视为文艺上的拨乱反正,视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正确道路,即文艺“只能‘放,不能‘收”。这时期,文艺界除了逐步恢复文艺组织、整合文艺队伍、复刊文艺刊物以外,还深入批判文革文艺的“三突出”原则,确立文艺“形象思维”的创作原则。至此,文艺路线的拨乱反正实现了真正的历史转换,文革文艺路线甚至后期的调整被彻底摈弃,党的双百方针以及“归来”的文艺家所信奉的文艺规律得以确立,并被视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真正地到来。
《人民文学》从1977年开始介绍文艺必须用“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去打动读者的心”的创作规律;时年11月,编辑部又召开了促进短篇小说“百花齐放”的座谈会。讨论如何提高短篇小说艺术质量的问题。《人民文学》引导文学创作遵循“形象思维”的原则,不久成为党的文艺政策并在全国贯彻。《文学评论》1978年复刊后,也旗帜鲜明地倡导文学“形象思维”的特点。批判文革文
艺反“形象思维”的谬论及路线。《上海文艺1978年也发起了“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强调文学形象要有独特的“个性”。这样,文艺的形象思维原则就成为了文艺界清除文革文艺“假、大、空”的“解毒良药”。不仅如此,文艺界还深刻认识到,文革时期文艺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弊病,实质上根源于“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文艺观念,认识到它实质上“忽视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忽视了文艺的特殊规律”,所以,文艺界积极呼吁要恢复文艺“用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创作原则。
总之,文革结束以后,由于揭批“四人帮”的政治运动影响,文艺界不仅废止文革文艺路线,恢复与贯彻了党的文艺“双百方针”,而且确立了文艺“形象思维”的美学原则。这样,文革后期就开始的党的文艺路线调整,因为“四人帮”的政治失败而骤然间被置换,文革文艺路线及蕴涵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念被清算,以形象反映生活的文艺观念获得重建。即使在批判“四人帮”的文学写作热潮中,文艺界也呼吁要克服文革“帮味”式的创作风气,鼓励作家“观察现实中各种生动的生活方式和斗争方式,描写各个阶层、各种各样的人物的心理和面貌”。文革文艺路线的清算与文艺“形象思维”规律的确立,终于催生了伤痕文学的诞生,党繁荣文艺的渴望也以文艺界对“双百方针”的拥护而实现。更为重要的是,文艺界终于盼来了渴求许久的社会主义文艺百花齐放的“春天”。
以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立场看,伤痕文学叙事形式的粗糙和陈旧十分明显,它参与“新时期意识形态的建设”的叙事实践也有为政治服务的嫌疑。由此,人们愈来愈怀疑伤痕文学表征“新时期”文学开端的合法性。这种历史重审虽然揭示了伤痕文学的历史复杂性,但是淡化了伤痕文学与其生产语境的关系,无法全面呈现伤痕文学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即它有别于文革文学的历史断裂性。诚如洪子诚先生所说,伤痕小说的出现预示着对文革文学模式的脱离,显示了文学“解冻”的一些重要特征,即“对个人的命运、情感创伤的关注。和作家对于‘主体意识的寻找的自觉”。
从文艺政策调整的角度看,伤痕文学是在“以形象反映生活”的文革后文学语境中产生的。1977年邓小平政治复出后,积极开展教育、科学等战线上的拨乱反正,“这对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包括恢复文学创作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为伤痕文学之父的《班主任》,就是《人民文学》编辑部“闻风而动”的结果。编辑部首先向熟悉教育工作并有着写作潜能的刘心武约稿·小说写成后“立即在编辑部范围内引起了震动”,然后,作者又按编辑部的意见作了些许修改,最终顺利地以小说头条位置发表。这篇小说问世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并非因为它反映了当时教育战线“抓纲治国”的新面貌,而是因其深刻的思想力量揭示了“四人帮”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内伤”,即谢惠敏这个小说人物呈现了文革政治给人们造成的心灵愚昧与僵化。总之,谢惠敏的形象塑造显示了“作者对生活现象的敏锐的洞察能力”,呈现出文学创作“一扫帮气”的历史性转变。尽管《班主任》的小说情节、主题以及作者的叙事声音,都明显残留着文革文学的气息,但它被当时的文艺界视为文学转折的历史标志,被视为文学创作上的成功典范,起着“引导和促进其他作者在一个新的创作道路上探索前进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者已指出,《班主任》实质上隐喻当时社会愿望的正当性及政治话语的历史转换。换言之,它仍然以文学叙事指涉政治领域的权力,并没有冲破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文学观念。和它相比,卢新华的《伤痕》“更接近文学的特性”,标志着“由写概念的人到写具体的人,理想的人到现实的人的开始”。它虽说是一篇大学生的文学习作,但它以稚嫩的叙述技巧,展现了文革给生命个体造成的感情创伤,展现了政治领域的权利冲突造成的个体人生信仰的迷乱与困惑,展现了泛政治化的国家生活对生命个体血缘伦理秩序的破坏及祸害。因此,主人公王晓华的心灵挫伤。并非仅仅是对文革“血统论”的政治愚昧的批判,也并非仅仅是对生命个体忠诚政治权威的现代迷信的精神反思,它其实还隐喻一个深刻的心灵悲剧,即个体对“无限”虔诚地神性信仰跟神性天国的意义荒谬的二元冲突,表达了政治浩劫之后个体意识复苏的心理情绪,隐喻个体对信仰王国的怀疑及世俗伦理意识的复苏,真正引爆了“伤痕”叙事的文学写作热潮。那些展现由政治动乱而铸就个人生命“伤痕”的感愤型作品中,“大都以人伦关系的破裂作为情节”,表达了对文革政治的控诉和重返世俗秩序的个体意识转型。因此,《伤痕》才象征文学真实反映生活、人情、人性的时刻到来,象征文学表现个体生命体验的时期到来,它已完全“避免了帮八股那种空、假、滥、绝的文风”。
不可否认,众多的伤痕文学叙事多把“文革”叙述为个人痛苦命运的社会根源,这既隐含着文革后政治权威对社会情绪的有意识诱导,又呈现了伤痕文学向真正意义上的“新时期文学”转换的历史艰难。在这种意义上,张洁是真正冲破政治意识形态藩篱的新时期作家,她将文学创作引向了作家自我抒情的发展方向。张洁被当时文坛誉为文学“新苗”,其创作为文坛吹来一股优美而奇异的新风,令人仿佛看到了一幅幅优雅而娟秀的淡墨山水画。她的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把音乐家受迫害而屈死的“文革叙事”推向背景,以一个由森林深处而来,具有音乐天赋的学生考取音乐学院的经历,表达了对纯洁、高尚等美好社会感情的向往与赞美。这篇小说不仅驱除了文革留给人们的梦魇记忆,不仅表现了“经历了深刻的痛苦之后的欢乐”,而且表达了对生命、社会、历史的高尚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心灵渴求。在张洁那里,文学创作不再是政治意识形态叙事的转喻者,而成为作家表达自我情思的抒情方式。至此,伤痕文学才实现了跟文革文学叙事模式的历史断裂,才象征着个体体验性叙事的文学意识的形成,才终于迎来了个体体验性叙事的发达与繁荣。无论是王蒙、张贤亮、从维熙等“归来派”作家对“少共情结”的抒发,还是礼平、孔捷牛、叶辛等知青作家对知青命运及心理情绪的表现,方之、林芹澜等作家对社会、历史荒谬感的传达,陈建功、周克芹等作家对政治激情失落后人们心灵落寞的揭示,都表明伤痕文学已从“‘改换文学的叙事歧路上突破出来”,实现了文学向“入学”方向的真正转型。
总之,在文革结束后政治转型的社会语境中,文艺界不仅积极进行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斗争,而且也逐步确立了“形象思维”的文艺观念,使文学创作逐步摆脱了文革文学的叙事风格,完成了文学由意识形态叙事向个体体验性叙事的历史转换,逐步实现了伤痕文学跟文革文学的历史断裂。这种文学风格的历史断裂。使伤痕文学拥有了自己的文学史特征及意义。我们认为,伤痕文学标志着文学表现个体生命感性的历史开始,隐喻作家个体写作权力的恢复与拥有。在这种意义上,伤痕文学不仅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序幕,带来了社会主义文学复苏、繁荣的社会景象,而且呈现了文学叙事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些疏离。从“歌德与缺德”的争论到对自由化、异化、人道主义等思想的批判,都隐喻着伤痕文学个体性叙事的自由追寻与政治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背离。
(责任编辑曾毅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