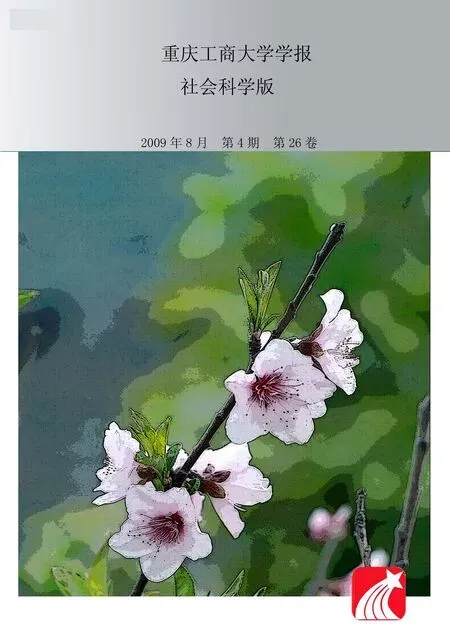从语义变化探察英汉语中性别歧视的社会根源*
苏 琴
(江苏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初教系,江苏 连云港222006)
一、语义中的性别歧视
英语中许多词语仅有表示男性的用法,没有体现女性存在的形式,如forefather,freshman,man-made,manned-vehicle等;有些表示男性的褒义词没有相对应的女性褒义词,如:chairman,Man of the Year等;而有些表示女性的贬义词没有相对应的男性贬义词,如shrew,virago,bitch,wanton等。另外,mistress是“男人的情妇”的意思,而同一词根中没有表示“女人的情夫”的对应词。
汉文化里的“龙”“凤”是富贵、吉祥的意思,形成独特的龙凤文化。龙指男性,凤指女性,所以人们有“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思想。古代皇帝称为“真龙天子”,他的后代被称为“龙子、龙孙”;皇后则以“凤”相称。皇帝和皇后被喻为“龙凤相配,龙凤呈祥”。“龙”又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故有“龙的传人”,然而,却没有“凤的传人”。
即便是同一个词用于不同性别的人时,意思却完全不同,指男性时为褒义,而指女性时变成了贬义。英语中的如easy指男性性格随和、容易相处,而指女性则是水性杨花;aggressive指男性有魅力的、可尊敬的,指女性则是没有同情心的。另一方面,不同性别的人在相同的地方,竟成了意义差别巨大的人,如:
the man in the street(普通人)
—the woman in the street(妓女)
—a public man(担任公职的人)
—a public woman(娼妓)
从这两组词看出,男人在街上、在公共场所是一个正常的人,而女人在这些地方就成了妓女,这说明了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有一个无形的标准,即将女性定位只能待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伺候家里的人,不能出门在外。汉语里类似的情况如“虎”字,用在男性身上,意思是男人勇猛威武,身体强壮,力量强大,用在女性身上,意思是嚣张霸道,专横无理,令人讨厌生畏。比如说“这男孩长得象小老虎,虎头虎脑的,很可爱。”《三国演义》第二回里说“为首一将,生得广额阔面,虎体熊腰。”[1]说明这个将士身材强壮,是员猛将。但用在女性身上,通常会形容女人是“母老虎”,非常令人讨厌;若形容女子身材又丑又胖,则讽刺她“虎背熊腰”。比如有报道说:“布兰妮自曝体重57公斤,虎背熊腰肉光四射”。
人们也常会发现在汉语中凡原来用于男性的词汇,用于女性时往往不带有贬义。而原来用于女性时的词汇用于男性时则至少带有轻蔑的意思,如当人们用“假小子”称言行很像男子的女子时并非带有贬义。有时人们还称某女子是“女丈夫”表示对该女子的杰出行为的称赞。但当人们说某男子有“女人气”、“娘娘腔”或“婆婆妈妈”时却带有强烈的贬义。
在英语文化中,有的词从开始的褒义逐渐转变成中性,最终演变成贬义。这种语义变化现象多见于与女性有关的词语。如harlot原来在语义上并没有性别选择,在中世纪英语中,它更常用于指代男性。自从伊丽莎白时代后,harlot进一步贬义化,从lewd的语义发展为专指a disreputable woman,后来进一步沦落为“娼妓”。tart这个词的贬化过程也是非常明显的。tart原指“馅饼”,后来表示对年轻女子的“亲爱的”昵称,再后来指“轻佻的女子”,而近来又指“在街上拉客的女子”。“妓女”的同义词在英语中有500多个,对应的男性名词仅有90个,这500个“妓女”的同义词往往由一般表示女性的词汇降格而来。汉语中如“秘书”,原意是指“掌管文书并协助领导处理日常工作的人”[2],现在随着嫖娼现象的出现,“女秘书”逐渐转变成了“妓女”的代名词,成了贬义词。类似的还有“女公关”、“女招待”等。汉语中也有许多侮辱贬低女性的说法如“野鸡、破鞋、二锅头、贱货”等,也都是一般的词汇降格而来的。再比如“雌雄”,本义是表示不同的性别,后来意思逐渐向两个方向发展,“雄”有“强有力的、强有力的国家、伟大”的意思,被褒义化,如“雄师、雄伟、雄才大略”等;而“雌”有“胡乱涂改、随口胡说”的意思,被贬义化,如“妄下雌黄,信口雌黄”。说男人发“雄威”是表扬和赞许,说女人发“雌威”是鄙斥和厌恶,有明显的贬斥之意。英汉词汇中贬低女性的词汇多于贬低男性的词汇,并不是说社会上女性比男性更胡作非为,更道德败坏,而是因为男性在社会中占统治、支配地位,社会价值标准是男性制定的。他们对男女道德要求严重不对等。
人们用动物比喻男人和女人,并把自己的好恶和褒贬也带进了这种比喻。由动物的形象及其比喻引起的联想常能产生各种各样受民族文化制约的附加意义,这种附加意义反映的就是民族心理特征以及民族风俗和伦理道德观念。如,cat,猫,心地恶毒的女人;cow,母牛,肥胖粗笨的女人,婊子;bitch,母狗,坏女人、淫妇;hen,母鸡,尤指爱讲闲话或爱管闲事的女人;bat,蝙蝠,妓女;slut,母狗,邋遢女人,妓女;shrew,地鼠,泼妇,悍妇。
斯彭德在《男人创造语言》一书里说,工作和社会并不包括照顾孩子和操持家务,因为这些都是没有报酬的。所以,“家务劳动(housework)”,排除了妇女所做的工作,就其定义而言,也不是工作。妇女虽然非常辛苦地劳作,但是她们所做的工作得不到社会的承认,甚至女性有时也会自我贬低说:“我不工作,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
从这些词汇的运用上,我们可以推断出指男性的词汇通常都是普通、常用的,而指女性的词汇是把女性作为无用的人和附属品,这反映了语言对男性而非女性有主观上的倾向。
二、成因
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从父权制社会至今,男性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王权是政治统治的核心,父权则是宗法制度的基础,二者共同构建了一整套完整而严密的社会组织形式。”[9]这种男权制度从父系氏族开始,历经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直至今天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汉民族的意识观念。在帕特曼(1988)的著作中,现代自由国家中的“父权制”已经变成了“兄弟制(Fraternity)”。在“父权制”中,父亲既统治着男人,也统治着女人。而在“兄弟制”中,男人在私人家庭领域中统治自己的女人,而在公共领域里,男人之间彼此建立了平等的社会秩序。伊瓦·戴维斯(Yuval·Davis)在《性别和民族的理论》中提出,妇女受压迫的地位是与社会中权力和物质资源的分配有着密切的关系的。男人以自己的性别为本,制定出维护男性统治天下的制度。女人为了得到选举权,要和男人进行斗争,为了得到平等的公民权,也要和男人进行斗争。即便是现在,当我们提到某某领导的时候,人们首先认为这个领导是个男性,也就是说社会上的政治经济大权仍然大部分掌握在男性的手中。当然,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女性的统治者,如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中国历史上的武则天,但是她们只是极少数的个例而已。所以,根据萨王尔·沃尔夫的假说(Sapir-Wholf Hypothesis ),语言不仅仅是社会的产物,还能反过来影响人的思维与精神,因此性别歧视语言又在以某种方式促进社会心理定势的形成,维持着一个压迫女性的社会。男人们甚至把一个国家的灭亡和朝代的更替都归罪于“红颜祸水”。
在文化方面,男女之间诚然存在着生理意义上的性别(sex)差异,但这并不足以造成人类文明史上如此巨大的性别鸿沟,是延续至今的父权文化导致的对女性的歧视。西方国家的人普遍信奉基督教,其经典著作《圣经》对人类的影响很大。语言学家在追溯英语中性别歧视的渊源时,都常常提到《圣经》的影响:耶和华用世上第一个男人亚当的肋骨创造了第一个女人夏娃,他对夏娃说“女人,你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你必须依附男人。”让人们从心理上接受女人是男人身体的一个多余部分,要永远附属于男人,做男人的仆役。莎士比亚在《王子复仇记》中写到:Frailty, thy name is woman!(弱者,你的名字叫女人!)。在中国,儒家思想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就说:“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还说:“女子无才便是德。”至今,中国百姓还能顺口说出来,足以见其影响是多么的深远。儒家思想中的“男尊女卑”、“男外女内”、“三从四德”等女性价值观念和道德礼教观念,千百年来一直禁锢着中国的女性。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玉皇大帝是男性,王母娘娘再有本事,也只是玉帝的妻子,不能和他在权利上平起平坐。“在世界各国许多神话中,男性往往被当作‘物种之范’,而女性则是男性的变体。即便女性有时也受到‘富饶之神’、‘大地之母’等赞美,但她最终仍逃脱不了‘万恶之源’的罪名。”[16]文化通过语言反映社会现实,同时语言也是文化的形式之一。语言中男性常被描述为有能力、有魄力、有远见,而女性常被描述为被动、无力、多话。
在思想方面,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早期西方文明,曾用貌似“理性”甚至“科学”的语汇,指出女性有重大缺陷。例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男子“在各方面都超过妇女”。亚里士多德说女人是一种自然的残缺,正常的人类胚胎在正常条件下都发育成男人,只有那些残缺不全的胚胎才变成女人。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先天缺陷,女人后天形成许多不可克服的毛病,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愚蠢。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则逐渐将古人的“阴阳”宇宙说演变为无所不包的伦理哲学体系。古老的阴阳观念逐渐被儒学改造成泾渭分明的主从系统,失去了平衡。“阴阳”原始的互补关系,逐渐退化成“阳”对“阴”的压迫与奴役关系。即“天尊地卑”,“阳尊阴卑”,“男尊女卑”。“经过了这样一番理论上的演绎之后,女性性别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西蒙·波娃所说的‘第二性别’,为男性对女性的支配统治找到一个像模像样的理论前提。”[8]古代的“夫为妻纲”、“三从四德”就象紧箍咒一样千百年来牢牢地禁锢着女性的思想,摧残着女性的身体。从远古的女子陪葬到近代的女子裹小脚、立“贞节牌坊”,哪一样不是男性挖空心思想出来束缚女性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支配权的。
在心理方面,人一生下来就被烙上“男尊女卑”的烙印。西方人都从《圣经》里知道女人是男人的一部分,要依附男人。在中国封建社会,婴儿出生时,就因为性别的不同而遭受不同的待遇。《诗经·小雅·斯干》中有这样的诗句:“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大意是:生了男孩子,就给他穿上衣服,睡在床上玩玉;生了女孩子,就给她裹上被子,睡在地上玩纺锤。这显然是天壤之别。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后”就是儿子,家族的地位、产业和手艺是传给儿子的,不能传给女儿,因为女儿终究是要嫁人的,是人家的人。人们可以从心理上接受男子撒野,说粗话,高谈阔论,对人发号施令,却不能接受女子做着这些事。时至今日,还会发生扔掉女婴的现象,可见重男轻女的思想在大部分中国人的心目中仍然根深蒂固。
在社会地位方面,性别角色、性别身份以及与其相适应的角色行为,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完成的。歧视语言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人类早期社会经历了“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两个发展阶段。在母系氏族社会,女性地位较高,处于支配地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到父系氏族社会,男子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于是男性逐渐处于独立的、统治的中心地位,而女子越来越失去自己的地位和尊严,被置于一个从属的地位。由于社会分工、社会地位的差异,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某种潜在的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的导向。整个社会对两性所产生的不同期望使得男性处于独立的、统治的中心地位,男性主宰着社会;而女性则处于从属的地位,只能从事家务劳作,被排除在权利、利益之外。即使女性与男性从事着相同的工作,她们的成绩也不能象男性的那样容易得到认可,有时获得的报酬也比男性低。
在教育方面,文化教育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当孩子一生下来,因为性别的不同,就穿不同的衣服,玩不同的玩具。几乎整个社会和所有的家庭都对男孩和女孩进行不同的价值观、社会观和行为规范的教育:鼓励男孩子要刚强,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要有主见、有进取心、有独立性和冒险精神,要成为男子汉,社会栋梁之材;鼓励女孩子要富有同情心,有耐心,有礼貌,要温柔文静,所谓“女人是水做的”,要会打扮自己,要嫁个好人家,成为贤妻良母之人。英国女作家玛丽·沃斯通克莱夫特在《妇女权利论辩》中指出:“妇女的卑劣是由于给她们以卑劣的教育与培养造成的。”她认为“‘女性’是教育培养的结果”,“女孩喜欢玩娃娃是因为不给她们其他的玩具”。整个社会鼓励男性从事社会性的劳动,而规定妇女必须为家庭服务。男性与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时时刻刻受到这种观念的灌输,并根据这种观念来修正自己的行为、举止,在成年生活中进行整饰。这样,这些观念被内化、接受,渗入人心,极大地影响人们的心理和行为。
当然,还有很多方面,都有对女性的歧视。比如说法律方面,曾有男人可以随意休妻的制度;还有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法律,之所以有这样的法律,就是因为妇女一直以来都是弱者,像儿童一样需要人来保护和照顾,那只有靠男人来保护了;在军事方面,“战争让女人走开”并不仅仅是一部电影名称,事实就是这样,虽然女人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获得荣耀和声誉的永远是男人;还有在哲学、宗教、大众传媒等方面都可以看到其中的性别歧视。
总之,语言性别差异产生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上述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三、发展
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语言中的性别歧视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现在,语言学家和全社会其他方面的人都在尽力规范语言,力争最大限度地消除语言中的性别歧视。语言学家们也提出了消除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的一些建议。我国的语文工作者对语言性别歧视也已开始关注。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地位得到了改善。如女性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就业中等方面的地位有所提高,妇女普遍充实到政府、法律、企业管理、医疗、教育和计算机工程等各个行业,一改以往男子一统天下的局面。男女地位逐渐平等,这些现象反映到了语言中,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也随着某些社会现象的消失而逐渐消失。男女地位的巨大改变,“并不意味着可以消除人类两个变异体的全部现存差别而归于划一。未来社会并不会消除两性之间现存的差别,它将为男女特有的素质最合理地发展提供广阔天地。男女两性所固有的长处和短处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它们相互补充、相互补偿,形成人的完整画像。”
[参考文献]
[1] 刘小云.英汉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及变革[J] .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4).
[2] 吴长镛,姚云竹.汉语中的性别歧视[J] .修辞学习,2002(6).
[3] 孙汝建.性别与语言[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4] 张娜.英语中对女性性别歧视语言的词汇特征[J] .文教论坛,2007(7).
[5] (英)玛丽·塔尔博特.语言与社会性别导论[M] .艾晓明,唐红梅,柯倩婷,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 现代汉语小词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7] (明)罗贯中.三国演义(上册)[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8] 欧阳洁.女性与社会权利系统[M] .沈阳:辽宁画报出版社,2000.
[9] 贺友龄.汉字与文化[M] .北京: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出版社,1999.
[10] 陈顺馨,戴锦华.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11] 沈锡伦.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12] 罗宁萍.英语性别歧视语的文化分析[J] .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5).
[13] 王德春,孙汝建,姚远.社会心理语言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
[14] 白解红.性别语言文化与语用研究[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15] 孙绍先.女性主义文学[M]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
[16] 王德春,杨素英,黄月圆.汉字谚语与文化[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