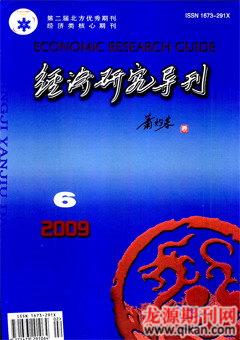货币的有关经济人类学解读
黄福东
摘要:货币作为现代经济运行的基石,其作用和意义毋庸置疑。然而,如果我们从货币的诞生、使用和发展这一个大的范围来看,就可以发现货币带给我们的思考应该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经济人类学最独特和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它的研究视角——从人类学的角度去研究分析人们的经济行为与经济生活。所以,经济人类学对货币的看法和研究,或许会给我们观察现代经济带来某些启迪。
关键词:货币;价值;经济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F8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6-0051-03
这里所费力阐述的思想应当是非常简单和显而易见的。困难并不在于提出新的思想,而在于摆脱旧的思想束缚,对于绝大多数跟我们有着相似成长经历的普通人而言,那些旧思想却是遍及我们头脑中的各个角落。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一、货币的产生及其演变
经济人类学在看待和分析历史上交换现象的产生及其变化时,注意到了其他的一些方面。早期的人类学家们在田野考察中就发现,西太平洋美拉尼西亚地区的特罗布里恩岛的“库拉”交易圈中的交换手段——红色贝壳项链“索拉瓦”和白色贝壳手镯“母瓦利”的“特殊”交易形式。著名人类学家马凌诺夫斯基在他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指出:“索拉瓦”和“母瓦利”在其本身并无直接经济有用性,却拥有一种社会身份的认定和稳定的非经济的社会含义;而与此并存的“财富标志”,也是用“希罕并难于获得的”材料并花费“大量时间和劳动”来制作的,并且是在他这个西方人看来是“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用途”的“仪式使用的斧身”[1]。
换言之,如果完全不从“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角度去思考的话,那么很多其他文化状态下的经济行为,其实是与其社会的制度性因素和传统性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经济行为不仅有着“经济”目的,更有着族群关系、道德风俗、宗教礼仪等方面的诉求。因此,在马凌诺夫斯基看来,红色贝壳项链“索拉瓦”和白色贝壳手镯“母瓦利”的交换现象的本质就很能说明问题。即,其他文化状态下的经济行为与西方文化中的资本主义关系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是不可能用西方经济理论去阐述与分析。
粟本慎一郎在其《经济人类学》中总结到:人类学的诸多资料都表明,“被‘无文化民族用作货币的物体中很少是具有使用价值的,大多是给展示它们的人带来声望。”同样也可以看到的是,“黄金和银根本不是必要的使用对象,所以它们也被排斥在直接生产过程之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同样明确地表示:“商品的价值形态与商品的对立,只是为了马上又消失。”因此在“W—G—W”过程中,与货币不断换位的商品相继退出流通,而货币同一个又一个商品的位置变换使其始终驻留在过程之中。由于“运动的连续性完全落在货币方面”,由于“货币流通表示同一个过程的不断的、单调的重复,”“所以在货币流通中就隐藏着一种可能性:可以用其他材料做的记号或用象征来代替金属货币执行铸币的职能。”因此就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货币作为剩余使用价值的特点,隐含着以前我们不是很了解的其他方面的丰富内涵。
所以,黄金、银同别的财富形式的区别何在呢?通过以上的观点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其实,黄金和银同别的财富形式的区别不在于其价值量(因为价值量是由其中物化的劳动量决定的),而是在于它们是财富的社会性质的独立体现和表现。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黄金和银的本质就可能是其绝对毫无价值,因为关键是,你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当中。从经济人类学的分析看,事实上,以合理用途和真正的人类需要来衡量,现代经济中的黄金、银和古代经济中的贝壳、狗牙或羽毛束在实质上毫无区别,南太平洋雅普岛的那些“即使在海下也继续象征着价值的巨大石盘与欧洲诺克斯堡地下的黄金也并无不同。”[1]
现代国际通货理论的权威波尔·爱因齐格曾为了弄清包括“金问题”在内的现代通货问题的本质,以数年时间完成了《原始的货币——从民族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一书,受到了经济人类学者的高度评价。研究古代经济的权威海希尔海姆指出:在古代近东地区附加于金银之上的价值,本质上具有巫术——宗教的性质;经济学家约翰·洛克对这一现象的表述是“人类同意给金银赋予一种想象的价值”。著名经济学家、有效需求理论的鼻祖凯恩斯在其《货币论》中充分承认:现代经济附加在金银之上的想象的价值,完全是从宗教领域中衍生出来的。他曾写到“古老埃及祭司的巧计使这种黄色的金属充满了其有魔力的特性,这至今也没有全部丧失。”
这就给我们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对黄金的崇拜就成为欧罗巴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而这种特征延续下来的结果,就是只要历史上有欧洲人参与的交易中,他们对黄金的疯狂追逐和极端贪婪就会表现得非常强烈,甚至令人憎恶,这是其他民族所无法理解的。
二、货币的实质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
其实,只要理解到货币所具有的一种接近又超越社会物质财富的、真正具有的物质或商品这种社会存在的本质,就能清晰地了解到“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的这句名言。事实上,前半句道出了这种存在与表现的关系本质,而后者简洁地告诉我们,正如经济人类学已经不客气地指出:完全是“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一种观念反映和陈述。
经济人类学在进一步解释了黄金和银的“无用性”或“无价值性”之后,那么就能清楚地看到,当人类把货币的贮藏手段功能定位在黄金和银上时,贮藏的实质并非金银的“实物性”或其自身的“物质有用性”,而是人类社会赋予它的一种“权力关系”的价值。不过,必须要注意的是,一旦另外的社会关系成立,用于货币贮藏手段的“实物”也就不可避免地随之变更。本质上,现代社会中的贮金与古代社会中的贮贝,甚至与现代社会中更为常见的对纸币这种被社会学家克纳普和人类学家韦伯称之为“官许凭证”的保有,实在是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唯一的不同仅仅反映了“权力赋予”的社会情境的变化。
事实上,经济人类学一再论证了货币表现出不同的功能,甚至可以表现为目的本身,而这些不过反映了货币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不同的功能,是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的职能扩展。著名经济人类学波拉尼以“有限目的货币”和“全目的货币”概念,强调了货币的社会性规定。粟本慎一郎指出,波拉尼对“货币在不同社会中的不同用法以及货币在这些社会中所发挥的不同功能,并以对货币作为沟通社会与经济之间的一种制度性手段的描述,形成了对现代经济学货币理论的重要补充。”[2]
(二)货币是社会的各种关系和各种要素的联结
从经济人类学已经收集和研究的大量资料中看,许多货币的原始初期形式,其实既非粮食也非贵金属,而是超出劳动价值衡量的商品范围。如,历史上西太平洋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的开孔平石,新几内亚的木制胸甲,新不列颠岛的犬牙,以海贝为基质的罗塞尔岛的达普币和达荷美的安产贝,以及斐岛的鲸牙等等。用拉德克里夫一布朗的话说,它们是具有最高社会价值的物,带有构筑更大社会关系和社会整体的能力。比如,在太平洋中的雅普岛,巨大的石盘就是一种“货币”,但它们几乎无法搬动,因而也就无从谈起便利性;更重要的是,这种用于礼仪性交换的货币——石盘,是其他价值不能与之折合的;存在于特罗布里恩德岛“库拉”交易圈中的“货币”——用贝壳做成的红色项链“索拉瓦”和用贝壳做成的白色手镯“母瓦利”——也具有类似的价值不可转换性。通过实地观察与研究,马凌诺夫斯基指出,“库拉从其影响的地域范围及组成事物的多样性来说,是一种极为庞大与复杂的制度。它将数目可观的部落联结在一起,并从事着大量互相关联、彼此作用的复杂社会行为,从而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1]
粟本慎一郎在其《经济人类学》中指出,鲸牙在斐济岛“遵从礼俗而认真地呈献,作为酋长间的交易,鲸牙安排战事、刺杀、贵族联姻,鲸牙缔结或解除政治联盟,鲸牙拯救濒临灭亡的村庄和王国,鲸牙祈诉神和恩典。从它能创造社会,予生予死的角度看,鲸牙与神旗鼓相当……。”于是就有航海家霍卡特得出的鲸牙的交换价值:几两重的神性等于成磅的粗货。因而也就有当时斐济人所持的观点:在19世纪国家形成的过程中,鲸牙的作用远胜毛瑟枪。流通的鲸牙愈多,斐济群岛上存在的国家愈强大。
同样我们从人类学的经验资料中可以看到,货币的原始初期形式,是先于其任何功能而存在于社会中的一种对象物。这种对象物必然是为人们所珍重和崇拜的、拥有精神威力的东西,有时甚至成为维持族群共同体的精神支柱。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虽然也曾看到货币形式固定在不同物质材料上的偶然性;但他还是天才地发现,从交换过程的固有逻辑中看到,“金银的使用价值的性质就在于它应是某种多余的东西。在商品流通的初期,只是使用价值的多余部分转化为货币。这样,金和银自然就成为这种多余部分中财富的社会表现。”
从这些实例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不能仅仅从货币作为商品的这一项物质基础来考察货币的本质和存在形式的重要意义,货币之所以具有社会性的力量,乃是社会的各种关系和各种要素的联结。
(三)货币的文化意义
货币的存在一直被概念地当做一种“超现实的物”。然而,这种超现实性并不只是唯一地限定在某一物质上,货币对象物的具体形式究竟体现为黄金、银、铜还是海贝、豚牙或现代的纸币等等的物质形式上,其首先在历史上就表现为一种偶然,而这种偶然性,又强烈地透出不同文化实存的决定关系。
在中国早期多民族部落群体“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的过程中,货币的存在一方面体现在不同的实物形式上,另一方面,黄金虽然成为货币存在的最早形式之一,却未能成长为中国多民族经济中的货币主导形式。这充分表明,符号货币本身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物理特性来告诉人们,这种货币提供什么质量的货币性服务。“因此,如果仅从现代经济学中的特定物质的物理性质或经济性供给的角度去理解货币的不同形式的存在,是极其片面的。由于其对文化解释的严重缺失,使对货币存在和发展的研究方向出现了片面的趋向。”[4]
可以看到,物的价值同物的实体分离是在货币的符号形式上得到完全实现的。但也正是在这种形式上,货币展现出了它的社会性质。货币,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从而作为物体化的财富,曾在炼金术中被人追求。而黄金作为人们最先知道的金属,在人类进步的最初记录上,被认为是人类状况的尺度。但是,人们并不能在黄金的物质化学结构上发现其价值,而正是其象征价值使黄金的客观特性成为了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同时,一方面,黄金的生产“只需要人的最粗笨的劳动,既不需要科学,也不需要发达的生产工具”;另一方面,它既不作为消费对象来满足直接的需要,又不作为要素加入生产过程,因此,仅从劳动或商品的意义来认识金银成为货币或其象征材料的存在是不充分的。
经济人类学的这一货币分析视野提出了一个极为深刻的启示:货币的存在可能并不仅仅表现为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即便对当代的货币理论来说,这一分析视野也具有启示意义。众所周知,最具纯粹符号象征意义的货币形态是纸币。因此,在纸币这种货币的社会存在形式中,波尔·爱因齐格在《原始的货币——从民族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所表达的“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身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生产当事人个人的信仰。”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定,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类型与历史上的其他文明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波郎尼通过引用和分析马凌诺夫斯基等人的大量人类学素材,指出:在其他的文化形态中,物品的生产与分配制度等所谓的经济现象,其实是“嵌合”在整个社会制度当中,并且是属于从属的、相对次要的位置。
事实上,对于历史上的很多其他文明来说,交换行为根本上就不是像西方以货币为基石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类型那样,而更多的是根据亲属关系、政治的或氏族的权利与义务来进行分配。在其他文明历史上的经济生活中,尽管也有市场及其贸易行为,但是市场本身并不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占据着支配性的核心地位,而是边缘化的、附属或服务于其他重要经济组织与经济行为。从根本上说,“人的基本生计和权利是作为一个氏族成员的道德权利而被保证。”[3]
参考文献:
[1]马凌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北京:华夏文化出版社,1996:55-83.
[2]粟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M].北京:经济出版社,1998:91.
[3]施琳.经济人类学[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45.
[4]陈庆德.经济人类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王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