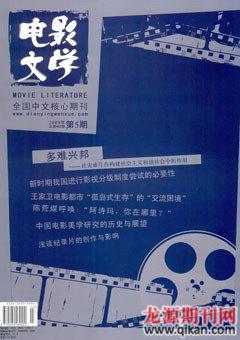苦难·屈从·抗争
冯永朝 王 颖
摘要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成熟女性意识的女作家之一。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多为农村下层劳动妇女,这些形象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屈从于苦难的女性,她们挣扎在“自然的和两脚的暴君”的双重奴役之中。一类是在苦难中抗争的女性,发出女性不甘卑弱、屈从、从属地位的声音,让挣扎于苦难和黑暗中的女性看到了一线光明。她们融合了萧红对封建男权制下女性命运的同情、思考和想象。
关键词女性,苦难,屈从,抗争
萧红十分重视题材与作家自身之间的亲密性,认为作家写的应该是那些自己熟悉的有独到认识和独特感受的生活和人物,她说:“一个题材必须要和作者的情感熟悉起来,或跟作者起着一种熟悉的情绪。”(萧红:《现实文艺活动与<七月>》,载1938年5月《七月》,第15期。)早年无爱,孤独的家庭环境使她有机会走近下层劳动妇女,熟悉她们的生活,了解她们作为女人的悲苦·叛离家庭、走上漂泊生活后,她多次受到男性的欺骗、背叛和伤害。亲身体味了在男权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的苦难和悲哀。正是凭借这种人生经历加上自己对北方劳动妇女的熟悉和了解,使得萧红拿起笔来,回望家乡时,将自己的笔触主要聚焦在自己熟悉的乡土文明的农村妇女身上,既写了她们备受压迫、歧视、侮辱和摧残的苦难遭遇,又写了她们在苦难中的挣扎、抗争和呐喊,成为底层势动妇女名副其实的代言人。
萧红笔下的女性包括寡妇、农妇、乳娘、童养媳等。这些女性形象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屈从于苦难的女性,一类是在苦难中抗争的女性。
一、屈从于苦难的女性
批评家李洁非曾说:“农业文化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男权文化。农村社会是二个绝对的男权社会,整个农业文明时代也是男性权威被强化,制度化、合法化,而女性则被进一步和全面剥夺、控制、奴役的时期,所有对女性造成压迫、使她们丧失各种自由、沦为男性附庸的宗教、伦理和政治经济制度,都在这个时期建立并且完善化。”萧红笔下的女性正是一群生活在中国北方受着牢固的以男性为中心本位的宗法制度控制下的乡村妇女。她们挣扎在“自然的和两脚的暴君”的双重奴役之中,不仅面临着与男人一致的社会危难和贫困饥饿等多重攻击,而且受到来自男性和传统势力的多重压迫,特别是她们的身体遭遇暴力,疾病、生育、死亡的痛苦侵害。这一切给她们带来的是生命的消失、肉体的苦难和精神的折磨。
1苦难的身体之痛
在《生死场》中,女人的生育没有给她们带来创造生命的自豪和喜悦,有的只是有如刑罚般的痛苦和灾难。小说在第6章中集中地描写了几个女人的生育过程以及生育给她们带来的痛苦感受:麻脸婆在生孩子时痛不欲生大声哭闹,“肚子疼死了,拿刀快把我的肚子给割开吧”;李二婶“小产了,李二婶子快死了呀”,年仅十七八岁“仍和一个小女孩一般”的金枝也未能逃脱这种痛苦的经历,“她在炕角苦痛着脸色,她在那里受着刑罚”。而最为凄惨的是五姑姑的姐姐,即将生产的她,因为婆家讲迷信,怕“压财”,将土炕上的柴草抽走,只能忍受着因难产所带来的巨大的恐惧和痛苦,“和一条鱼似的”光着身子在灰尘中爬行、哀号、挣扎。不但得不到丈夫的同情和安慰,反遭来打骂和折磨。男人用长烟袋投她,用冷水泼她,她“带着满身冷水无言地坐在那里,她几乎一动不动,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门响了,她又慌张了,要有神经病似的。一点声音不许她哼叫,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她仇视着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呀”。自然性别的劫难,更加上男人的粗暴与冷酷,女人的身体完全倒下了,“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
在《生死场》中,给女性带来身体之痛的并非只有生育,与生育相关联的性爱给女人带来的是更大的伤害,她们承受着男人施加于身的性暴力,体会着灵肉被撕裂的痛苦和屈辱感。青春少女金枝受着情欲的驱使,怀着对美好爱情的憧憬,被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成业的歌声感动着,向恋人敞开了少女的心扉。但她并没有得到性的欢乐。爱的抚慰,得到的只是男人一次次粗暴地占有。未婚先孕的金枝肚子越来越大,她心里害怕极了,于是去找成业商量婚事,要成业的叔叔赶紧找媒人来家里提亲。可被欲火燃着的成业却根本不顾姑娘病态的身体和恐惧心理,只想着在她的身上发泄情欲,他“用腕力掳住病的姑娘,把她压在墙角的灰堆上,那样他不是想要接吻她,也不是想要热情的讲些情话,他只是被本能支使着想要动作一切”。成家后的金枝遭到了丈夫更粗暴的对待,成业不顾她有孕在身和因劳作而疲惫的身体,只由着自己的欲望强行房事,导致她早产。差点丢了性命。在金枝与成业的性爱中,我们看不到两情的相悦,只感到“兽性”的发泄。性爱中的。爱”的成分已被抽空,只剩下赤裸裸的“性”的成分,而这“性”又是由男性单方面施予的,女性在性活动中完全是被动的,她无权要求或拒绝男人的性快乐,而只能充当男人泄欲的工具,施虐的对象,欲望的符号。在无爱的痛苦中经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年轻、健康的女人尚遭此粗暴的对待,那么等老了病了,对丈夫、对家庭尽不了女人的“本分”时又会怎样呢?《生死场》中月英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受虐待,遭厌恶,甚至被遗弃。月英是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她是如此温和,从不曾听她高声笑过,或是高声吵嚷。生就的一对多情的眼睛,每个人接触她的眼光,好比落到棉绒中那样愉快和温暖”。她脾气温和、轻言细语,她不嫌穷爱富,嫁到了村子里最穷的夫家。可以想见,当初她的丈夫因娶到她,会是怎样的得意和满足啊。可是“好人没好命”,她不幸患上了瘫病。起初丈夫还“替她请神,烧香,也跑到土地庙前索药”,见病情毫无起色,就开始嫌弃和打骂她,不给她水喝,“烧饭自己吃,吃完便睡下,一夜睡到天明,坐在一边那个受罪的女人一夜呼唤到天明”。后来,月英臀部腐烂生蛆,丈夫说她快死了,索性撒掉被子,只用冰冷的砖块依住她。被折磨得没有了人样的月英,眼睛、牙齿发绿,头发似烧焦般的紧贴着头皮,两条腿像白色的竹竿,整个身体弯成一个僵硬的直角形状。当前来看望她的王婆帮她擦洗身体,一掀开被子,看到的是满炕的排泄物中蠕动着白色的蛆虫。月英死了,这个美丽的女人死于疾病的折磨,更死于丈夫毫无人性的虐待和遗弃。
2屈从的精神之累
萧红曾慨言:“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啊,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我牺牲的惰性。” 仔细分析这段话,我们会发现,萧红不仅感叹、同情由于男权社会的压迫造成的女性生存空间的逼仄和被压迫、受歧视的屈辱地位,同时还从女性自身挖掘了造成这苦难、非人境遇的原因,那就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和“惰性”。这自我牺牲的“精
神”和“惰性”起初是由男权文化强加于女性的,是“他律”性的,久而久之在“长期的无助状态中“慢慢潜入女性的意识深处,成为女性的““集体无意识”,成为女性身边“笨重的累赘”,由“他律”变成了“自律”。在萧红看来,女性的这种自我牺牲的“情性”、“自律”性比来自于男性的压迫更可怕,它使得女性一味地顺从男性、屈服于男性,自甘为奴。《生死场》中的金枝、福发婶在男人粗暴地占有后,她们没有反抗,她们也不知反抗,只能忍气吞声地嫁过去。奴隶般地被任意打骂、凌辱,村中最无能、最懦弱的男人二里半在众人面前总是个失败者,可在他的老婆麻脸婆面前却可以颐指气使,大声斥责,而麻睑婆却从不敢反驳,在丈夫面前“她的心永远像一块衰弱的白棉”柔弱无声。同样,《呼兰河传》中的女性也没有自我意识,对一切都是逆来顺受,甚至认为本该如此。老胡家的大孙媳妇被丈夫打了,不仅没有任何反抗,反而对人说:“哪个男人不打女人呢?”于是便“心满意足地并不以为那是缺陷了”。可见女性麻木、顺从到何种程度。不仅如此,有些女性还将这种“自律”和“律己”转变成“他律”和“律他”,用这沉重的精神枷锁去牢牢地束缚其他女性,在窒息、毁灭自己的同时,也窒息、毁灭着自己的同类。在《呼兰河传》中展示了两位鲜活的女性过早走向死亡的悲剧命运: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小团圆媳妇原本是一个健康、充满生机的少女,来到婆家后,只因为个子长得高,吃饭吃得多,不会害羞,便招致左邻右舍女人们的百般挑剔、议论。婆婆为了规矩她,使她“像个团圆媳妇”,便白天黑夜地打她。小团圆媳妇被打出病来后,邻家妇女们又向她婆婆“献计献策”,怂恿婆婆为她请来了巫医,最终把一个天真、健康的姑娘折磨至死。在整个“治病”过程中,麻木的人群如同看客一般欣赏着巫医用开水给小团圆媳妇洗澡,没有一个人出来阻拦。王大姐做姑娘时长得“像一棵大葵花”,又高又大,人人夸奖她“将来是兴家立业的好手”,连有钱家的女人都说如果自己有这么大的儿子一定要娶她做儿媳。可一旦发现她没有通过明媒正娶就与穷磨倌冯歪嘴子好上了,而且还“非法”生下了孩子,赞美之词马上翻了个个,一时间,议论、咒骂,嘲笑声四起。就这样,这个毫无过错的女性成了众矢之的,随后东家在数九寒天将他们赶出了磨房。几年后,王大姐撇下冯歪嘴子和两个孩子离开了这冷漠的人世。造成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悲剧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与周围女人们的议论、咒骂、嘲笑有着直接的关系,她们无疑扮演了男性和传统势力的帮手,成为“无意识杀人团”的成员。这些在贫困与死亡线上挣扎的女性群体,她们被男性漠然地践踏着、毁灭着,与此同时她们又在木然地践踏、摧残,毁灭自己的同类。可见,女性的悲剧不光是男权所为,与女性的屈从、驯服、自甘为奴的“惰性”也有着直接的关系。萧红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她在对女性苦难命运的叙述和探索中,既对男权的罪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揭露,又对女性的“惰性”进行了自审和反思,显示了一个女性作家理性思索的光芒。
二、在苦难中抗争的女性
华莱士·马丁说:“在一部作品中。透过一切虚构的声音,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总的声音,一个隐含在一切声音之后的声音,它使读者想到一个作者——个隐含作者——的存在。”这表明叙事主体与文本之间有着紧密联系,作家在创作时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的生活经历,追求、理想,性格等主观因素融进作品,通过所创造的形象发出自己的声音。萧红骨子里有着一股叛逆精神,她一生都在奋力挣破传统文化的束缚,争取女性自由的空间,即使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也在所不惜。早年,为了反抗包办婚姻,她不顾被父亲开除族藉的威胁,叛离家庭,走上了流浪漂泊之途,即使过着冻饿街头的生活,也绝不回头,绝不屈服,后来,因忍受不了爱侣萧军的大男子主义和对爱情的背叛,她又不顾众人的不理解和劝阻,毅然与萧军分手。这叛逆的精神、反抗的性格因素,自然而然地融进萧红的叙事当中。使她在描述苦难中屈从的悲剧女性的同时,也塑造了一些富于抗争精神的叛逆女性,发出女性不甘卑弱、屈从、从属地位的声音。这声音也许不够响亮,甚至有些微弱,但它必定让挣扎于苦难和黑暗中的女性看到了一线光明,也给牢固的封建男权大厦带来不小的震动。
在这些叛逆、抗争的女性中,《生死场》中的王婆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王婆与挣扎在“生死场”上的其他女人的命运一样的悲苦,甚至比她们更悲、更苦,她结过三次婚,失去过三个儿女,但是喝足了生命苦酒的她,却从不像其他女人那样沉迷于苦难中,默默地舔舐伤口上的滴血,而是以抗争的姿态、斗争的精神向男权社会发出挑战。她摆脱了“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从一而终”、“贞洁妇道”等封建思想和道德观念对女人的束缚,不甘于女人卑弱、屈从、被动的从属地位。在婚姻生活中,她不屈服于男人的暴力,不愿做男人和家庭的奴隶,追求人格的平等和独立。她之所以离开第一个家庭、第一个丈夫,就是因为忍受不了丈夫对她的暴力。第二个丈夫死后,她又嫁给了赵三。赵三在《生死场》的诸多男人形象中是一个强悍的角色,但王婆并不屈服于他的强悍,始终与他保持着平等地位,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当得知当“红胡子”的儿子被官府杀害的消息后,她曾一度绝望,服毒自杀,顽强的生命力使她“死”而复生。重新活过来的她,抗争精神更加坚定,鼓励女儿要为哥哥报仇。
萧红还将王婆的抗争精神由家庭的私人领域引入社会的公共领域,以凸显其性格的坚强和斗争的坚定性。村里的男人组织“镰刀会”抗租,女人们都很害怕,只有她不但支持男人们的行为,而且还主动为他们提供武器,教赵三使用老洋炮。这一点让五尺高的男人们都感到羞愧。“镰刀会”失败以后,赵三妥协了,同地主讲“良心”,每天担着菜给东家送去,以示报恩。对赵三的这一举动。王婆十分瞧不起,与他生气、争吵,挖苦他:“我没见过这样的汉子,起初看来还像一块铁。后来越看越是一堆泥了!”日本鬼子对村中妇女奸杀掳掠,激起了她的民族仇恨。主动替李青山的抗日组织站岗、放哨。与《生死场》中的其他女性相比,王婆可以说是一个在苦难和抗争中觉醒的女性,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一颗不屈的灵魂。这一形象表明,在男权称霸的社会里,女性只有起来抗争才能获得做人的尊严。
萧红是位体验型、情感型的作家,她笔下无论何种女性形象,其实都灌注了她对女性命运的同情、思考和想象,她的思考对我们今天探讨女性命运、女性解放也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