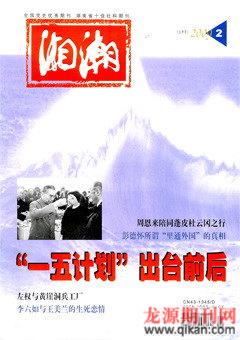李六如与王美兰的生死恋情
凌 辉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李六如和王美兰同甘苦,共患难,他们坚贞不渝的爱情足为一代风范。
毛泽民给他们做嫁
1933年秋,红枫似火,瑞金城郊一派丰收景象。
这天,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副行长兼财经专修学校校长李六如,风尘仆仆地走进一栋简陋的教室去讲课。他站在讲台前扫视了全班学员一眼,却见坐在前排的是一个十分秀气的姑娘。她个子不高,短发齐耳,穿一件蓝格子青布衫,一身山里姑娘的打扮,圆圆的脸蛋上镶嵌着一对深深的酒窝,双眼皮下两颗黑而透亮的眼珠,特别明亮,格外逗人喜爱。此时,她手里拿着一支铅笔,低垂着头,在抄课文。
讲课开始了,李六如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几个道劲的大字:财政金融学的基础知识。直到这时,那女学员才抬起头。
她叫王美兰,原名宁景英,参加革命后改名,1913年出生于江西省永丰县。父亲宁秀达是一位忠厚的贫苦农民,母亲罗莲秀是一位勤劳贤慧的农家妇女。她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哥哥。王美兰很小就给人家做童养媳。大革命时期,她加入少年先峰队,积极投入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1931年,她和丈夫一道双双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她在江西永丰前方医院任护士,后调至瑞金中央财政合作总社任营业员,于1g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党组织为了提高她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业务水平,送她到中央财经专修学校学习。她原来没进过学校门,目不识丁。但她有着坚强的毅力,夜以继日地刻苦学习,虚心向老师和同学请教。深夜,同学们都睡了,她还蹲在月光下用松树枝当笔,以沙盘做纸,演练数学习题。凭着她的勤奋、刻苦和不凡的接受能力,经过一段时间的补习,她居然渐渐地能够听写自如了。
专心讲课的李六如,开始并没有对王美兰有更多注意,只是在授完课的复习提问时,发现这个学员很腼腆,老是低着头,愁眉不展,好像有很重的心事。
这天下课后,李六如为帮助王美兰解开心中的疙瘩,在他的办公室找王美兰谈话。问过她的学习情况后,问到她家里人近来是否都好。问得王美兰忍不住眼泪扑簌簌掉了下来。原来,早些时候,部队来人告诉正在听课的她一个很不幸的消息她的丈夫在反“围剿”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她难过得肝肠寸断,心痛欲裂。她噙着泪,咬着牙,要求上前线去为亲人报仇。然而,她的要求没有被批准。她整天愁眉不展,圆圆的脸庞消瘦了许多,听起课来也就没精打采了。
“你不能消沉下去啊!”李六如劝慰道,“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人要化悲痛为力量。”并说,“上前线可以报仇,难道留在后方就不可以报仇吗?”
王美兰低着头,默默地听着。她是那样文静,那样淳朴,而又那样执著。她对亲人,对同志是那样深情,那样坚贞,这使李六如深为感动。他开始不由自主地喜欢上这个农村姑娘,便诙谐地对她说:“仗是有打的,只是你一个女同志,连枪都不会打,到时候说不定打不着敌人,反被敌人打着你了啊!是不是?”
一句话把王美兰问住了。是啊!虽然自己早已是红军了,但还没有摸过枪呢!
“校长,你教我打枪吧!”王美兰红着脸说。此刻,她一个心眼要报仇雪恨,迫切地需要学会打枪。
“搞军事我还不太里手,但打枪么,我倒可以教你!”李六如说着,让他的警卫员拿出枪来,手把手地教王美兰擦枪、装拆、瞄准。直到这时,王美兰才感觉到这个在课堂上非常严厉的校长,倒还很关心体贴人;直到这时,她才认真地端详校长李六如:个子高大,脸面清瘦,天庭宽阔,两鬓饱满,双眼炯炯有神,高鼻梁上架一副金丝眼镜,穿一身青色中山装。
这以后,除了上课之外,他们又接触了好几次。王美兰失眠了,李六如的影子老在她的脑子里盘旋着。她朦朦胧胧地感到已爱上了他。她也确信,他对她有着好感。她打听到,他19岁即参加辛亥革命,以后留学日本,是由毛泽东介绍入党的我党早期党员,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王美兰想,我一个穷山沟里的童养媳,能与他般配么?“这不可能!”她在心里说。
然而,没过多久,当专修班结业时,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和会计曹菊如亲自找她来了,毛泽民亲切地询问了她的家庭情况和参加革命后的经历。寒暄过后,毛泽民直截了当地对她说:“李六如同志与原配夫人已经失去联系六七年了,早已脱离了夫妻关系,一直过着单身汉的生活,他很需要一个革命伴侣。经过学校老师介绍,你和他也认识很久了,你是他的意中人。他爱你勤劳、忠厚、朴实、情笃。他的情况你可能都知道了。他是我们党内一位资深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非常忠诚,德才兼备,很受大家尊重,连我老兄润之也特别器重他。10多年前在长沙时,他俩就是朋友,他对六如同志的婚事也很关心。只是六如的年龄比你大些,不知道你是否同意,特让我们来征求你的意见。”
王美兰听了,疑虑全消了。她红着脸,点了点头,说:“没意见。”
那时候,时兴组织出面介绍。有毛泽民这样信得过的领导和曹菊如会计做媒,李六如和王美兰的婚事很快就成了。
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在造纸厂一间用杉皮盖的小房里,一张由两条木凳搁着一块门板搭成的“床”,“床”上铺着的厚厚的稻草和打了补丁的毯子,一件褪了色的蓝印花被面裹着的盖了多年的单薄棉絮,一床被烟熏黑的夏布帐,加上两把木椅,这就是他们的新房。唯一有点新房气氛的是床上摆着一对绣着大红“喜”字的枕头,床头瓦钵里插着一束盛开的菊花。
新婚的第二天清晨,李六如夫妇还没有来得及共进早餐,李六如就接到紧急会议通知,于是,他告别新婚的妻子,骑上马一挥鞭,消失在王美兰的视线之外……
铁窗共患难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李六如留在江西做党的地下工作。
1936年初夏的一天,李六如从街上回到家,随即把房门关上,极其严肃地就着王美兰的耳边说:“现在风声又很紧,要有思想准备,万一被捕,绝不能背叛革命、背叛党。”停了一下,他侧耳听听外面的动静,又告诉王美兰听到讲有人自首了,并说“为了应付万一,如果有人问你的身世,你就讲原先的婆家是开小饭铺的,丈夫跑船,不幸于前年翻船淹死,婆婆便经常骂你是‘克夫星托世,要把你卖掉。李老板正要续弦,花了几十元大洋买了你。”直至王美兰点头表示记住了,他才又上街去办事。没过几天,国民党驻吉安的五十一师就出动了大批军警,以“重大罪犯”将李六如五花大绑,单独关押,严密看守。
就在李六如被捕的同一天,一群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朝李六如住地奔来。王美兰一看来势不对,立即转移到了镇外。这里有一条小路直通山上,是李六如和王美兰早就探寻好了的,以备万一发生紧急情况。王美兰沿着这条小路上山,找到住在山里的邻居老人的儿子,说李老板恐怕被抓走了,为不连累街坊,她想在山上避
一避。
“要得。”邻居老人的儿子很重情义,真诚地答应了,叫妻子给王美兰开了一个临时铺,将她安顿在内间偏房里。
王美兰忧心如焚,坐立不安,整天整晚担心着李六如的安危。她托人下山去打听消息。然而,敌人封锁得很严密,四处查找也没有李六如的下落。王美兰更加焦急,便连夜下山,去找原来认识的李正浩医生探听情况。
王美兰一进李正浩家的门,只见屋里乱七八糟,破玻璃瓶子撒了一地,天花板上也被捅了几个窟窿。李正浩见到王美兰,急切地告诉她:李老板关在五十一师牢房里,已经用过刑,人还活着。那天军警找不到王美兰,知道她家和李正浩家有来往,就到他们家里来搜查,搜了个底朝天。因为连累了李正浩一家,王美兰感到极其不安。李正浩倒反过来安慰她,夫妻两人都热情地挽留她住下。王美兰怕再连累他们,又连夜赶回山里。
为了打听李六如的案情,王美兰想到曾与他们做邻居的一个妓女,妓女那里常有国民党军官去鬼混。她出身贫苦,人长得漂亮,性格豪爽,颇重义气。王美兰悄悄找到她,请她帮忙。她满口答应。没过两天,那妓女告诉王美兰说:“一个当官的讲,李老板的案子又是一个‘共匪案,打得昏过去了,但一时还死不了人。”
这时候,王美兰虽然住在山里,但她仍变着法儿打听党的地下组织。在城里找不到地下党,她想在山里找。找到了党,李六如就有救了。她扮成一个叫卖小百货的小贩,提着一个竹篮子,里面盛了一些袜子、肥皂等零星物品,在山里一家一户地转悠,找人攀谈着,探听地下组织的消息。但跑了几天,脚打起了泡,鞋也磨破了,却没有一点结果。
找不到党组织,营救无望。王美兰决心去探监,哪怕是龙潭虎穴,她也要去间一遭。即使死,也要和李六如死在一块。于是她又下山了。
这时,风声已没前些时那么紧了。王美兰下山后先回到家里。当时实行“十户联防”、“五户联坐”,谁要窝藏不报,就要受到株连。二房东见王美兰夫妇平日对他们好,主动出来招呼大家,说李老板是好人,遭了冤枉,李老板娘子很老实,不会连累大家的。还要各家管好自己的小孩,不要到外面去乱说。就这样,王美兰仍在原地住下。
李六如在敌人的监狱里,始终坚强不屈。敌人首先用“软”的一套,诱惑他。主审官很客气地将捆在他身上的麻绳解下,请他坐下喝茶、抽香烟,完全不采用审问形式,只是随便“聊聊”,问他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共产党。李六如平静地回答说:“我叫李训生,是个生意人,钱被抢了,不得已到报馆来谋生。”
主审官假惺惺地微笑道:“不对吧?”边说边递过一张贴有李六如照片的通缉令给他看,要他招供并登报脱党。主审官担保他的生命安全,并许他一官半职。
李六如态度坚决,严词拒绝。
“打!”敌主审官手一挥,几个凶恶的打手蜂拥而上,一阵乱棍,打得李六如皮开肉绽,昏倒在地。
几天后,敌人将李六如加镣上铐,寄押在吉安县城的死刑牢里,只候回文一到就立即执行枪决。
王美兰闻讯后肝肠寸断,悲痛欲绝。一连数日,她四处奔波,请求准许她见李六如一面,却遭拒绝。一脸横肉的典狱长硬邦邦地说:“你就等着收尸吧!”
王美兰忍无可忍,愤怒地大骂道:“你们枉杀好人,自己也不得好死!”
……
狱中的李六如,临死不慌。他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利用当局的法律条款和他在辛亥革命及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建立的老关系,力求改判。当时他“只希望判处无期徒刑,以待机会而已”。这时,王美兰得到一位好心医师的帮助,趁那典狱长不在时,让她进去探监。夫妻俩没有抱头痛哭,丈夫对噙着泪水的妻子说“别哭,哭也没用。你去设法给我弄点纸笔墨来,我要上诉!”
王美兰擦掉眼泪,安慰丈夫说:“不要挂念家里,你自己要宽心些,总有出狱的一天。”
还是通过那位医师,李六如得到了王美兰送来的纸笔墨和一些食物。因上了铁镣手铐,自己无法书写,一位好心的牢友主动为他代笔,由他口述,向南京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和江西省省长兼保安司令熊式辉等辩诉,说明自己并非“要犯”,根据条律,亦无死罪。同时将这一底稿分寄已断绝关系10多年之老友、南京司法院副院长覃振,请求营救,以免死刑,但并未请求保释。信是1936年11月18日寄出的。覃振收到信后,从中斡旋与几次力保,并让南京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书记厅回了信(当时覃振兼任该委员会委员长),说明覃振已给熊式辉写信,正在设法营救。
这时,监狱换了一名新典狱长。王美兰持李六如的老友、国民政府参军处章裕昆的信去找那新来的典狱长,被允许每天可以去送一顿饭。王美兰将仅有的一点家什也卖了,还每天清早给人洗衣,然后去做一点小生意,挣几个钱买点食物,送到监狱里给李六如吃。她一天天瘦下来了,李六如见状潸然泪下,说:“你不用天天给我送饭了,再这样下去,会把你弄垮的。”
王美兰没有生活来源,自己受苦不打紧,愁的是没有什么东西给李六如吃,而且每次送饭总要遭旁人的白眼,受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歧视和欺侮。这样的日子何时是尽头?她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和煎熬,但她一天也没停止过给李六如送饭,而且总是想着法子,给他做点能下饭的菜。冬天,怕饭菜冷了,她便带个小火炉,到监狱的巷道里热一热。
一天,一位邻居把王美兰拉到内房里,开门见山地说,她打听过了,李老板这案子即使有朋友帮忙不被处死,也会判无期徒刑,你还很年轻,只有20多岁,怎能老守活寡呢?还是改嫁吧。并说已给王美兰物色了一个好男人,人正派,家庭很富裕,是一位开店做大生意的老板,只要她愿意,便给她做媒去。
王美兰谢绝了那位邻居的好意,坚决地说:“不!李老板就是判了无期徒刑,我也守他一辈子。”
她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李六如关在狱中两年多,王美兰一直守护着他,给他送衣物,给他搓洗血衣,千方百计营救他。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逐渐形成。1937年3月,李六如被释放,得以出狱。出狱后,他提起笔激动地在王美兰的照片背面写道:
吾妻美兰,赣人也,性忠实而重情义,曾与吾共生死患难于枪林弹雨之中,跋山涉水,艰苦倍尝。在吉安遭难时,尤其辅助之力不少。吾以是爱之重之。古人云: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吾与美兰患难之交也,糟糠云乎哉,故数年未尝离左右。
患难之交,刻骨铭心。李六如始终如一,全身心地爱着王美兰。
“天下美女多得很,我就只等她!”
1939年秋,李六如到延安后,担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王美兰得了阿米巴痢疾,病情严重。当时的延安缺医少药,生活又非常艰苦。李六如
把自己仅有的一点津贴买来中草药,守护在身旁,给妻子熬药、喂汤、洗衣服,其体贴之入微,使王美兰深为感动。李六如设法兑来一些细粮给她滋补身体,自己却吃黑黑的窝窝头。眼瞅着丈夫的身子天天消瘦下去,心里很过意不去,王美兰便说:“你应多照顾自己,不应为我这样费心。”
李六如回答说:“难道就只能让你服侍我,我就不能为你尽点心吗?!”
“你要干大事呀!”王美兰说,“自己身子骨要紧!”
“你不是同样在干革命事业吗?!”李六如说,“干革命没有大小事之分。你现在病了,就应多照顾你。何况在吉安落难时,要没有你,恐怕我早就……”说着眼眶就湿润了。经过李六如一再劝说,王美兰终于恋恋不舍地离开延安,离开了丈夫,到苏联治病。
王美兰到苏联治病后,因关山阻隔,战火纷飞,国内国外通讯断绝。她想回国也无法回去,一年又一年,一直呆了3年。李六如非常挂念她,可也没法和她取得联系,心里异常焦急。王美兰虽然苦苦思念着自己的祖国和亲人,但没翅难飞,身不由己,只好在异国苦撑苦捱。
其间,大批知识女性进入延安,她们不但年轻漂亮,而且思想新潮,追求进步,文化水平高,能说会道。延安的一些高中级干部和妙龄知识女性谈情说爱,很快结了婚。
作为我党少数的几个老前辈之一,辛亥武昌首义、北伐战争时期的将军、留目的高级知识分子、我党的高级干部,李六如以其曲折传奇的资历和超人的才干,使党内外人士尤其是知识女性非常敬佩与爱慕。李六如与王美兰已失去联系多年,孤身一人,过着寂寞的生活,另找一位伴侣也是允许的。而且,身边也不乏追求他的漂亮知识女性。于是有人劝李六如:“你这是何苦呢?天涯何处无芳草,眼前就有美女追求你哩,再娶一个吧!”
李六如断然回答说:“天下美女多得很,我就只等她!”
“这要等到何年何月啊?”
当时有一位从国统区来到延安的女大学生,身材苗条,红通通的圆脸上闪着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黑黑的眉毛,高高的鼻梁,文静而又端庄。经过短期培训后,分配在财经部门工作。一天,听了财经部副部长李六如的报告后,为他那有理有据深入浅出的精辟见解所深深折服。后来经过与李六如工作上的一段交往,更为他对下属的关怀体贴和一丝不苟的作风所打动。当得知他的人生经历和现状时,由敬慕到滋生了一股强烈的爱恋之情。她觉得像李六如这样经历丰富、学识渊博、温雅亲切的知识分子,才是值得她托付终身的意中人。虽然他比她年龄大一些,但爱是没有年龄界限的。经过一段观察思考之后,她鼓足勇气,给李六如写了一封“思想汇报信”,字里行间洋溢着如海般的深情。
如豆的油灯下,李六如仔细阅读了这封信,脑海里久久不能平静。他早就感觉到了那位女大学生的深情。然而,他不能爱她。为什么呢?因为在他脑海里根深蒂固的,是他曾给王美兰许下的诺言。王美兰在他的心中所占的位置,是任何人所不能替代的。在没有得到她离开人世的确信之前,他是决不会另找新人的。于是,他毅然挥笔婉言谢绝了那位女青年的好意。为不使她难堪,他假说近已获悉妻子信息,不日将回国,到时请她前来作客。
说来也很凑巧。1942年春,王美兰终于回到了延安,回到了李六如身边。“久别胜新婚”,两人之间的欣喜之情无以言表。王美兰回延安后,党让她到中央党校学习,参加整风审干。然后继续担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处干事。
贴心呵护熬过艰难岁月
1945年8月下旬,李六如偕王美兰由延安奔赴热河,一路上,历经艰险,终于到达承德,李六如任中共热河省委常委兼热河省政府秘书长。
当时,作为热河省省会的承德,刚刚从敌伪手中接收过来,经济很困难,物质条件很差。党政军机关的干部和承德的老百姓,生活都很苦。承德地处塞外,地势又高,冬季一到,冰天雪地,气温可降至零下30多度。可是,这样冷的天气却没有棉衣穿,没有煤烧,就连组织上照顾高级干部的那几个鸡蛋,有时都没有火煮。这时的李六如,已经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他日夜操劳,一下子病倒了。幸亏有王美兰的精心照料,经过慢慢调养,病情才渐渐好转,勉强支撑下来。
1946年6月,蒋介石背信弃义,发动全面内战,热河的形势也日趋紧张。不久,国民党军队进犯热河。按照中央的指示,李六如和一些同志一起,撤到承德北面约100公里的比较安全的围场待命。没过多久,国民党军队追来,他们又从围场撤出,路上还遇到了土匪的袭击,突围后才到了内蒙吉林西。按照上级的安排,他们在林西暂住下来,苦熬了一段时间。
从到达至撤离,李六如与王美兰在热河工作生活了不足一年的时间。在他俩的一生中,这却是一段十分难忘的岁月。李六如后来回忆说:要不是美兰细心照料他,呵护他,他体弱多病的身子真难熬过来。
“文化大革命”中又一次生死与共
1970年,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备战”为借口,强迫已经83岁高龄的李六如和夫人王美兰,从北京去桂林,还特别“规定”:不许带女儿一起走,也不许与女儿与亲友通信,说这是“为了老同志的安全”。
李六如被遣送到桂林。他们被安排在一幢房子里,并被告知:不许会客访友,不许离开圈定的活动范围,没有任何文化生活。他们成了这场大劫难的沦落人,他们过的是被软禁的生活。每天他们能见到的人,除了几个“监护”他们的“造反派”,就只有一名姓贝的医生了。
桂林多雨,终年潮湿,天总是阴沉沉、灰蒙蒙的,晴朗的天气很少。李六如夫妇整天被关在屋子里,面对四壁,心情十分郁闷。每当心头的闷气无法发泄时,李六如便站在窗前,仰天长叹,声音高亢而又凄凉,此刻,王美兰知道丈夫的烦闷又达到了极点,禁不住泪水满面。
一天,李六如从“监护”他的“造反派”那里听说,邓子恢也被遣送来到桂林。得知此事,他决定前去看望。几经“请示”得到许可后,他疾步来到邓子恢的“家”。那是一处单独的院落,也有人“监护”。李六如突然登门,让邓子恢喜出望外。一见面,两位老人异常亲热,眼含热泪,相互使劲摇动对方的肩膀,这是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老战友,在特别的年代、特别的场合里的一次特别的会面。他们都心事重重,有太多的话要说,一时又不知从何处说起。他们只有连连叮嘱对方要想开些,要多多保重,迎接重见天日的那一天。自从到桂林以后,这是王美兰第一次看到丈夫这么高兴,她的心情也随之好了许多。
贝医生40多岁,为人和善,对李六如夫妇敬重有加。对于给李六如检查身体、开药治病这些事更是认真负责,从不马虎,表现出很高的医德。他理解李六如的处境和他的心情,所以,他总是借看病的机会透露一些外面的消息,说一些宽慰的话。一次,李六如问贝医生:“你看我们什么时
候才能回北京?”贝医生宽慰说“您别着急,不会太久的,等‘文化大革命胜利了,就可以回去了。”
李六如、王美兰夫妇曾经从育婴院抱养了一个女孩,取名海龙,十几年一直在他们身边。这次他们被遣送到桂林,上边不允许小海龙一起来,无依无靠的小海龙就只身到西藏闯荡去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在一次车祸中,年仅十几岁的小海龙,竟惨死在雪域高原。对于身处逆境的李六如夫妇,这无疑是雪上加霜,使他们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
在那段度日如年的日子里,王美兰一步不离地日夜守护在李六如的身边,给他关爱,给他温暖。在当时的条件下,补品、营养品是不能奢求的,王美兰精神上的抚慰,饮食上的照料,使李六如的心情逐渐平静了下来,体力也得到了恢复。看着由于过于操劳疲惫不堪的王美兰,李六如心里是说不尽的感激。凡是了解他们过去的人都说,李六如和王美兰是一对患难与共的恩爱夫妻,他俩的爱情刻骨铭心,忠贞不渝,被许多知情的人称为“一代风范”。
从桂林回到北京后不久,李六如又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但是,他得的不是什么很难医治的疑难杂症,而是由于心情极端不好导致的身体极度虚弱,只要好好调养,就可慢慢康复。
可是,在江青、康生等人的迫害下,李六如的病得不到调养,也得不到及时治疗,身体不仅没有康复,病情反而迅速恶化。后来,李六如脚肿得厉害,连走路都困难了,王美兰就送他去住医院。须知,头上顶着“叛徒”、“反党分子”帽子的人,是不能住进条件较好的单间病房的,只能住在十几个人的大病房里。所谓“治疗”,也只是每日做些常规检查,服些维生素之类的药物。加上人来人往,嘈杂不堪,大病房里根本无法休息。无奈,王美兰又只好把他接回家里。
1973年4月,李六如的病情更加严重了。王美兰想把他送到医院去抢救,但是要不到车,只好到街坊那里借来一辆三轮车,艰难地把丈夫拉到医院。
李六如病危住院的消息,冲破江青一伙的层层封锁,很快传到了正在接受“劳动改造”的新凤霞的耳边。新凤霞冒着私通“叛徒”、“反党分子”的风险,日夜兼程,来到北京想见李六如最后一面。可惜呀!她来迟了一步,时年86岁的李六如,已于4月10日上午8时含恨离世。王美兰紧紧拉着新凤霞的双手,向她哭诉当时的情景:
“就在他快要咽气的时候,拉住我的手,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喃喃地呼唤着:‘毛主席、周总理、老同志……一位好心的医生见后,轻声对我说:‘他想念主席和总理呢,你给他找张照片看看吧。可是,待我找来主席和总理的照片,他却不省人事了。过了好一会儿,他又睁开眼睛,吃力地四处张望,好像是在寻找什么,看见床边只有我一个人守着他的时候,他凄苦地流下两行热泪,然后慢慢地合上了双眼。”
在王美兰不断申诉下,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1980年7月2日,党中央为李六如举行了追悼会,平反昭雪。王美兰异常兴奋,并抓紧整理李六如的遗稿。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第三卷。李六如在天有灵,也当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