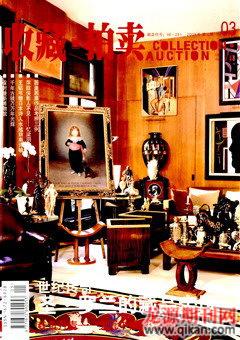萍踪侠影人不见
苏 晨
牛年春节刚过,年初二[1月27日]大拜年的日子,突然获悉武侠小说大师梁羽生悉尼病故的消息。想2008年6月3日《参考消息》第14版还以大半版的篇幅报道他《“看风流慷慨,谈笑过残年”》。这相去才半年多,他就驾鹤西去了,虽然享年85岁,已属高寿。
2008年《参考消息》驻堪培拉记者江亚萍去采访梁羽生的时候,他和夫人一起住在澳大利亚悉尼伍德区的陈秉达养老院;因为一年前右脑中风,左腿麻痹,他已经自己走动不得,要由夫人用轮椅推着。当时两相交谈,梁羽生谈笑风生,谈到香港报纸此前报道糖尿病、心脏病、癌症“三大杀手追杀梁羽生”,如今加上中风已经是“四大杀手追杀梁羽生”,可是他自诩自己“武功高强”,不在乎。然而生、老、病、死,人生的自然规律,谁也绕不过去。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1924年3月22日出生在广西蒙山,广州岭南大学毕业,曾在香港《大公报》任副刊编辑。是由他率先开创武侠小说新风气。自1954年至1984年的30年间,陆续创作了《萍踪侠影录》等35部、160册、约1000万字的新派武侠小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后他虽不再创作武侠小说,可仍笔耕不缀继续创作其他作品。1987年他离开香港到澳大利亚悉尼定居与子女团聚,晚年在“三大杀手”、“四大杀手”的“追杀”中,自诩“武功高强”的他,还是创作了《名联观止》上、下册和散文集《笔花六照》。在最后告别我们这个美丽的星球之前,他编了一本《文心侠骨录》,结集他全部武侠小说中的诗、词。关于梁羽生这种人,我看大抵适用于著名的日本哲人铃木大拙的说法:“人,不一定伟大,只要成为一个坦诚可靠的人就可以了。一生默默地工作,到了要说‘永别的时候,即自然消失,这就是我说的伟人……”
我和梁羽生相交平平,业务往来而已,无他。或者尚可一提的是,他的武侠小说和散文集的在中国内地出版,倒是由花城出版社率先来做:当然,我不过是因为职务关系要承担全责的签发者。须知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内地出版社出版海外作者的武侠小说,还是一宗“危险”的事。花城出版社捏着一把冷汗出版了他的《萍踪侠影》(去了原书名的“录”字)和《白发魔女》(也去了原书名的“录”字)……等几种新武侠小说,《萍踪侠影》出版之先,我写信去和他联系,在信中老老实实告诉他,花城出版社想出版《萍踪侠影》等书,一来是为了要把新派武侠小说这个内地缺失的当代文学之一枝,介绍给内地读者鉴赏,这是主要的:二来是实不相瞒,花城出版社新成立,资金基础薄弱,也有想出版一些畅销书以增加经济收入,有便尝试进一步改革整个儿出版业务的意思。我不是骗他,这也是真情,我既奉派负责花城出版社业务,还以为随着国家的深入改革开放,出版社的出版物也可能很快不再“定死”由新华书店包销,出版社也可以按新的经营方式开设别具特色的书店,开设为读书人设计、订制特定图书收藏家具的木工厂(一次老作家秦牧告诉我:他在珠江三角洲走一圈,种种家用电器让人眼花缭乱,就是没见到有一个像样的书柜),我傻大胆地痴想试行出版社的一系列综合发展,当然没有一定的启动资金不行。无独有偶,我的这种痴想,还由著名记者黄淑儒在她的报纸上发了头版头条。梁羽生收到我的信,复信表示:“没有任何意见”,“是求之不得的事”;有让我“慎重考虑,且莫因而生祸”;甚至提到“如有必要,也可不必给作者支付稿酬”。他大概也知道,那时候的所谓“清污”[即文艺界、出版界的所谓“清除资产阶级影响”],仍然很是可怕。正是因为我也知道率先出版梁羽生的著作可能因而惹祸,便分别作了专题上报备案,把梁羽生的复信也作为附件上报,没有保留。
不谈这些。再谈梁羽生在中国内地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笔不花杂记》,那是我去信向他特约的。因为此前我注意到,他不但武侠小说写得好,散文也写得好,有盼望他多写些散文的意思。还因为花城出版社出版他的武侠小说发行量很大,使出版社增加不小的经济收入,我也想有所报答的表示。于是写信给他,请他把一些散文著作编一个集子,由花城出版社来出版。至于这是不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我还不清楚。
1985年11月1日,他到广州参加岭南大学的“同学曰”,顺便把他编好的《笔不花杂记》书稿带到广州,托人送给我,附有一封信,这信还在,内容是:
苏晨兄:
遵嘱将旧作文史小品三十余篇编成一集,请兄裁夺是否适合在国内出版。
弟此次来穗参加同学日,来去匆匆,只在东方宾馆住两晚,未能前往拜候,歉甚,歉甚。诸多有劳,容后面谢。
弟羽生
1/11
23年前的事,我已经记不清《笔不花杂记》一书为什么到1986年6月才印出来。现在看来太慢,可是那时候中国大陆一般图书的印刷还处在“火与铅”的时代,按当时的规定,一本书要社领导签发排、签付印、签发行“三签”,又要等为期3个月的征订才能签付印,所以印刷、出版周期都比较长,半年时间才印出来,在当时怕是还不能说慢的。《笔不花杂记》,132开本,12万字,6.5印张,2插页,共212页,发行1.5万册,售价1.3元1册。这也是出版社赚钱的书。有没有再版,我也记不得。
我在花城出版社主持业务的时间不长,却是一再得到相关系统高高上头的“整”来“整”去(这是当时文艺界、出版界人们知道的事,无须讳言)。照理说本该是一提起那段日子,我就该“灰头灰脸”才是。可能是因为我“觉悟”低,始终装也装不出来。原因?主要的,说来费笔墨。这也可能与因为得到主事的机会,和社里同仁一起抓紧时间做了若干开创性的出版工作,有多多少少的关系?不知道率先在中国内地出版梁羽生的新派武侠小说和散文集,是不是也可以算作一项小小小小的率先?埃利斯说:“我们称之为进步的,只不过是以某种麻烦代替另一种麻烦的事。”德富芦花说:“新事物常常是反叛的。”我曾以之自勉,所以挨“整”本属“正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