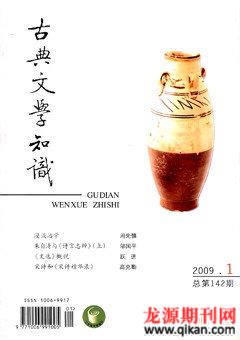新时期《绿野仙踪》研究综述
赵维平
一、关于作者和成书
《绿野仙踪》作者为李百川,因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百回手抄本前有“李百川自序”,并且所有版本都有的“陶家鹤序”中有“予于甲申岁二月,得见吾友李百川《绿野仙踪》一百回”之语,而向无异议。侯忠义《论抄本(绿野仙踪)及其作者》一文,推断作者生卒年道:“乾隆十八年写作此书时,他自言已‘年过三十,假定作者此时为三十四五岁,那么作家当生于康熙五十八年(公元一七一九年)左右,而卒于写作时间最晚的侯定超序完成之时,当在乾隆辛卯(即三十六年,公元一七七一年)之后。”上世纪90年代在美国发现新的百回手抄本后,翟建波《(绿野仙踪)作者、版本新证》指出俄亥俄大学馆藏百回本上李百川的作者权,除一见陶序外,尚二见于陶序补记,三见于第六回夹批,李百川的作者权成为铁证,
李百川籍贯,自吴晗1931年根据为小说作序的陶家鹤是绍兴人,侯定超是洞庭人,认为百川自序“宜删”的周竹蹊是南京人,李百川自序中“癸酉携家存旧物远货扬州”一语,提出李百川“江南人”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作为学术界主流看法。上世纪80年代末陈新《(绿野仙踪)作者、版本及其它》指出吴晗的“江南说”证据不充分,提出“李百川为北方人,小说开始即写山西事,似为山西人”的新见解。继而苏兴、苏铁戈《(绿野仙踪)丛谈》标榜郑振铎提出的“山东人”说,除了从作品语言特色例证,还从叙述语气和人物语气、温如玉活动在山东省太安州、作品对苏杭的描写及感叹带有北方人的气味三个角度分析作品的山东人创作印迹,得出“作者是北方人,可能更合适一些。……是山东人(当然到过北京)也是可能的”的结论。翟建波进而力证李百川是山东人,实证色彩比较浓厚。首先,作者自序中说曾被时任直隶太原府辽州牧的堂弟迎请到辽州,而“羞归故里”,山西显然不是作者故乡;其次,作者自序中有“远货扬州”,夹批中有“余在江南”、“余在江南扬州居停七载”的话,可知作者也不是南方人;再次,作者对北方方言尤其是对河南、山东一带方言非常熟悉,他很可能是河南或山东人。但自序中有“壬午抵豫”一语,非返乡口吻,所以他只能是山东人。作者还列举内证,根据“全书约三分之一的故事发生在山东境内”,作品中山东籍人物(温如玉、金钟儿、苗秃子、萧麻子)性格刻画最鲜明,有关故事情节最精彩,以及温如玉镇江被骗带有作者扬州被骗的“影子和教训”,得出“作者为山东人较为实际”的结论。
《绿野仙踪》的成书研究,人们主要根据作者自序。侯忠义论述成书过程道:“据自序称,清乾隆癸酉(即十八年),他草创《绿野仙踪》三十回于扬州旅邸,至乾隆壬午(即二十七年),在河南完稿,历时九年,共计一百回,”可谓清楚明白。李百川创作思想,经历了一心写鬼、兼重人情、偏重民生三个阶段。李百川“家居时有‘最爱谈鬼的嗜好,继之更有‘广觅稗官野史的兴趣,但创作《绿野仙踪》的最根本原因,还是根源于他穷愁潦倒、浪迹他乡陌路的艰辛生活经历”。林虹《论(绿野仙踪)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指出:“在他酝酿创作及创作之初,他‘最爱谈鬼而想创作‘百鬼记,因此,此时他心目中的‘奇无疑是‘牛鬼蛇神之奇,可当他历尽沧桑,四海漂荡,经历了形形色色的人情物性之后,脑海里更活跃的必然是那些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若男若妇。这使得小说真正出‘奇的恰恰是在写‘日常起居的人情部分。”可谓的论。
二、关于版本研究
《绿野仙踪》传世的版本分百回抄本与八十回印本两个系统。抄本系统主要三家,北京大学图书馆百回抄本先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据之影印出版和整理校点出版,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藏百回抄本由中华书局“古本小说丛刊”第四十一集收录,印地安那图书馆藏百回抄本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所影印。八十回印本则分三类:刻印本有乾隆刊巾箱本、道光十年刻中型本、道光十五年乙未集谊堂校刊本、道光二十年武昌聚英堂刊小本、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刊本:石印本有光绪三十年上海书局本和民国十三年上海大成书局本;铅印本则有大达书局本。
《绿野仙踪》版本研究新成就,主要集中在:
(一)手抄本和刻印本关系。侯忠义指出“抄本在前,刻本在后;抄本是‘繁本,刻本是‘简本;抄本是‘原本,刻本是‘节本(刻本本身也有个繁简问题)”。这一意见为苏兴、苏铁戈所认同,但苏文对问题阐述较为细致:八十回刻印本对百回手抄本的删改,除相同情节中个别词语及词句改删外,情节改删还有三种情况:一是单纯的删减,靠上下文自然衔接,或稍加几字使上下文衔接起来,以至于减少内容,合并回目;二是删减的同时,在删削处有增改;三是情节有调整。翟建波《(绿野仙踪)版本、作者再证》根据“北大本删节了的文字,刻本有”和“刻本与俄本一样,都没有作者自序,而北大本却是有作者自序”的现象,断定后世流传的八十回刻本是由俄本做底本,“另有其人”删改而成,他在删改时“只能是沿袭旧文,即俄本之文”。
(二)《绿野仙踪》的祖本。郑其兴《(绿野仙踪)>“印图本”价值浅论》比勘了北大图书馆所藏百回手抄本和美国印地安那图书馆所藏百回手抄本,根据“印图本”上多出的陶序补记及其保留了许多“北大本”所缺漏的文字、保留了祖本情节推进的逻辑性、保留了祖本情节叙述的丰富性、保留了祖本情节刻画的细致入微处等现象,指出“‘印图本较‘北大本更完整地保留了《绿野仙踪》祖本的原貌”,它“有力地证明了《绿野仙踪》另有一个祖本的存在”。作者认为:陶家鹤所见并为之作序的本子可能是作者李百川的手稿本,或者是李百川自己把手稿本誊抄又加上傍注、评语的定本;“北大本”与“印图本”便是以这个本子作为祖本,由不同抄手抄录于不同时间的抄本;八十回刻本也是以这个本子作为删改的原本,而非以“北大本”或“印图本作为删改的原本。
(三)手抄本之间的比较研究。翟建波《(绿野仙踪)版本、作者新证》指出美国儉亥俄大学图书馆藏百回手抄本与印地安那图书馆藏百回手抄本“二书”一字不差,抄写一模一样,因而知二书实为一书,其中当有一书为另一书的影印或摹印本”,进而比勘俄亥俄本与北大本,根据二本对应处俄本语意通顺合理、删改后的北大本正文与保留下的夹批相矛盾、俄本批注语被北大本误入正文三大发现,认定“北大本实为俄本的一个删改本。俄本在前,北大本在后;俄本是原本,北大本是节本;俄本是繁本,北大本是简本。北大本与俄本相比,大约删去六七万字,为全书的十分之一左右”,根据比勘第一回就发现二本有一百多处异文,以及北大本“不仅正文有删有改,而且批注也有删有改,还有增加。而多数的删改,并不影响本书的价值,对读者了解作者的思想或者说读者了解冷于冰的思想意识并无多大妨碍”的事实,推知“北大本为作者自删自改的另一种传本”。因为“若是抄写者致误,断不至于如此之多”,这是很有见地的。
三、关于构思、结构和主题
早在上世纪初,鲁迅就认同黄人关于《绿野仙踪》“盖神怪而点
缀以历史者也”的论断。文革结束后,再版的北大中文系《中国小说史》指出《绿野仙踪》“通过明代嘉靖年间冷于冰求仙得道的故事,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看法和政治见解”。其后林虹认定《绿野仙踪》由神魔、讲史、人情三个方面内容有机构成,而“选取冷于冰求仙得道这个神魔内容作为全书线索,将讲史和人情内容串连起来”,并指出作品神魔、讲史、人情三大内容又各取前人之长,神魔板块取《西游记》以中心人物贯穿始终,而以冷于冰为线索;讲史板块取《水浒传》围绕聚义、忠义大业的人物传递法,呈现出一人引出另一人、一事激发另一事的连锁反应结构;人情板块取《金瓶梅》家庭切入法,不受时地限制地展现多个家庭,对小说结构的分析相当精当。侯志义则一针见血地指出《绿野仙踪》“托明代嘉靖之名,实写清代乾隆之世,借冷于冰求仙得道故事,寄寓他的政治理想”的构思特点。
由于《绿野仙踪》既有神魔又有讲史和人情内容:所以对它主题的看法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究其本质无非两种意见。一种认为,社会和人生情节是《绿野仙踪》的主体,主人公以出世的方式行入世之事,表达了铲除人间不平的主题;另一种认为,神魔内容是《绿野仙踪》的重心,主人公不停地度人成仙,反映的是道家文化,表达了人世是苦海、出世方逍遥的思想。
林虹、侯忠义、董建华持第一种意见。林虹认为,神魔内容不过是讲史和人情内容的线索,讲史和人情才是作品主体,因而《绿野仙踪》的主题是入世的,“表现在贯串全书的一种人生哲学,即作品第二回首次出现以后又屡次提及的四个字‘窥时顺势,大到朝廷政治斗争,小到闺房家事之争,这种观点都一以贯之,在作者看来,违背了这条原则,在政治斗争中不仅会有杀身之祸而且事业无成,在家庭纠纷中也会被动失势甚至身死名灭”。侯忠义认为,作品中弃家访道、伏鬼降妖情节不足凭,入道后的主人公苍白无力、非常概念化,倒是冷于冰要点化的对象温如玉、连城璧等人物写得有血有肉,小说所写世俗生活和忠奸斗争让人趣味盎然。这说明“小说中某些人物和情节,完全来自现实生活,而在这些故事和人物身上,又寄托作者的感慨、牢骚和不满”。董建华《从(绿野仙踪)看作者李百川的心态》指出,《绿野仙踪》的主题是表现功成名就思想。首先,主人公冷于冰“求仙访道,与其说是消极退隐,不如说是曲线救世”,他利用道技仙术参加归德平叛,发起平凉放赈,成就他人功名;作者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愿望,通过作品中朱文炜、林岱的成功去表现,入世用意是十分明显的。其次,作品在宣扬道教文化的同时,也不时表达对道教学说的怀疑。“作者的理想天堂胜境就是人间的高官厚禄,富贵奢华”,而这恰好是他人生理想的翻版。再次,李百川生于末世而不敢发泄对末世的不满,就“借助作品,让自己在虚构的世界中自由自在地徜徉,寻求希冀与宽慰”。
李峻锷、徐润拓持第二种意见。李峻锷《道教文学作品(绿野仙踪)浅析》认为,《绿野仙踪》是宗教文学作品,“通过描绘社会生活,宣扬宗教思想”。他还从作品赖以产生的明代背景分析这种出世主题的根源,“在尖锐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交织之中,社会上很大一部人就幻想要脱离现实以超脱于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之外。宗教小说《绿野仙踪》中极力宣扬的摒弃富贵、割断尘缘、修道成仙的思想,就是这部分社会意识的反映”。徐润拓《(绿野仙踪)求仙主题中的死亡意识》认为,小说主人公冷于冰一生经历了两个重大转折,“一是由仕进到退隐,二是由现世到求仙”,第一个转折是对社会现实理想的幻灭,由奸臣当道的社会现实所造成;第二个转折是对生命长驻希望的幻灭,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只能将获救的希望寄托于神仙道术上,认定了小说的出世主题。
伍大福持论介于上述两种观点之间。其《试论(绿野仙踪)的非儒思想》认为作品写封建末世儒家文化的衰微,而张扬道家、侠义文化救世的理想。一方面,“时至明清,士人言顺行悖儒学的本旨已尽现儒学的衰微。《绿野仙踪》正是借小说中的形象对儒学这一根本价值观进行了现实的反思,让我们得窥儒学没落的迂腐和苍白”。证据是儒家思想核心是内“仁”外“礼”,但小说中叶体仁:周琏等人却为富不仁、为人非礼;儒家思想基础是“内圣外王”,但小说中的皇帝却荒淫昏庸、忠奸不分,权臣严嵩只知贪污受贿、党同伐异,致使士人“‘身不能修,‘家不能齐”;儒家政治理想是“立德、立功、立言”,而作品中的儒家君子离开仙道帮助就不能成一点功业,等等。
四、关于作品成败和文学地位
《绿野仙踪》神魔、讲史、人情三大板块,一般学者都认为人情部分写得最出色,其次是讲史部分,神魔部分最苍白,侯忠义认为:“就像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仙人冷于冰,是一个苍白无力、非常概念化的人物,倒是作者并非着意的连城璧、金不换等人物,却写得有血有肉、可真实感一样,我们肯定有较高认识价值的,是指书中所反映的现实内容。”林虹指出《绿野仙踪》真正出奇的恰恰是在写日常起居的人情部分。理由是人情部分以家庭为画面充分展示了明代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成功塑造了许多世俗人物群像。林虹还分析了《绿野仙踪》问世以来没有引起轰动效应的原因,间接指出了它的不足之处,第一,艺术表现极不均衡,小说最出色的是人情部分,而神魔部分却多所依傍,缺少创新。第二,作品中心人物冷于冰形象过于理想化以致远离人世、脱离现实,流于苍白浮泛;假如写一部贫士冷于冰的现实经历更能打动人心。第三,作品创作于所谓“乾隆盛世”,社会己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点。面对这个行将崩溃的时代,作者缺乏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反思,缺乏同时期《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中的强烈的反叛精神。
李国庆《绿野仙踪·前言》指出,作品在小说史的地位,是它“吸收了前人在各方面的成功经验,将历史、神魔和世情熔于一炉,为中国古典小说增添了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虽然对这一大胆的艺术尝试之得失见仁见智,却无法否认它为中国小说发展史留下了宝贵的研究个案”。董建华《试论(绿野仙踪)题材类型的多元化》揭示了类型多元化的必然性:“一是凭空捣虚的难,二是小说发展到清朝中叶,各种小说体制都已完备,并且都出现了难以企及的典范之作,为了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只好从题材角度加以翻新或者写前人尚未挖掘过的题材,或者将性质不同的题材融为一体,《绿野仙踪》属于后者。”都是中肯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