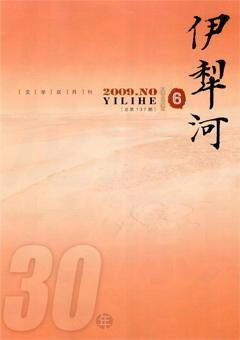日本和尚
陈 谦
陈谦,女,笔名啸尘,在广西南宁度过青少年时代。一九八九年春赴美留学深造。现居美国硅谷,曾长期供职于芯片设计业界。自由写作者。视写作为生活奢侈而本质之必需。主要作品为中篇小说《特蕾莎的流氓犯》、《覆水》、《残雪》、《何以言爱》等;长篇小说《爱在无爱的硅谷》;并有散文随笔散集《美国两面派》。
到达京都,是在中午。在前一个夜里,我和三个女伴海伦、佳佳及劲建,从北海道的钏路上了火车。京都是举世闻名的古都。而我们此行,还将人住京都名寺高台寺,这让我们期待不已。
我们每人的箱子都很大很沉,又都是急性子,一下车拖着行李就跑。有时不仅换车,还要换轨,我们连电梯也不曾想到过去寻,拖着沉重的箱子就下楼,边走边喘。换车的时间很短,根本来不及相互合作轮流来搬。而且在日本,男人们看到我们这些女人吭哧吭哧地,竟也不会有人来搭个手的。每到这时,真是让人怀念美国的绅士们。
这一夜不停地大小火车转换下来,就着晨色相互看着,都觉得彼此确实像是逃难的人了。天亮的时候,我们的车子终于钻出了漫长黑暗的海底隧道。望向窗外,可以见到海了。火车像在一个微缩的盆景地上穿行,铁路沿线是LEGO一样小巧的高房矮屋,密密麻麻连成风景。秀竹、绿木、海、船,在自然的色调中层层叠叠,跟北海道宁静开阔的自然相比,是全然不同的另一个日本。但因着洁净的拥挤,让人觉到人间烟火中的温暖。
列车在早晨停过青森、八户、再东京,一路去往我们这段旅程的终点——古城京都。一路都是西装笔挺的上班族,黑鸦鸦一片,蔚为壮观。在美国,特别是在美国西部,如今大部分的地方都已经不再要求着正装上班,所以看到沿途如此庄严肃穆的人们,实在新奇。
在东京前后的景致大致是现代的,很多高楼,很多广告,让人提不起劲儿来。直到近名古屋一带,地势开始平坦,古色古香的日本老房子开始出现,屋边的植物郁郁葱葱,小小的池塘闪着亮光,很有些田园风光意思,到底是要进古都了。
京都车站热闹非凡。拖着行李在人流中穿行,看到许多精巧可爱的小店,一色的桃红果绿鹅黄,却不能停留细看。
我们从车里一出来,在月台上就见到了前来相接的高台寺住持——寺前净因桑师父。那一刻,京都月台上的阳光竟是白的。净因桑四十出头的模样,穿着一身像是早年中国那种叫“阴丹士林”的蓝染粗布衣裳,背一布袋。他的衣裳很旧,抬手间,我看到肘下竟补着一块小补丁,他的脚下是一双半旧的拖鞋。
净因桑对中国很有感情。在日本,寺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产业,而寺庙的住持是法人代表,相当于企业公司里的CEO,是要为寺庙谋生存求发展的,所以净因桑因生意上的一些合作关系,不时会去上海,跟海伦有了联系,此番盛情招待我们在京都期间入住高台寺。美女海伦来自上海,早年曾留学日本,如今在上海有自己的生意和事业,是非常能干的女强人。我们这回日本自助游,从头到尾都靠她在当外联——除她之外,我们都不会日语。海伦祖籍台湾,她父亲自幼会日语。中日邦交时,她父亲曾给周恩来和田中角荣作翻译。
净因桑个子不高,光头,双目炯炯有神,说不上是仙风道骨,却不怒自威,很有住持的派头和气质。我们几位跟净因桑行礼招呼——来日本多日,已知见面鞠躬总不会失礼。我们是外人,就是做不好,人也不怪的。于是众笑,愉快结队,出去坐上净因桑事先叫来等候的计程车,开往高台寺。
一路出去,转的都是小街小巷。日常的京都,在这样的正午时分毫不起眼。无非是商铺、民居,矮矮小小地挤在一起,非常日本的自然色调,让人一时不知如何反应。
高台寺离京都名胜祗园、清水寺、知恩院很近,都在京都的东山老城区。车子转进那个方向时,我们坐直了身子,好奇张望。密集的寺庙楼字,一派的古色古香,小街上浅淡的门帘,巷里转走着的那些游客扮着的歌伎,让我们不停地轻叫,前一夜长旅的困顿顿时消失。
车子在高台寺月真院的小门前停下。门外是一条小街,可谓四通八达,可一径通往清水寺或知恩院,往来的游人不断。月真院的门很矮,出入不小心,会撞到头的。高台寺一般是不接待住客的,我们这回,完全是沾了海伦的光。
我们的行李放置在院里一楼的一间屋里,卧室则在楼上的一套两间屋里。完全是日本式的民居形式。那几日,我们四位女友一溜排开,就睡在榻榻米上。窗口是木窗杆的,小小几扇,可以看到院里。桂树正在开花,香气袭人,远望是秋日京都纯净的天色,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塔楼阁寺,让人以为是在梦中。
同住在这栋月真院楼里的,是在一楼的老和尚新田桑。那里有个开放的大厨房,院里有茶道馆,若接待茶客或作斋事的人,就会用此厨间弄吃的。洗澡房也在一楼,我们是跟新田桑共用的,卫生间则要拐过走廊,到作茶道的厅堂边上。我开始夜里总是有点怕的,因为走廊边上的小空地里,竟有些坟碑,还供着吃食和鲜花。它们是如此之近,阴阳并不两隔一般,跟美国人倒有些像了。后来我了解到,日本的墓地,基本都是由寺院经营管理的,是寺院收入的主要经济来源。而凡事也真讲的是个习惯,很快,我也就能自己夜里去晒收衣物、上卫生间,不再对那些坟感到害怕了。
老和尚新田桑很热情。他会几句中文,总是试图跟我们搭讪。他的眉毛都白了,但身手还是很矫健。我们到的第一个中午,就闻到了他煎鱼的味道。以我们对出家人的比较狭义的理解,都认为他是在“偷吃”!于是窃笑。后来明白,日本僧人修的是“人间佛教”,甚至可以结婚生子的,吃几条鱼,算不得甚么。
因语言不通,我跟新田桑无法有很多的沟通。但他对我很热情,我的好奇心又重,所以会比手划脚,或写着汉字,尝试交流。有次他给我看他的照片时,竟说中文:我是很老很老的老人!一百岁!我吓一跳,问:一百岁?他说是的呀,一百!带点口音的中文,却很清晰。我看着他的白眉,竟信了,赶紧上楼向我的女伴们报告,可她们没一个相信,我也不试图说服她们,自顾拿出从旧金山带来的巧克力,下去送给新田桑。转眼,他就背了个袋子出门,步履矫健地出了月真院。她们在楼上看得大笑,说,他将你的巧克力拿去给他的女朋友去了——后来,净因桑告诉我们,新田桑不过六十多岁,他还曾跟黑道有联系呢!大家就再一次笑话我的天真。
在京都的第一顿饭,是在月真院外小街上的一处日本小馆子里吃的。净因桑开始问我们的安排。说好夜里他请客,去吃大餐,看歌舞伎表演。下午净因桑带我们去看了高台寺。
高台寺是日本名将丰臣秀吉的夫人宁宁为思念亡夫而于1606年修建的寺院,也是她晚年的居所和去世后的墓地。在修建过程中,德川家康曾给予过资助。正式名称为高台寿圣禅寺,是日本国家级重要文物,也是京都东山一带的名刹。
高台寺里的楼台阁宇依山就势,亭台楼阁的气势都很宏大。它又是典型的日式
庭园,建筑全是原木的色泽,跟庭院里的草木和谐相间,看上去秀丽典雅,非常舒服。它里面的很多建筑不幸曾遭火灾焚毁,现仅存开山堂等建筑是为原始的景观。我们得净因桑亲领着看过寺内的伞亭、时雨亭茶室、灵屋、观月台等名胜景观,又说起他曾经接待过的张艺谋、巩俐、章子怡及中国的好些文艺界名人,甚是有趣。
高台寺春季的樱花和秋季的红叶的夜间灯饰观赏,是京都绝景之一,可惜我们来的日子不对,无缘得以观赏。净因桑说:这就给了你们再回来的理由啊!
净因桑招了好些中国留学生在寺里当导游,可见这儿的中国游客不少。我们就碰到了来自青岛和北京的姑娘,她们课余时间在这儿给中国游客作导游。她们说净因桑对她们非常照顾,她们也很适应和喜欢在京都的留学生活。看她们穿着式样老旧的灰色尼姑样的衣服,很是有趣。她们给我们讲解了景点的故事。我还托其中的一个张姑娘,帮我寄了发往美国的明信片。
京都第一夜里,净因桑招待我们的那顿有歌舞伎表演的大餐吃得非常开心。我们几位都是特地换了衣裙前来的,由净因桑领着在东山区的昏暗的小巷里穿行。石板路,昏黄的街灯,小巷里一家家门脸小小的餐馆酒肆,都安静地垂着素雅的门帘,或挂着月白的灯笼——在日本,绝少我们在中国随处可见的红灯笼,人就总是能感到安静。在京都秋夜的深巷里,一个和尚领着四位盛装出行的中国女子,一路说说笑笑,那种情景,大概真是日本才会有的。
净因桑订的应该是他熟悉的地方。我们被主人迎进榻榻米包间,非常正式。菜色一道道送进来,极其精致绝色,非常好味。为我们表演的那个十八岁的歌舞伎,还在学校里受训。她是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那种典型的歌舞伎的样子,很浓的妆,全是模式化了的,让她们的面孔看不出特色。她给我们唱了歌舞伎最常唱的一支曲子。有点像《四季歌》那样的内容:“春天我遇见心爱的人,夏天爱上他,秋天却分开,冬天妈妈就要我嫁给另外的人啦”。我听不懂日语,她脸上的表情又变化不多,只能从曲调里去想像。
说来也巧,正是看了这段歌舞,让我忽然明白了《色·戒》里汤唯给老易唱《四季歌》的那场戏。那时他们是在一个日本人的馆子里,邻间的歌伎正在唱,大概就是这种《四季歌》的调调了,汤于是跟老易说,我给你唱,我唱得比她们好!于是她唱了周璇经典的《四季歌》,男女主角的关系由此递进:“穿在一起不离分”——生出了天长地久的梦想。导演李安采用了这种延伸的意境,真是好手笔。
我们在京都的游历十分愉快。看过了著名的清水寺、知恩院、平安神宫、金阁寺、银阁寺等,还去了古都奈良。净因桑还为我们专门安排了一场茶艺课,让一位茶艺老师,给我们四位讲演茶艺,我们每人都有机会学了一次日本茶艺的功夫。
从奈良回来的当夜,我们如约,到净因桑的庭院里去吃他为我们亲自烧煮的“熬点”。
净因桑在门口迎接我们。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日本院落,他一个人住在里面。他领我们看过各房间,并告诉我们,这些都是他日日亲自收拾整理的,各处可以说是一尘不染。我们看过他的经房、他的茶室,处处都是简单洁净,东西很少,都很有年头的样子,配着经书读本和木鱼,让人不禁要轻声屏气。我们最后落坐在大厅里,那一桌的菜,已经备好。
所谓“熬点”,就是我们的火锅之类。净因桑说他从昨夜就开始炖了锅底,有鱿鱼、海鲜等,还有菜、肉丸鱼丸。这个夜里,我还第一次吃了用豆浆作汤底的“熬点”,非常特别、可口。
这时,净因桑拉掉暗厅里的灯,拉开通向内院的拉门,启动电源开关,那个美丽的日本庭院在彩灯的打照下,美如梦境。我们欢叫起来,我说了好几遍:我都想出家了呀!净因桑看着我温和地笑,说,你也可以在矽谷开个分寺啊,那口气,就像是在谈论开个分公司那样,果然是日本和尚。
我们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始了那夜长长的晚餐。我确实是个太过好奇的人,那夜竟问净因桑那么多的问题,关于宗教,关于人生观,关于净因桑的个人经验。我们的对话,全都得靠海伦帮忙翻译,而我太过投入,竟然都没有意识到,这让海伦几乎没能安稳地吃饭!
净因桑讲的其实是哲学,而不是我们平日理解的那种“宗教”。他大学原念的就是哲学,所以我能理解他的思路。他甚至说,没有所谓的地狱和天堂的,你自己的每一天,全靠自己在把握着是上天还是入地——这里面就出了禅的意思了。他还坦诚地跟我们谈到日本宗教界的一些问题,内里的复杂性。说到日本和尚是可以有妻室的,我们就笑问净因桑对自己的生活有何打算。净因桑笑起来,说,别人是可以的,但他的修行,他的祈告,就是这些都不要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都是负担”、“最好不要有负担才好啊!”——谁又能说不对呢?
我们四个女人,在那个美好的夜里,在热气腾腾的熬点桌上,和智慧又幽默的净因住持把酒谈笑,十分开心。如果有人在墙外路过,一定会很惊异于这日本的特别:夜深深的时刻,寺庙住持的院落里竟有男女谈笑风生喧哗如此。这是多么美好的人间宗教啊!
在当夜的餐桌上,我们又约好净因桑第二天一早来月真院带我们打坐。当我们在深夜里吃饱喝足,踏着夜色给净因桑道别时,相信每个人心里,都会同意,这个夜晚,是我们日本之旅的一道高光。
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我们就起床了。梳洗完毕下得楼去,盛装的净因桑已在茶室厅里静候。这日他换上了出客的住持服,看上去就像换了一个人,手里还拎着一把长阔的戒尺,“啪”地在榻榻米上拍出大声响。
我们四位一字坐下。按净因桑的指示开始学习打坐。我压根儿就没想到,打坐会是这样困难的事情,要姿态,要会呼吸,眼睛的张合还要有度。我一会儿就有点顶不住了身子开始乱动,好不容易熬到第一回合结束,就要求退出。净因桑严肃地看我一眼,说:你其实是最该练的。又摸了摸他的戒尺,说:如果你是我的学生,这就该上了!——这也许是开玩笑,但他的表情是严肃的。
我小心地退出到边上,给他们偷拍照片去了。
因我们各位都喜欢拍照,特别是海伦和佳佳,简直是专业的摄影师精神,所以净因桑在这个早晨还专门安排我们在高台寺向公众开放前进去拍照。那个秋天的清晨,已有些凉意。寺中的亭台楼阁,林木小径间,淡薄的晨霭和早晨金色的阳光纠缠着。我们在那个时刻,就是这个寺院的主人,寻找各自眼中的佳景美色。
离开京都那日,我们是从车站的大厅进入的,我这次看到的是大厅里浩大的挑高不锈钢结构的现代造型,让人真有在外星上的感觉。交响乐在轰鸣,宽大的电视屏幕上五颜六色的动感,人们进出上落,行色匆匆又规矩本分,它是古城京都的另一张面孔。就像净因桑平日家常的朴素和手持戒尺的威武,一体两面。我站在大厅里仰头四望,我知道我会一直怀念这些在京都的日子的。一直。
谢谢你,净因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