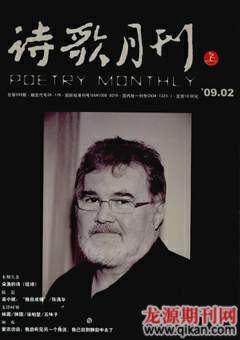文河随笔(二篇)
文 河
一个人的秋山
有一天,突然就无端端地想起了韦应物。我想,一定是这个古老的唐朝诗人在我体内的某个地方呼唤我了。于是,我打开了他的诗选。作为一个修辞爱好者,我对语言保持着一种天然的敏感,因此,一个在他的诗句中反复出现的词语不可能不引起我的注意。这个词语就是“秋山”。
在《淮上喜会梁川故人》一诗的结尾,诗人写道:“何因不归去?淮上有秋山”。此诗写于公元770年秋。而我们知道,公元755年,安禄山对唐玄宗发动了一场战争。渔阳鼙鼓动地来,从那时起,大唐的天下就乱了。当秋山作为一种情感的召唤和心灵的寄托时,它当然就不仅仅只是一种纯粹的客观存在了。但一座山,尤其是一座秋天的山,它又不可能没有自己巨大的阴影。对于这座山,诗人往往会把向阳的那面留给语言,而把背阴的那面留给生活。在《淮上即事寄广陵亲故》一诗中,这个词语再一次出现:“秋山起暮钟,楚雨连沧海”。在浩大低沉的天空下,一座秋天的山,仿佛完全变成了影子。影子是寂静的。而这个时候,作为对寂静的提醒,突然空中又响起了钟声。钟声是一种兼具真实与虚幻双重特质的事物,当它消失时,会留下更大的空寂——钟的声音消失了,留下了钟和钟的影子。当然,还留下了更多的雨水。每一滴雨水都很凉。
当一个诗人无处可去的时候,他就会把自己安置在语言里。事实证明,也只有语言,才是一个诗人最后的家园。一个词语,当它对一个诗人的暗示性过于强烈时,它就变成了明亮的灯盏,悬挂在家园沉默的房檐下。“数家砧杵秋山下,一郡荆榛寒雨中”。在《登楼寄王卿》这首绝句中,我们看到,“秋山”一词又一次出现了。砧杵的声音是质朴的,也是单调的,这是生活本身的声音。它在无边的寒雨中敲响,意味着生活对于温暖的固执的诉求。这首诗大约作于公元783年。诗人时任滁州刺史。我注意到在距上面《淮上喜会梁川故人》一诗的写作时间,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十多个秋天从一个人心中依次走过,又有谁知道,会踩出多少个苍老的脚印呢。脚印多了,一条通向秋山的路径就会自然形成——
“兹楼日登眺,流岁暗蹉跎。坐厌淮南守,秋山红楼多。”《登楼》一诗诗人依然写于滁州刺史任上。秋山依旧,但人已经老了。后来的刘禹锡这样咏叹道:“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刘禹锡是个达观的人,但这两句诗,还是散发出了无穷的感慨。和《淮上喜会梁川故人》一诗一样,在《登楼》这首诗里,秋山也是作为现实的对应物出现的。对现实产生厌倦时,对自然的向往就开始了。在这首诗里,诗人对于秋山的描述变得相对具体一些了。他写到山上红色的林木。一种明艳的暖色在现实的灰暗和清冷中显得格外动人。仿佛秋山才是诗人应该置身于其中的惟一现实,而真正的现实只是一座秋山的虚幻的影子。这里的秋山离他很近,似乎转身即能投靠。但我感到诗人虽然转过身来了,最终却仍然无法从现实的泥潭中迈出深陷其中的双脚。他对秋山的热爱方式只能是眺望。
一座美丽的秋山耸立在生活的对面。是的,那满山的红叶很快就会飘落的。但是,对于这座诗人的秋山来说,它“失去的仅仅是事物的毫无意义的外表(博尔赫斯)”。这座秋山有着自己的肌肤和骨骼。
契诃夫
喜欢契诃夫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大约十五六岁吧,暑假,我回到我的老家刘关庄,下午,半躺在檐前的藤椅上看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和《阿霞》,就看到一大片乌沉沉的黑云突然从西南方向气势汹汹的翻卷而来,明晃晃的阳光一下子消失了。狂风把门前两排大杨树吹得哗哗啦啦的,转眼间一阵暴雨横扫过来。朗朗乾坤完全变了个样。不过一会儿,风停雨住,天朗气清,阳光比先前显得更加明亮。这阵雨只是过路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记得那种长长的雨鞭狠狠抽打大地的情景,记得那两排白杨树在风雨中手足无措的模样。如今,那些树也老了。树刚一长大,就进入自己内在的秋天了。树的秋天比人的秋天漫长。那时候,我还没读到契诃夫。就是读到,我也许会更爱屠格涅夫的吧。相对于契诃夫,屠格涅夫的世界似乎比较明亮一些。打个比方来说吧,同一种月光,在屠格涅夫的世界里,这月光往往会落在水面上,星辉点点,波光粼粼,这里面充满了宁静的波动和闪烁,从某个遥远的地方,也许还会飘来缕缕花香。而在契诃夫的世界里呢,这月光也许就会落在大地上了,明亮中夹杂着更多的阴影,可以闻到牲畜的汗味和泥土的气息,不经意间,或许还可以看到某个点着灯的窗口。
当生活的年轮在我心中一圈圈扩大、增加,诗意的东西即使没有消失,也日益变得凝重了,所以,我又格外喜欢契诃夫起来。喜欢他作品中那种内在的深沉的诗意,那是泥土里的诗意,骨子里的诗意,而不是浮在这个世界表面上的光影。这种诗意不仅可以闻到,而且可以抚摸。《姚尼奇》、《带阁楼的房子》、《没有意思的故事》、《跳来跳去的女人》、《醋栗》、《草原》、《黑修士》、《带狗的女人》……他创造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这是一道不设防的风景,你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走进去,但很多时候,你却无法描述它。你只能默默地感受。到后来,这个世界又变成了某种温暖的流体,慢慢渗进你的生命或肉体。又或者变成某种类似于花香的东西,在无边无际的晚风中,低沉的萦绕着,挥之不去。
契诃夫四十四岁就离世了。他死得真平静,仿佛死亡从来就没有潜伏在他的生命之中。因此,他的死亡没有经过死亡的高潮,便直接结束了。似乎更是一个开始……在德国南部一个叫巴登维勒的小疗养地,1904年7月2日,深夜三点。他清楚的知道自己就要死了。他的死亡对他来说,没有丝毫悬念。到最后,他只想喝一小杯香槟。他的妻子克尼佩尔后来这样回忆道:“他拿起杯子,把脸转向我,以他特有的异常优美的微笑笑了一下说,‘我很久没有喝香槟酒了……他安静地喝完了那杯酒,轻轻地向左侧躺下,很快他就永远地沉默了……”看看,连他的死亡都像他一贯的叙述风格,朴素,平静,甚至还很优美。
和契诃夫一样,我惟一的叔叔离世时也是四十四岁。他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农民。因此,他身上几乎综合了所有普通农民的特点。临终前,我叔叔最想喝的东西是豆浆。因为,豆浆是他所能想到的最好的东西。我常常觉得,我叔叔的命运很早就被契诃夫描写过了。我叔叔不会描绘自己的命运,他的命运只能被别人描绘。他甚至不会反思,他只是默默承受。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他寂然而生,寂然而死。他走进了那个永恒的无底深渊,再也不会回来了。——生活的歌声无论怎么美妙动听,也无法把这个逝去的生命从深沉的黑暗和虚无中召唤回来。当我读契诃夫时,我常会想到我的叔叔,想到很多平时我不曾想到他的方面。通过虚构,我发现了更多的真实。这个遥远的早已消失的俄罗斯人,不断补充和丰富着我对自己亲人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