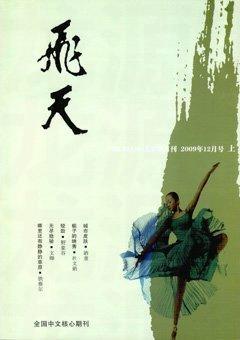透视苏轼之崇高:对《前赤壁赋》的新解读
叔本华是以反理性主义的意志论和悲观主义的人生观著称的德国哲学家,他的哲学中有深厚的西方思想做后盾;而苏轼作为中国的文学家,他所著的《前赤壁赋》中也包涵有传统的中国古典精神。这两种全然不同的理论和文学何以能够相互阐释,相互印证?他们之间相互联结的纽带是什么?是印度佛学。
一、佛学思想——叔本华哲学与苏轼文学互释印证的纽带
作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苏轼以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吸收了儒释道三家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生观。儒家使他能够心系民生,积极进取;老庄使他能够怡情山水,修身养性;佛教思想则使他认识到万物皆空的真谛。三家思想相互交融,使他进则能奋厉治世以“致君尧舜”;退则能寄兴佛老,以求“静”求“达”。而自“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苏轼便更加倾向于佛道思想了。他的作品中除直接用来阐发佛理的偈语(如《养生偈》《戏答佛印偈》等)外,还表现出一种佛教的人生观。如“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1](《念奴娇·赤壁怀古》),表现了梦幻的人生;“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1](《和子由绳池怀旧》)表现了偶然的人生。正是由于他看透了人生的梦幻性和偶然性,因此能在内心感悟中超越世俗情感,表现出“也无风雨也无晴”[1](《定风波》)的淡定的佛教色彩。
叔本华自称是康德的后继者,在他的意志论哲学的建构中,康德哲学和柏拉图哲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他同时也深谙印度佛学。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他用于解脱人生痛苦的两种方式(禁欲和审美)均带有佛学色彩。前者是宗教的方式,它要求个体通过苦行、绝欲来泯灭自我意志,最终达到人生的寂灭;后者是审美的方式,它要求个体通过审美观审超越尘世利害之外,获得暂时的宁静。相对于前者的“寂灭”来说,它相当于一种暂时超脱人世欲望的小“涅槃”境界。阎嘉教授曾经提到,印度佛学在叔本华哲学中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康德哲学和柏拉图哲学,“尤其考虑到叔本华哲学的终点走向了‘世界是无,人生的幸福之道在于以智慧克服意志,用哲学、艺术、宗教来净化意志,最后臻于佛教的‘涅槃境界”。[2]
正是佛学这根纽带,使叔本华和苏轼跨越时空界限和文化传统走到了一起,使他们间的相互阐释成为可能。
二、《前赤壁赋》崇高之体现
叔本华理论的建构是在康德的启发下形成的,在关于崇高的理论方面,他保留了康德关于数学的崇高和力学的崇高的划分,不过滤去了康德关于道德内省方面的内容,而注入了印度佛教思想,从而赋予了崇高以新的内涵,即主体在面对与之存在利害关系的外物时,依靠本质内省力,克服个体化原则,从而超脱利害之外,作为纯粹认识主体直观眼前之物,获得内心的宁静状态。从叔本华的崇高论来看,《前赤壁赋》同时体现了数学的崇高和伦理的崇高。
(一)数学的崇高
数学的崇高是由于对象在数量上的绝对的大引起的,它的形成需经过以下过程:
第一,大小的对比引起观赏主体的压迫感。当一个沉溺于尘世欲望的个体在观察“这世界在空间和时间上无穷的辽阔久远时”,对象的大和个体的小形成强烈对比,从而使个体力量变得渺小,甚至被压缩至零,觉得自己作为个体和“无常的意志现象”,“就像是沧海一粟似的,在消逝着,在化为乌有。”[3]
第二,观赏主体超越个体性原则,成为纯粹认识主体。在强大对象的压迫下,个体意识起而反抗自己渺小、虚无的事实,将个体上升为整体,成为“纯粹认识的永恒主体”。
第三,纯粹认识主体直观眼前之物,获得平和宁静之美感。
在《前赤壁赋》[1]中,苏轼由“望美人”而不得,到叹作为“一世之雄”的曹操及其他的功绩的消逝,再叹自身之须臾与长江之无穷,最后由变与不变的哲理阐释归复平静,这一过程同叔本华对数学崇高的体验过程相似,不同之处只在于《前赤壁赋》把审美主体的体验通过主客对话的方式外化出来,其中,“客”代表了欲望主体,“苏子”代表“自由而不知有任何欲求和任何需要”的纯粹认识主体,他们的对话构成了作者内心两个方面的冲突和斗争:
泛舟之初,尽管苏轼给我们描绘了一幅“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极乐图景,但从他吟唱的“望美人”歌中可看出他仍有出仕的愿望,“幽壑之潜蛟”“孤舟之嫠妇”恰是他自身怀才不遇的写照。这时,苏轼只是作为充满欲望的个体而存在,而他所面对的对象——不停流逝却未曾变化之水、盈虚有数却并未消长之月都是广阔辽远,永恒存在的。相形之下,个体的人仅仅是寄于天地之间的蜉蝣,沧海之中的一粟,恍惚而来,须臾而逝。大小之冲突对立,让人无法释怀,只好“托遗响于悲风”。在对比的苦闷中,苏轼通过一种变与不变的哲理阐释——“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超越尘世功利之外,将个体提升为与万物相通的整体,从而摆脱物我之间不均衡的大小对立,以宁静平和的审美心态观赏“造物者之无尽藏”。
两者都是由欲望而起,由宁静而终。但这种宁静不是通过欲望的满足,而是通过欲望的舍弃而得,因而显出一种看破红尘,消极淡定的佛教色彩。
(二)伦理的崇高
叔本华对于崇高的说明还可移用于伦理的事物上,特指一种“崇高的品德”。具有崇高品德的人,往往能摒弃自我意志,以纯粹客观的态度观察世人。因而当他们在面对适于激动意志的对象时,却不为所激动——看到世人对自己的不义却不因此而憎恨;看到幸福而不嫉妒;看到美色而不想占有。[3]
以此看来,叔本华所谓伦理的崇高似乎就是一种从始至终不为意志所激动的绝对宁静的状态。其实不然。从以上分析可看出,叔本华的崇高本身就是一个“压迫——抗争——反思——宁静”的由动至静的内心体验过程,而最终的宁静只是崇高感的一个必然结果。伦理的崇高作为崇高理论在伦理上的移用,乃是指主体在同生存意志的激烈斗争中,在尖锐的痛苦中对自我精神的纯化和提升,它最终表现为一种平和泰然的人格魅力。他曾引用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话来加以说明:“因为你过去,象这么一个人,在备尝痛苦中并不感到痛苦;象这么一个人,不管命运为他带来的是打击或是酬劳,你都以同等的谢意加以接受”。[3]
这段话本是哈姆雷特用来描写霍拉旭的,但也可用于对苏轼的写照。身为文人士大夫,苏轼自觉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然而却屡屡遭受贬谪之苦。“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4]便是他一生贬谪生涯的总结。《前赤壁赋》作于元丰五年,也即作者遭“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的第三年。我们从殷殷渴盼的“望美人”歌,“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箫声,“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自况中,可看出作者内心的失意苦闷和惆怅幽怨。然而,此种境况下的苏轼,仍能借佛老以自释,逍遥于江湖,进入“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的自由境界。这种对名誉、荣辱、得失、成败都能泰然处之的平和心态,这种“足以千古”的人格魅力的体现,正是叔本华所谓伦理的崇高。
综上所述,由于佛教这跟纽带,西方理论在中国文学中得到了印证:《前赤壁赋》的泛舟游历和辩论释理过程完整地反映了叔本华数学的崇高,而其中所体现的苏轼的人格精神又吻合了叔氏伦理的崇高。其实,中西思想虽有不同的渊源和表达方式,但关于人生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则中西哲学文学兼而有之,从而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第三卷[M].北
京:中华书局,2007.
[2]阎嘉.洞悉人生痛苦的智者:叔本华[M].成都:四
川人民出版社,2000.
[3](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
[4]苏轼诗集.第八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2.
(作者简介:黄学燕,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