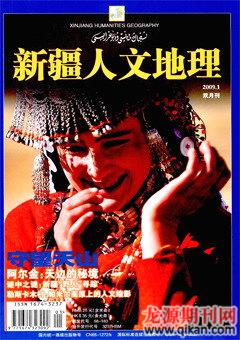勒斯卡木村:帕米尔高原上的人文缩影
刘湘晨
在帕米高原,对于散布在河谷之间和河漫滩草甸的大多数人来说,勒斯卡木是一遥不可及的丰在隐藏在重重大山之中。这是一个仅有7户人家的小村子,牦牛蹄子下的一条山道是这个小村子与外界唯一的沟通。
关于勒斯卡木村的种种
每次翻过盖加克达坂,用不了走太远,回头一望,在一片相去不远的山景之间,你倾尽体力刚刚翻过来的那个高山峡口转眼就很难再区分出来,这个细节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
中国塔吉克族的总人口近四万,占中国总人口的比率实在太小;勒斯卡木村的总人口不会超过一百人,这是大多数塔吉克人都很陌生的一个世外小村,每每让我想起都会眼底潮热……
勒斯卡木村每年九月才熟的杏子还是那么甜吗?
勒斯卡木的都尔那玛大妈和提加大婶待我亲如老母,每次去,在谁家少住一个晚上,少吃一口饭,也会让老人家不高兴。这些年过去,她们都是70开外的老人了,我惦记着她们的身体是不是很好。而我更多的担心是,几年之后,盖加克达坂我能不能再翻得过去,翻过去能不能再见到两位老人呢?
艾尔肯、鄂郎米克和沙迪尔这些小伙子正值虎狼之年,按辈分算弟弟,按年龄是儿子,在我走后这么多年不成家是不可能的了,他们娶的是谁家的姑娘,现在已经有几个孩子了?
提加大婶的小孙女第一次见我就叫我“汉族爸爸”,这是我一直想把她带出大山的原因。她的名字很好听:姿雅迪曼,翻译过来的意思是“众月之月”。这些年过去,她出落得该是一个“倾山”的大姑娘了,我一直等着她走出大山读书的消息,至今还没等到……

但是,我知道,这个翻译成汉语意思是“温泉”的勒斯卡木村,不仅仅具有怀恋价值,在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那么一片山地,人类追寻生存的努力竟然没有遗漏。
在帕米尔高原东部边缘的无数峡谷之间,找到勒斯卡木这条沟怎么说也不是轻松工夫。锁在重山之间,一根绳似的一条路在裸石和野林之间蜿蜒伸曲,两天或者三天之后才能看到一片山间阔地,这就是勒斯卡木人的家。
可能,正是因为这两天或者三天才能穿得过去的山的阻隔,勒斯卡木保留了人类追寻生存之地所有最初的信息和他们形成的所有有关这个世界最初的见解,再加上较少受到外界的影响,能够让我们今天的人侥幸看到一种隔世的样式,由此,勒斯卡木成为整个人类的经历和寓言。
编年史
说起来,这已是整整10年前的事了。我第一次穿越盖加克峡谷到达勒斯卡木,第一个见到的人就是提加大婶的男人,没想到第三次再去的时候,这个人就不在了,我非常后悔没能给老人家留一张照片。
记得是在一棵杏树下,村里年事最高的这位长老每天都会在杏树下的一张椅子上坐很久很久,偶尔站起来,手搭作一个棚向远处望。就在这样一个时候,他第一个看见我渐渐走进了勒斯卡木村。我清楚地记得这位长老与我相见并握手的感觉,没法儿握得紧,他和我的两掌之间被硌着:他的一根手指残颓,仅剩寸半棍头儿的一截儿。
由于塔吉克人口总量少,迫使他们每每都在突破生育的危险临界:三代以外,甚至不出第三代,父系血亲之外就可以通婚,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各种各样的畸形。这是塔吉克人为种群繁衍付出的代价。
这位塔吉克长老让我吃惊的另一个地方是他的叙事方式,凡年代必讲得极清楚,不是阿拉伯数字的简称,而是把标准的公历纪年全读出来:
一千九百二十七年,水大大的嘛,房子没有了嘛。
一千九百四十五年,那个石头山上下来了嘛。
一千九百五十三年,杏子一个娃娃(果实)没有。
一千九百五十七年,雪这个地方(指没过大半腰),羊、牦牛没有了。
一千九百六十八年,塔吉克的吐马克换了解放军的吐马克(帽子)……
最后,他说他“一千九百九十八年乌鲁木齐去”。估计,这是这位长者为自己一生策划的最远的一次远行。
非常遗憾,我最终没有在乌鲁木齐等到这位长老的来访。随着他的去世,10年间我已得到勒斯卡木村其他一些人陆续逝去的消息,每每想象中大山遮蔽的那个小村更有了一种世事沧桑的感觉。
我很后悔没有与这位老人更多的聊天机会,他大半生都在小山村教书,他的存在和他的叙述方式,是勒斯卡木岁月沧桑最重要的纪年方式和佐证。
地理符码
勒斯卡木恐怕是天下最大的村子了:从村子的这一头到那一头,骑一匹快马十天未必跑得完。沿塔什库尔干河谷南北贯穿的中巴公路是两千多年前著名的葱岭古道,蹚过大路东侧的塔什靡尔干河距勒斯卡木村的山门盖加克达坂就不远了。十年间,我至少不下十次翻越这座达坂,比许多远没有深入塔什库尔干河以远的地道的勒斯卡木土著一生翻越的次数还多。
到达盖加克达坂之前,在距县城大约8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每个高原旅人必看的吉勒尕勒古驿站,距今大约两千年。仅百步之外,帕米尔高原至今发现的唯一一处旧石器文明遗迹,就在塔什库尔干河畔仍在不断坍塌的一片断崖之下。每到午后,西斜的阳光贴着崖沿刚好照进洞穴并从洞穴的顶端慢慢向底部移动,最后落在一层有两指宽的赭红色的土层之上而后很快退去,这是高原最早的古人类的一处烧火遗迹,距今约八千至一万两千年。
人类最早起源于非洲已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这些最早族人的后代何以会在八千年前或一万两千年前的某个下午跨越亚非大陆来到帕米尔高原搞了一次篝火party呢?也许有另一种解释,这是另一个族群或者是沿着另一条繁衍线路发展的人类先祖?这种推测和想象的时间概念常使我有一种错乱和迷离,昨天、今天与明天,或过去、现在与将来,这种时态的描述对帕米尔高原完全不着边际。帕米尔完全是空间对时间、质量对矢量的一次越位与突破,这使帕米尔始终处于既真实又虚幻的两极之间。
我的这个感觉在我进入勒斯卡木村的时候,又得到了一次强有力的佐证。
进入勒斯卡木村,一条线路是绕行新藏线从勒斯卡木村位于帕米尔高原东部边缘的一边进入,另一条线路就是翻越盖加克山门到达小村腹地。在翻越达坂之前,我很快注意到塔吉克人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地名,我特地嘱咐我的两位塔吉克兄弟把沿途的地名全部记了下来:

乌鲁克苏:这是一个宗教故事,一位圣者长途渴极,最终找到了一股清流,人和马喝下去倍觉精神,从此,这里被称作“圣水”或“伟大的水”。
盖加克达坂:风大,让人冻得发抖的地方。另一种说法,是让人可以等到野兔子的地方。
克拉鲁阿勒:出火药的牧场。
莫力吉兰:一种牛爱吃的草名。
塔里迪库勒:树苗子长得很直的地方。估计是红柳。
卡西促勒:两个馕坑。
吉力木阿勒:临近石头的地方。
迪先拜夏依迪沟:这是一个故事,有一个人路过这里被山上正巧落下来的石头砸死了,从此,死者的名字就成了这里的地名。
卡西布克:有很多河湾的地方。
达林卡波尔戈:很久以前,一个叫达林卡波尔戈的人住过一个晚上的地方。
黄卡边拉克:麻黄草很多的地方。
盖加艾劳克(吐乎鲁克):新牧场。
沙特马力克:树棚屋,一群做木匠活儿的人路过这里打了一个遮阳棚让人可以休息的地方。
沙赫马克:打火石很多的地方。
奉木考克(依沙布拉克):温泉。
托库子布拉克:九眼泉。
穹托阔依:临河的大牧场。
包仙迪江:村的尽头。
可可塔西:绿石头很多的地方……
上述这些地名,仅是从盖加克达坂以西到村里第一个居民点沿途的地名。后几个地名更为简略,略去了所有途经地名,仅保留了几个民居居住区域的地名作概略。从第十五个地名到第十九个地名之间,相连的路至少得让人走五天。另一点,十九个地名称谓多是塔吉克人叫熟的地名,其中,有些是柯尔克孜语,如盖加克、克克塔西;有些是波斯语,如包仙迪江、塔里迪库勒……据当地人说,距今三代人以前,勒斯卡木一带讲波斯语的人尚很普遍,这隐约透出一个信息:很久以前,勒斯卡木,更大范围则是整个帕米尔高原,尚是波斯语系非常普及的区域,仅百年之后的情况已大为不同。

对上述十九个地名再作分析,不难看出:“乌鲁克苏”与东部帕米尔最开阔的塔什库尔干河谷仅有一河之隔,站在高处望去,让人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巴(基斯坦)国际公路在阳光和冰峰的辉映下蜿蜒伸去。两千多年前,那是丝绸之路中国路段最西端的葱岭大道。这条公路,不仅是商贸大道,也是文化载体,使伊斯兰教最终叩响东方的大门,有“乌鲁克苏”这样的地名也就不奇怪了。
翻过盖加克达坂,情况大为不同,不但没有宗教影响,甚至找不到哪怕最轻淡的文化色彩,这不能不让人吃惊:仅仅相隔一道达坂,竟成了文明的分界,其余地名再也没有与伊斯兰教的一丝瓜葛。很显然,这里列举的所有地名,几乎都是最先抵达这里的人以第一眼看到的东西和最先发生的事件随意命名,最终习惯成俗,流传下来。当我最初把这些地名记录下来的时候,我犯了一个判断上的错误,以为这些地名全不似敦煌、嘉峪关、轮台、龟兹……这样的地名有西风萧瑟的雄浑意境和深远的文化蕴涵。稍作梳理,从发生形态上细细揣度,我不禁大为吃惊:勒斯卡木人所处的心理年代,远早于古希腊人的城邦文化和罗马人的神话时代,还应该在中国的三皇五帝之前。这是一个没有史诗、神话和尚没有形成任何传统的年代,这是一个英雄和诗人尚未诞生,每个人都更能表现自我,每个人都更具“英雄”实质、表现“英雄”风采的年代!如同一座山、一条河,只有作为自然有机片断或部分的意义,尚未脱离自然,背离自然,进而支配自然成为主人。这是英雄未临、而人类的智慧还远不止于膨胀的黎明之前,只等创始的第一声雷鸣。
辟力克节
在1996年这个年份,我42岁,第一次进入勒斯卡木村,在乌鲁克苏牧场遭遇了高原近大半年的雪季,雪从当年的九月一直持续到来年的五月。在没膝的大雪中走,拖不动腿,我偎着一堆牛粪火看雪花从屋顶外往屋里飘。那一会儿,塔吉克人石屋的一方透空的天窗诗意飘逸,隐约有簌簌落雪的声音。后来,我翻越盖加克达坂去勒斯卡木村,沿途随处可见牦牛的尸骨累垛。这一年,莱提甫·霍加一家的40头牦牛全部冻死了。
在中亚的各个游牧民族中,塔吉克人的草场位于垂直植被带的最顶端。在这个海拔高度,不可能有蒙古人或哈萨克人的大片草场,加之在高原特定的气候条件下草情短暂,单一的游牧很难支撑塔吉克人的全部生活,这使得他们在高原河谷间不断寻求与开拓成为必需。零星的地被开出来,最小的地块并不比一个面盆大多少,种植一季小麦或青稞,由此构成莱提甫·霍加一家及其周边邻居们全部的生存格局:一半是高原牧场,一半是农区,一座海拔5500米的盖加克达坂是两边的天然分界,连接两边的路要走两天。
我到村子里的这天已是午夜。第二天早晨天刚亮,久视高原雪景的眼睛一下有被水淋的清晰,黄橙橙的杏子点缀着各家前后油绿的杏子树,杏子树稍远是大片的麦黄,沿山坡一片雾气升腾,走近一看,有晶亮的溪水汩汩溢出。
这天午后,莱提甫·霍加的老伴都尔那玛大妈拽着孙女、孙子出了门,满山遍野地在拔一种褐色的草杆儿。这种草叫卡吾勒,有油性,耐烧。在女儿和儿媳淘米的时候,大妈把采回来的一捆草杆逐一截成两柞长短,然后缠上棉花蘸上菜籽油,这是在为塔吉克人所独有的辟力克节做准备。所谓“辟力克”,是火把的意思。这一天,是伊斯兰历巴拉提月的第十五天。
照人类学的一般见解,火把是太阳的直接指代,这是人类宗教意识最早、最初期的形式之一。我很纳闷儿:由于地缘关系,塔吉克人是中国最早接受伊斯兰文化影响、并且至今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何以保留这种典型的原始崇拜的形式呢?
傍午之后,勒斯卡木的各家都出了门向村西头聚拢。这是一片稍显稀落的坟地,最早的坟不经人提示踩过去都不知道。这里埋葬着勒斯卡木自有人居住以来的所有逝者,最早的先民距今大约三代之前。勒斯卡木村的完整谱系翻到这儿,才能让人看清它的全部面目。
勒斯卡木村的全部老少男女穿梭在零落的十几处坟间,并不是像汉人那样仅把心思投在各家的先人那里,而是每一处都走到。他们以手轻抚坟堆,再逐一触摸自己的额顶和胸前,那是现时对往世的问候,也是祈望先人的祝福,希望能够相承先人所有美好的品性与成就。在此之间,村里最年长的几位老妇人将浸了菜籽油的卡吾勒草杆儿埋在地上点起来,然后率众围坐在坟前。塔吉克人哀伤而优美的哭丧歌随即响起,一人唱众人和,整个山谷一时为这高原的灵歌而肃穆:
(领唱)撇下我您就走了
(众和)走了……
您是故乡的一盏明灯
明灯……
您是故乡的一根拐杖
拐杖……
这个世界上再也见不到您这样的慈父
慈父……
没有留一句话您就走了
走了……
愿您的安眠之处是天堂
天堂……
愿您的灵魂安息
安息……
丧歌起伏之间河水的喧哗远了,夹杂的是女人们嘤嘤的哭声和男人们摸鼻子唏唏簌簌的声音。稍静之后,莱提甫·霍加坐定吟诵祷文,众人最后附和诵礼,形式与维吾尔人的“都瓦”(伊斯兰特有的祷告仪式)完全相同。接下来,各家打开各家的包裹,有馕,有温热的茶和一堆杏子,最具特色的是奶和米煮的粥。大家围在一块儿吃,言语间是村里村外的趣事和未必有趣却有人爱说的零碎,不时激起笑声,让人有久违的感动。

勒斯卡木人在“辟力克”节这一天全族的祭祀,以莱提甫·霍加作为村里长老之一的身份率众完成“杜瓦”仪式,这说明塔吉克人与伊斯兰文化的基本关系。不过,我很意外:唱丧歌是地道的塔吉克“土著文化”的内容,祷告是典型的伊斯兰仪规,塔吉克人对两种不同文化的这种前后次序的确定,依据是什么呢?
在这天天黑之后,勒斯卡木村的各家都做了好吃的。莱提甫·霍加一家做的是抓饭,虽没有肉,在一把卡吾勒草杆儿点起来的火光的映衬下,油汪汪
的米粒儿格外诱人。在盖加克达坂以东的遥远边地,这样的饭,毕竟不是常日能随意赶上的一餐盛宴。餐后,最隆重的仪式是由莱提甫·霍加夫妇先行开始,孩子们由大到小逐一往下排,每个人默默许愿,然后靠近卡吾勒草杆儿点的一蓬火以双手撩着火苗子往脸上抹,这是最典型的以火祈福。
虽然已过去了千万年,塔吉克人的生存环境依然没有改变,影响他们生存状态最重要的原因,至今仍是高原上最古老的那些因素:日照时数的多少,雪季的长短,草情的好坏……其间,最终极的原因就是太阳。
正是因为上述这个原因,当世界上其它地域与文化的族群多已远离日神图腾的时候,塔吉克人的古老心境依旧,决定他们生存最终极的原因和影响他们精神世界最终极的因素,依然是太阳!相对于此,伊斯兰教及伊斯兰文化对他们的生存尚不能构成根本的影响,由此决定了在他们心里的位置和距离。
“辟力克”节这天晚上最重要的内容,是莱提甫·霍加在灶前点燃火把,然后通过屋顶天窗把火把递出去,早在等候的孙子萨迪尔攥着火把从屋顶跳下去再和村里各自攥着火把的孩子们聚在一起,他们排成长队呼喊着、尖叫着,向暗夜笼罩的山野跑去。跑到村里的温泉边,孩子们将所有的火把丢在一块儿堆起一丛篝火,然后纷纷从火堆上跳过去。照塔吉克人的理解,凡从火堆上跳过去,跳一次就减少一次罪过。孩子们未必能明确地知道这些,这只是一个欢悦的游戏,惊异与兴奋使孩子们个个成了跳跃在火焰之上的精灵,他们的笑声和尖叫使暗夜中守护着勒斯卡木村的四周高大山壁发出久久的回声。
马群从高原上踏过
跟随任何一位塔吉克人走出去,很快会注意到塔吉克人彼此见面礼数的周到堪称世界之最。有客策马而至,听着马嘶和渐近的吆喝声,主人会早早候在门外。及至见面到落座,同样的问候会重复三到四次。若是一年之内遇有丧事,有或远或近亲戚关系的人还会起身问候。我很吃惊:散落在大山之间各自居住偏落的塔吉克人,对人际关系何以会如此关注呢?

在勒斯卡木村待了十几天之后,各家的狗见到我已不再像最初见我那样狂叫。等到狗再叫,我这个勒斯卡木地道的“外人”也知道有客进村了。在大多数时候,进出勒斯卡木的人很有限,他们的来或走就是很大的动静。对这种来来去去的关注,最终把我的视线投入勒斯卡木村以外更广大的范围。我才弄清楚:以一眼温泉最先叫起来的这个小村子,只是勒斯卡木村的一个居民点,另有十几个大小不等的居民点分布在扎莱甫相河河谷两边的零落山谷之间,构成了帕米尔高原东部边缘稍显稀落的人文景观。
从一个居民点到另一个居民点,少则一天路程,最远的牵着骆驼要走八九天,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么长的路距,没有足够的支撑是难以想象的,你就不会奇怪勒斯卡木人每家每户何以每年都会消耗上千公斤的面粉。来往人多的时候,一家一天打两次馕不稀奇。
就绝对海拔高度而言,帕米尔高原并不适宜人类生存。但高山之间有一条条纵横分布的峡谷,其海拔高度相对较低,形成了河流和草甸,稍稍宽阔一些的河谷就成了人类聚居地,由此形成了类似勒斯卡木或辟力这样的许多鲜为外人所知的世外桃源。这些地方,海拔高度大多在2500米上下,甚至更低,有杏子树、柳树或其它一些矮科灌木生长,最大的障碍是远离中心、高山分割和彼此的路途遥远。
帕米尔高原的独特环境,使人的生存无法独立存在,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就成了塔吉克人最为敏感的神经。在塔吉克人那里,少做几次“乃玛子”(祷告)未必会有多少人议论,若是有客人到访招待不周,将会受到最强烈的谴责。面对帕米尔高原连绵不尽的大山,单独的人和生活的每一个片断清淡得都可以忽略不计,群体的联系和关注成为最重要的生存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帕米尔高原,几乎不存在纯粹属于个人的事,擀毡子、碾场、盖房子、娶媳妇、生孩子……在塔吉克人生存的每一个层面,群体的关注无处不在。其间,尤以婚丧两件大事表现得最为突出、充分。
在勒斯卡木村,我有幸参加了肖那扎夫妇独女雅库提的婚礼,一通手鼓敲响,一阵马蹄声滚过,整个帕米尔高原都被震撼!
婚礼最初是由极少的几个人开始的,他们是主婚人家的亲友,或者是村里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受主婚人家的委托提前几天就出发了,走到每一条有人居住的峡谷把婚讯和主婚人家的邀请带到。这是帕米尔高原的东部边缘,距最近的城镇也有三天到五天以上的路程。等到约定的一天,散落在各条峡谷的人们都会穿上盛装而动,有骑马、骑骆驼、骑牦牛的,多数是徒步,高原上一时烟尘滚动,迅速掠过的风挟裹着他们的呼喊声贴着河面远去。
婚礼上最令我感动的有两处:一处是主婚人拿着手鼓逐一走到每一位在场的来客面前请求被允许,以这种方式向这一年有丧事的人家表示歉意。通常,人们以击鼓的方式表示同意或接受;另一处,是婚礼最后由村里的长者向新人祝词,所有殷切的愿望、教诲都包含其间。在这里,最核心的内容,就是部族对一个分子的认可和被允许。不仅如此,每一对新婚夫妇和他们以后组成的家,除了父母之外,还有一位婚姻之父,其地位介于亲生父母与西方人所说的“教父”之间,会代整个部族对其最小的一个社会构成单元负责,所有的琐事,夫妻不和直到下一代人的婚姻,都得向婚姻之父诉说并最终由婚姻之父做出评判和选择。此种情况,为新疆各少数民族所少有。
婚礼的高潮,是鼓乐、鹰笛和舞。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更接近有山鹰出没的环境,塔吉克人与鹰神形俱肖的舞蹈兼有飘逸与奔放的两种品质,那些衣衫不整的人不是在跳舞,是借了一副鹰的翅膀乘着舞的神意在飞翔,人人脸上都是写不尽的尊贵和陶醉,在被踢起来的一片烟尘之间,你能感受到的是狂欢,更有融融的暖意流淌,那是高原上的塔吉克部族给每一个子民在上一堂形象的教学课。
抛撒给你的是幸福
高原八、九月,天空透朗,河青草绿,牦牛披着黑色的金丝绒,许多塔吉克人家都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娶媳妇、嫁闺女。这个时候,高原上往来的游客和旅行者很容易碰上塔吉克人家的婚礼,让他们最不可思议的,是婚礼上每每看到人们相互在抛撒面粉,新郎新娘面目全非。人群走过,地下被踢起来的烟尘和面粉白色的雾跟随着人群移走,久久不散。大概是因为婚纱和面粉在颜色上的接近,人们普遍接受了一种解释:塔吉克人的抛撒面粉是一种祝福,白色象征着纯洁。

在我第一次进入勒斯卡木村的时候,各家墙壁上的白色纹饰最先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些纹饰一般在紧邻房顶之下不足半米的墙上,或在灶边左右的墙上。涂纹饰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用石灰刷,一是用面粉撮撒上去。
不几天之后,我赶上了唯塔吉克人所独有的辟力克节,让我亲眼见识了塔吉克人重用面粉的情景:都尔那玛大妈、提加大婶和巴努汗的母亲,三位老人各端一个盘,揪一撮一撮面粉朝墙上甩,看似容易,实际上,照一定规则甩出纹样,村里也只有这几位老人才做得最好。
再后来,都尔那玛大妈去看提加大婶小女儿刚出生的孩子,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抛撒面粉,往墙上撒,也往人身上撒。
每逢佳节或喜事,塔吉克人万不能少的一个仪式就是抛撒面粉。
事实上,高原塔吉克人的农区,能种的作物只有一季小麦和青稞,而且数量有限,这决定了他们的粮食供给必须部分或全部依赖大山以外。更久远一些的时候,这意味着塔吉克人畜群和毛皮的大量支出。
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加之食物的过于稀缺,都使塔吉克人有一种近乎敏感的关注:除了食用,面粉被赋予了更多、更丰富的蕴意。
每有婚礼,牛羊、毛毯是最好的礼物。但是,所有最贵重的东西,也不能替代一撮面粉所能表达的意义。实际上,这是我们这个世界所可能有的最隆重的祈福仪式。
高原深藏的隐秘
高原的雪季,能见到真正的鹅毛大雪横飞,整个天空被添塞得密不透风。跨入高原塔吉克人累若积木的石屋。让人一下子彼此都看不清眉目。我喝着奶茶,然后靠在墙边准备坐下去,猛一下被女主人的惊叫声喊住,等她过来扒开一堆衣物抱出一个孩子,我才意识到后怕。

被抱出来的小孩儿一声没哭,在翻眼或动嘴巴的时候,才能搞清楚他的头脚两头儿,整个身体裹在襁褓中,脸被涂抹得漆黑。我最初以为,这个孩子,很可能得了什么病,后来辗转在高原的各处,在几家看到婴孩儿被涂抹得一脸漆黑,还亲眼见识了一个孩子被抹黑的整个过程,漆黑的色料是烧糊的杏仁儿。
我一直觉得,所有人都应该对高原塔吉克人怀有一种敬意。作为最典型的高原文化类型,塔吉克人在替整个人类做一种最极端的体验和尝试,如极顶的爱斯基摩人和赤道周边的各个部族。在塔吉克人的方方面面,都表现出一种简单到简陋的线条,严酷的自然环境使生存成为最大的挑战。另一个方面,近亲繁衍使塔吉克人命脉的每一个细部时刻都存在着巨大的隐患与危机,更无奈的是,直到今天,他们仍没有找到能够克服厄运的任何办法,由此构成了最基本的生存境遇,然而我吃惊竟没有听到塔吉克人的一句怨言。
基于生存背景的过于严酷,一脸沉静的塔吉克人对生命始终有一种敏锐到害怕吹口气就会不在的警觉。我注意到在他们每天都会重复无数次的问候中,一直有不愿意触及或者说始终在小心避开的一个话题,这就是孩子。那么,给孩子抹上一脸漆黑,是不是也出于同样的心理呢?
经过生命延续的漫长过程,塔吉克人找到了善待、呵护生命的一种最佳方式,用最草根化的方式让生命最珍贵、最神圣的内容成为最普通,实际上,那是一种掩藏和转移。想象零落分布在高原各处的塔吉克人,每一家的孩子就是他们最大的隐秘,不事声张,甚至每一个人都不去说。一个小生命初来人世,塔吉克人以为:这是一个生命最为脆弱、最需要呵护的时候!
一定有许多说得清和说不清的原因让塔吉克人最终固守高原一直到今天,更为吃惊的是,当伊斯兰文化从一千两百年前沿着丝路孔道迅速蔓延,如此强劲的震撼竟没有动摇塔吉克人基于生存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太阳崇拜意识。那么,生老病死,甚至是雪会有多大,两天驼路之外的一条河能不能过去,凡此种种的疑问和迫在眼前的事,塔吉克人会用什么方法解决呢?

在勒斯卡木村,每每待客或节日,如提加大婶和莱提甫·霍加这个辈分的乡村长老,吃完羊肉必做的一件事,就是留出羊的肩胛骨剔干净,然后根据骨面的纹路、厚薄和阴影的图形及大小来说事,最绝的是能准确知道谁家有病人,甚至哪一家哪一天会有什么人来。
人类寻找完善之途的努力和方式可能有一千种、一万种,塔吉克人只选择了一块羊的肩胛骨,一切的隐秘与玄机都隐含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