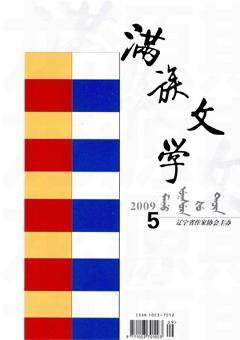只眼欧美
[满族]魏进臣
拉斯维加斯的街景文化
拉斯维加斯成为一座繁华的都市,与其说是利用了沙漠里的绿洲这样一个自然资源,不如说是利用了人性中的一块道德沙漠。赌作为一种行为,在其合法的地域被美化成为精神的娱乐,在不合法的地方则被视为人性的卑污。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种人类自身的精神存在,赌的动力和人与生俱来,甚至在决断的时候,成为魄力的一个部分。1931年内华达州议会通过了赌博合法的议案,就其议案的通过,无疑体现了对人性最基本特点的把握和张扬。几十年后,拉斯维加斯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赌城,这里也就成为了人们最好的彰显赌兴和演绎由赌带来的人世悲欢离合的场所。
即使你以道德家的面目对待赌博,你也无法拒绝对这座城市的向往。即使你真的把向老虎机里投几枚硬币当作一种消遣,你也确实摆脱不了被无声吞噬后的遗憾和响应环佩叮当时的快感。在立法的正当性确认之后,通常的道德在拉斯维加斯放下了架子,于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酒店在拉斯维加斯存在了九个,据说三千美元一天的客房往往需要提前三个月预定;从云端里下落的飞机排成一队等待依次降落,最多时可以一眼看到五架。拉斯维加斯就是这样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
拉斯维加斯,生存的本能挣脱了道德的束缚。挣脱之后,呈现出别样的情怀。
比如喜欢真实里的虚幻。卢克索酒店被认为是1990年代后现代建筑主义的典范,金字塔作为酒店的造型,建筑得比真正的金字塔还要雄伟,据说有四千多个豪华房间,成列地挂在呈三十九度角的金字塔内墙的高处。这种时尚对于我这样的保守的东方游客,多少有些不够适应,因为在我固执的概念里,金字塔就是法老的墓葬,而那些高悬的客房,则让我想起崖壁上的悬棺。
威尼斯人酒店是建筑里的建筑,惊叹之外,我很喜欢她的富丽和明媚。高科技的光影技术,使建筑的穹顶幻化成为天空,光线的变化与外界自然的时间同步,云朵或聚或散,朝霓晚霞,蔚为壮观。康佩尼尔塔、独立的圆柱狮碑与巍峨的酒店主楼、横亘的仿真副楼相呼应,圣马可广场被完整地复制到酒店中来了,只是缺少了那些争食的鸽子。里亚托廊桥上几个中世纪的汉子摇着手风琴拨弦弹唱,应和着桥下“钢都啦”船夫的桨声……和各地的世界公园里的景观不同,这里的景观虽也经过微缩,但功能上不仅仅是供人欣赏,他们具备一切可能的应用功能,比如在威尼斯是一家时装店,移在这里也生意兴隆。因而在这里,被渲染出强烈艺术氛围的环境,也就成为实实在在的商业场所。但也正因为如此,呈现在这里的艺术,缺少了悠久历史的斑驳和深厚,增加了外在的浮华和绚丽,带给我们的感受和置身与真正的威尼斯市井大不相同。
因为曾经什么都没有,所以什么都想拥有。所以我们在拉斯维加斯看到了金字塔,找到了威尼斯,还有埃菲尔的“铁家伙”,来自纽约海边的“自由女神”……
拉斯维加斯的室内表演场所,汇集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表演内容,从巴黎的“红磨坊”到夏威夷的“草裙舞”,从弗拉明戈的高音到泰森的铁拳,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呈现着强烈的开放性文化特征。但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依然是她的街景文化。它们在芜杂中追求着各自的单存与复杂,努力寻求着满足人们心理或精神的某个饥渴的侧面。他们有些是景观式的,有些则是表演式的。无论哪种都能给你带来一些震撼和冲击。
米拉其宾馆前的广场,在夜幕降临前就会聚集大批的游人。他们的面前除了宾馆华美的建筑外观以外,吸引他们的是门口的一座十七米高的喷泉,在夕阳里,在棕榈树硕大的叶片的掩映下,喷池里的水像混合了胭脂,沿着被修饰成自然味道的不规则的池壁欢快地溢出,梯次流下,宛若山野间淙淙的瀑流。然后夜幕降临了,“天池”里开始有了“骚动”的迹象,红色的水汽开始跃起,并逐渐沸腾;渐渐地你感觉那跃起的不再是一簇簇水的造型,而成为喷发的火的力量,果然水火不容的定律就被破坏了……淙淙的瀑流变成岩浆倾泻而下,一直燃烧到你的身边。在这里,自然破坏的力量,其震撼人心的壮观被保留了下来,破坏的恐惧则被适度的弱化,从而使游客完成了一次难忘的审美经历。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亲眼看见过火山喷发,我没有过;那以后听到火山喷发的消息,我的眼前出现的往往是米拉其宾馆前那个夜晚的印象。
米拉奇对街右手不远的地方,矗立着一家叫做“金银岛”的宾馆。我不知道宾馆用这个名字和创意,是否经过和需要经过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后人的同意,或许宾馆的创始者就是冒险的小孩吉姆的后裔?宾馆的标志就是以骇人的骷髅头为主体的海盗标志,内部布置,则以十八世纪的海盗战船为主题:大厅和走廊里,摆置着许多“海盗们”劫掠而来的宝藏,因而也有人叫它“海盗宾馆”。
海盗宾馆临街的一侧,被建设成一个人工的“海洋”,类似于好莱坞拍片的场地。贴宾馆建筑的一侧,被刻画成为海盗的堡垒,他们的海盗船就停靠在高崖下面的码头上。按导游的提醒,我在下午四点多种的时候就来到那里,那里只有舞台,没有坐席,也没有广场,人行道与“舞台”之间隔一道护栏,这边就是我们的“观景平台”。演出前的寂静里,我们看见蓝色的“海水”里,隐约有一条轨道样的设施,后来明白了,那是“皇家海军”战舰开来的“航迹”。
二十多分钟的表演,,紧凑精彩,带给观者的是紧张和刺激。从场面来说,也堪称恢宏大气。扮演海盗的演员很像中国功夫片里的人物,他们在崖壁上和桅杆上完成他们的表演。代表海盗的对立方,主角是位皇家海军的船长,古板固执得可爱,无疑被作为了揶揄的对象;他的那些士兵尽管是一群跑龙套的角色,却衬托出船长的个性与喜剧的风采。整个故事并不复杂:皇家海军的战船在接近一个海盗时发现了海盗的巢穴,船长利剑所指,船上串炮齐发,打了海盗一个措手不及。就在观众也被船长的得意所感染以为胜利垂手可得之际,海盗们的顽强反击开始了,一顿猛烈的火力袭来,皇家海军的战船吃不住劲了,舰长来不及下令后撤,船只已经遭受重创,面临下沉。搞笑的舰长完全失去了指挥的效力,士兵们纷纷跳水,四处逃生,还好有一个士兵还能想到拉船长一把,看去愚钝刻板的船长这时却表现出了英雄气概:扶正了被打歪了的帽子,笔挺地和桅杆抱在一起,在海盗的欢呼声里,与战船一起缓缓地沉如海底……
和好莱坞的电影一样,海盗之战的演出在灯光烟火声效方面都运用了富有技术含量的特技,场面效果震撼逼真。喷火的炮口,堡垒上的猛烈爆炸,水面溅起的浪花,让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战场的惨烈。但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不是演出的效果,而是内容,我对海盗胜利的结局感到意外。在我的观念里,总是正义的一方应该获得最后的胜利,强盗的得逞使我感到难堪。但拉斯维加斯就是这样,一个商业集团奉献的社会演出,它的主题绝不背离他飘扬的海盗的旗帜,他顾及正义的方式,是善意的让正
义一方不屈的失败。在这里,拉斯维加斯的街景文化体现出它的特征:在兼顾基本道义的情况下,呈现精神层面的开放性。
在拉斯维加斯浓郁的商业氛围中,他的街景文化表面是公益的,实质没有摆脱功利。同样它服务于物质,但又没有彻底的沦为附庸。在商业和艺术、物质和精神的纠葛中,它成为一道令人瞩目的风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觉得兴致盎然和耐人咀嚼。如果让我推举一个象征物,我还是推崇米拉其的火山:水的沸腾和火的喷发交织~处,不是水火不容也不是水乳交融,而是交织一处,相辅相成。许多事,包括人性个体内部的良善罪恶,卑污崇高,莫不如此。
人妖
芭堤雅地处热带,白日里空气被强烈的日光蒸煮,好像氧气都蒸发了,憋得人难受,街路上因此难得见到闲人。据说西方游客到此度假,喜欢在大白天躲在宾馆里睡觉,晚上出来泡酒吧,芭堤雅的夜生活因此喧嚣。导游指着街边排挡式的酒肆给我们介绍,屋檐楣下悬着白色日光灯的,是普通的酒吧;如果日光灯是红的,那里的服务员就是“做那个”的。“做那个”的服务员都是义务为酒肆排挡打工,趁机与客人接洽生意。谈拢了,就撂下酒吧的活计,做自己的买卖去了。
性交易在芭堤雅是开放的,但芭堤雅最著名的不是妓女,而是人妖。到芭堤雅去旅游的人,几乎没有不去看人妖表演的。
人妖从法律性别上到底是男是女,我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搞清楚,据说还算是男性。但他们从小从生理上被强制改变,在言谈举止上被刻意雕琢,以致到成年时心理上也比较女性化了。所以有人说,在人妖自己,更愿意自恋自怜自己为女性,上厕所也是避开“烟斗”和“大胡子”。
芭堤雅有两个著名的人妖歌舞团,据说是面向东西方两个不同的游客群体的。我们看到的表演,当然是东方式的。看舞台上凤佩华冠,鲜面明眸,舞姿窈窕,亮丽动人的一幕,你真的不能相信他们原本是一群男儿。着装亮相华丽且不出格,可能出格的是观众的心态,也是对他们的身体感到神秘好奇,说不上是邪恶。节目大都是中日韩风格的,有几首歌曲是港台腔。有一个节目我以为编排的极好,是用流行歌曲的方式演绎《铡美案》的故事,前后十几分钟,干净利落,一种在当时感觉很新颖的小品形式。总的说来,看人妖的表演,欣赏舞蹈更自然一些,举手投足都很柔美;听他们唱歌是另一个味道,一听就让人傻了:男性的声音和女性的形象怎么也般配不起来,发声的时候,隆起的喉结昭示了他们嗓音里那些无法改变的粗犷。
表演结束后在剧院门口有个与人妖合影的项目,要收取二十泰铢的陪照费。导游提醒我们合影时一定要手脚老实,他卖了一个关子,没有解释为什么,但参与项目的朋友都按提醒规规矩矩地做了。只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家伙出了故障,被人妖揪住不放。害得导游出面调解,问他你真的没有动手动脚?他急得说话都结巴了,说我确实没动,他拉我的!导游说,那你还是给他一百泰铢我们走人吧。第二天那老家伙还委屈地跟大家解释,是那个人妖拉我去搂他的腰,顺便往胸部按了一下,根本不是我动手动脚!看他那个认真劲儿,我笑着说:反正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了,你也别老是疙疙瘩瘩的,出来旅行就是个经历,别人没那种经历,你有了,那是偏得,花一百泰铢也值了。当时亚洲开始金融危机,一百泰铢大约值三十元人民币左右。
有了老家伙的教训,后来我们到那个什么东方公主号上就餐的时候,每个人都谨慎多了。那客轮餐厅的服务员大都是人妖,和歌舞表演场的人妖行止装扮都有了区别,特别流俗,不见高贵。有的干脆裸开胸怀,拿巨乳往游客脸上贴。多数人笑着往别处去躲,也有呵斥的,当然也有引以为乐的。据说泰国的人妖大致也是要分三级的,能够进表演场的最好;这船上的还有在其它场所有固定营生的就算其次;再有就只能在海滩上以与游客合影讨取陪照费为生了。
白日的芭提雅留下一个空旷的城市。他的喧闹一半给了黑夜,另一半割给了海滨。暹罗湾的海滨浴场,天碧海蓝,那种蓝不是我们通常看到的蔚蓝,而是海水被蒸煮过的泛白的蓝色。尽管如此,浸泡在温热的海水里的感觉,还是可以将自己体会成为一条自由自在的鱼儿。
在椰子树的荫下漫不经心地把别人当作风景欣赏的时候,导游指着旁边与人合影的“女子”对我们说:“有没有还想和人妖照相的?二十泰铢,这里手脚不老实没关系。”我们知道,那就是他说过的底层的人妖了。
在泰国,人妖一般都来自生计艰难的贫苦家庭。家庭从小把他们送到专门培养人妖的学校,冀图通过对他们肉体的改造,来改变家庭和他们自己的命运。据说塑造一个高级人妖,不仅个体先天的资质要好,还要付出巨大的花费,当然这一切都是以日后成功的巨大利益诱惑为回报的。然而做到高级人妖的毕竟也是少数,相当一部分在丧失了性别的尊严之后,也部分地丧失了正常人的尊严,沦落为变相的求乞者。不仅如此,人妖追求的成功还要以生命为代价,他们的寿命大都在三四十岁,即使获得巨大的成功,青春的生命对他们来说,也不过是暗夜流星。
我注意到我前面的海滩上有四个陪照者。其中有三位看来生意还不错。特别是一个身材颀长,披着一身透明的红纱的,更是应接不暇。这之前,我一直觉得与人妖合影是件别扭的事,尽管我不住批评自己内心可能存在某些龌龊而又刻意想当伪君子的想法,但这改变不了我的行为。但此时,我不由对那些与人妖合影的游客产生了敬佩,且不管他们出自什么心理动机。
四个人中受冷落的一位双手扯起一片红纱巾,在海滩上来回奔跑。
经过我们身边时,他狂放地自嘲般用生硬的华语吆喝:“免费喽——免费喽——”惹起海滩上一片善意的笑声。他穿着黑色的比基尼,依然看不出多少女性的特征,除了胸部的隆起,还有烫卷了的长发。
我身边的朋友这时对我说:“你想不想去照一个?”我略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朋友喊住奔跑中的他——他还是怔了一下,然后他愉快地迎上来,两手一边一个拉住我们俩,略一扭头的瞬间,我看到他眼里似乎的一闪而过的女性柔情——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错觉。
他没忘招呼另一个也时时被冷落的同伴过来与我们一同拍照。虽然他问了一声“可以吗”,但我还是能够感觉他生意上的精明。或许他对同伴照应的原因,来自同伴对他的照应。他们需要互相照应在我看来是种合理的解释。
我们就让老家伙给我们拍照。看我们摆出亲密的架势,而且几乎赤身裸体,老家伙一边按快门一边嘿嘿直乐,我以为他有些不怀好意,觉得把我们和人妖勾肩搭背的姿态装到他的镜头里,他花一百泰铢的屈辱就不算什么了。
或许是体会到我们的善意,我们给他们每人二十泰铢后,他们还要我们跟他们分别照一张“免费的”。但朋友还是又给了他们每人二十泰铢。
东南亚的那次行程最后,是到香港经澳门从拱北海关入境回国。在香港的时候,老家伙找我们商量说,和人妖照的那几张相,拿回国冲洗可能不大方便,万一照相馆有认识我们的,又不知道人妖到底是男是女,岂不是很麻烦的事?于是我们就在香港把照片冲洗出来,没问题,照的都很清晰。我们互相传看着,不停地大笑着,觉得那些照片真的很有趣。看够笑够,老家伙说:“我是不敢把这样的照片带回去了,女儿会瞪我,儿子会骂我,老婆子会跟我拼命!”说着慢慢地把他那张照片撕成碎片,一片一片地扔进垃圾桶。
离开澳门之前,朋友问我:“你那两张照片还带着吗?”我说,带着,我没事。朋友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那两张刚才也撕了,唉,还是别惹麻烦了。”只有我把照片带回了家里。当晚我给妻子看在国外的留影,有一百多张,我特意让她先看与人妖合影的两张,并抢着给她解释人妖是怎么回事。但她的脸色一直很难看。那时我们那里一般人连人妖这个词都没听过。
我和妻子没有因为我与人妖的合影发生不愉快。但几天后,有其他朋友到我家来玩,问起出国见闻,我就拿照片给他们讲。讲起人妖,怎么也找不到那两张照片了。问妻子,妻子说她不知道。过了两年,她还说不知道。直到今天,她也是说不知道。
[责任编辑丛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