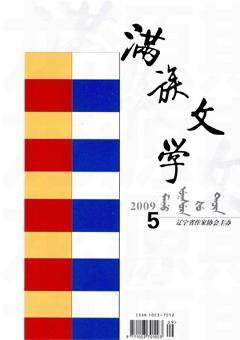风和太阳的痛
姜雁翎
“南筱风,现在、在哪?”
两瓶啤酒,竟令我不能自制,手捂肚子,蹲在了花坛边。鸟鸣嘤嘤,出自幽谷,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声?
“又喝酒了?我马上过去。”
南筱风和我是大学同学,帅哥一个。援引《世说新语·容止》赞扬嵇康的那一段——风姿特秀,见者叹日: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只是遗憾,我们三年的感情最后因为他的移情别恋而告终。他为了他的远大前程明智地放弃了我们之间的承诺,绝情地不晓廉耻地跟着那个女的走了,漂亮的马自达轿车,一喘气飞出好远,疾速地飞出我断断续续的视野……我竭力不去想他,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喝过酒想起的人只有他。
“知道我在哪么就要过来,我没事的。”我醉醺醺道,伸出两个手指头,认得是二。
“知道。等我。”南筱风扣了手机。他每次接到我的电话都有些紧张,我喜欢他的紧张,里面所含有的愧欠令我惬意?我给自己一个无理的解释。像影视里滥对白中所说的那样,做不成恋人还可以做朋友。
我一人呆在花坛边。这个花坛有一个只有我和南筱风知道的名字——风寒花坛,这是我们不谋而合用我们的名字取的。我们曾经有一次意外地睡倒在这个花坛里,等醒来,毫不留情地患上了感冒,南筱风囔囔着鼻音说:“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往事如昨,那个持续的伤痛在这样一个寂寥的夜色下,像大大的不可教药的脓包,一点点,在发炎,扩散至我的全身。海誓山盟都是曾经的冲动,冲动的时候往往都是主观在盅惑,而生活是现实的。
我从三流大学已经毕业三年多了,工作换了又换,刚刚百舍重茧找到了一份广告公司的工作,上了半个月的班天天和同事发生口角,椅子不比人家坐得稳,每回都不占上风,气得我肠子破个洞。而南筱风呢,可能是因为那个女人,现在成为一家贸易公司的业务经理。哈哈,我能不疯狂地大笑吗?
心烦意乱,乡思望中天阔,漏残星亦残。八街九陌使我感觉自己身陷淤泥,越想越憋气。琉璃的夜色柔媚得让人心动,虫子不知劳累地蜂缠蝶恋地嗡嗡闹个不停,似乎不懈地要闯人我空荡荡的心,任意折腾一番才肯罢休。我正浑身疲惫地在想明天要不要炒老板鱿鱼时,陡然一辆黑色轿车在我面前停下来,车灯刺得我眼睛什么都看不清,只听见自己内心的惴惴不安,脑子里所有在电影中看到的拐卖绑票的骇人情节栩栩如生浮现出来。心想:勒索我是不可能的,家里没钱,若拐卖大有可能,将我装进麻袋偷渡到某个世道混乱毫无规章的国家去卖身,要不就是给我拉到荒无人烟的地方把我健康的肝啊肾啊眼睛什么的给挖出来去卖钱,想到这,我噌地站起身,决心背水一战,可我还是感觉自己的腿在强烈地颤抖。
“易水寒,怎么又喝成这样?”
呕,我忘了,我给南筱风挂过电话。我松了一口气,冷笑道:“行啊,伟大的南筱风,换车了!”
“别闹了,工作又不做了?”他了解我。
“抱歉,让你失望了,这次的工作姐姐我做得很好。”我反击道。
“才怪呢。那说说为什么喝这么多?”他质问。
我指着他,踉踉跄跄,道:“别小看人!没有为什么。花能嫣然顾我笑,鸟劝我饮非无情。”
“上车,我送你回家。”
“切,心领了。”我嘴一撇,用手指车。“她送的?”
“我们分了。”他的语气很低沉,低沉的深处却藏着一抹温柔,用曾经的那种深情如履薄冰的目光看着我。
“是吗?”我内心划过一簇光亮。“那车可要还给人家啊,不然不清不浑的难做人呀!”
“你能不能不这么铁嘴,知道纪晓岚是你哥。”
“不,我哥是荆轲。”我讽刺他,“筱风君可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他羞赧,妥协道:“每次都说不过你,我认输行不?”
“哪敢?”
他无话可说。我也无话可说。僵持一会儿,他拉起我的手,命令道:“回家!”
我突然怒发冲冠,抬脚往死里踹车的轮胎:“我不坐她的破车!”
“好啦好啦,就知道你会这样。既然给我打电话,就得听我的!”他强横地把我扔进车里。
我突然放声大哭,哭得自己都被震撼得稀里哗啦。他有些目瞪口呆,半晌才抖抖地说:“易水寒,你千万别哭,我最怕你哭。”
我从车里滚了出来。我大声说:“南筱风,唱歌给我听,快,不然你死定了!”我抽咽,泪水如同家丁,纷纷退下。
“好好好,我唱,我唱你家王菲的歌行不?我唱你家的《催眠》行不?”他摇头笑道。于是,他捏捏喉咙干咳一声,打开干净的嗓子,天籁般的嗓音孕育出淡淡的忧伤——
第一口蛋糕的滋味
第一件玩具带来的安慰
太阳下山太阳下山冰淇淋流泪
第二口蛋糕的滋味
第二件玩具带来的安慰
大风吹大风吹爆米花好美
从头到尾忘记了谁想起了谁
从头到尾再数一回再数一回
有没有荒废
啦……
如痴如醉的我,和以往一样……曾经多少个晚上他就是在电话那头唱着这歌哄着我很快安睡,连梦都没有,一路顺风直达晨的彼岸。
这一次,他成全了我,也是又一次纵容了我。他没有开车,而是打车把我送回家。我的酒醉在继续,我执意地坚强地独立地依偎在车窗边。朦胧中听见他小声低语,你不小了,不应该是个倔强任性的孩子了。酒醉中的我在心里和他说,你可否知道,几年前我愿意在你怀里做个孩子,现在也是。
醉意这个东西是在愁闷、阢陧、恐慌沉淀之后开始浮泛上来,终于湮没了我的意识,我真的醉了,或者困了。
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已躺在我最爱的大床上,阳光暖暖的懒洋洋地洒满屋子。我立刻坐起,揉揉惺忪睡眼,扫了一眼壁钟,高分贝尖叫一声,掀起被子,跳到地上。我的天,十一点了!我风风火火一头扎到门口穿鞋子,南筱风如风而至,诧异道:“干吗?粥我都熬好了。”
我惊愕道:“你怎么在这?哥哥啊,你为什么不叫醒我?这哪是迟到!明明是旷工半天!”
他一脸无辜,慢条斯理说:“今天是星期六,小东西,酒还没醒啊。”
我无奈道:“亲爱的哥哥,我们不是公务员,哪有什么双休日。”
他像是未卜先知:“挺不住就别做了。”
我鬼使神差地说:“谁能比得上你,有贵人相助。吾小辈只能靠自己拼死地奋斗。”我颇为得意,掏出他的软肋。
他的脸闪过一片绯红,并没有辨白。我倒是希望他能为自己辨白一下,哪怕是穿凿附会无中生有,不然的话我会精神不正常地对他升起怜悯。我发誓。再也不掏他的软肋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他一声不吭,手脚忙乱地收拾东西,匆匆跑过来,递给我那么一个大口袋,“呶,这里面有面包茶鸡蛋,肠和奶。你的冰箱都空了,今天我帮你填满。”
我看着他塞到我手里的东西:“哪吃得下?猪爸爸猪妈妈加上猪宝宝也吃不下。谢了。”
我真的好怕从前的眷恋在心底复活。当然,可能并未死去。我像被猎豹追捕似的亟亟冲下楼。
我想起那个曾经的雨夜。我被他甩了,一屁股坐在大街上嘤嘤啼哭。大半夜,我傻
呵呵的蛮诗意地写着“你是夏天的南风,不再温暖我冬天的心。我失恋了,敢问全世界,有谁可以杀了你?”然后摔了笔很幼稚地撕个粉碎。到翌日白天,雨一直下,我躺在床上,望着窗外,对面陈旧的楼被淋得格外陈旧,亦如我当时的心情,眼睛明明很困却不想睡,任凭孤单疲倦在心底滋生。胃开始痛起来。所有的困扰矛盾忧愁饥饿都随之应运而生,雨滴在铁板上的声音麻木而响彻,敲碎一桩桩尘烟往事。我仿佛坠落在悲痛和黑夜的罅隙里。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疼。生命没有了生机,世界开始变得寂静,静得可以听到自己的呼吸困难和血液流动的寂寞。
后来,我特别憎恨下雨天,因为每下一次雨,便淋湿我一次灵魂。我拼命把为他流的泪水埋葬在记忆最深的荒冢里面,我试着让那个地方长满参天的野草和荆棘,然后和着垃圾腐烂掉,自此让我可以从他绝情的瞳孔走出,使我以后的人生远离大雨的黑夜,永远地忘掉曾经设想的未来和虚无的过去,我只想与夜里房间那盏放着冷冷白光的台灯相依为命。厚厚的日记继续工工整整地写着,累的时候习惯地抬一抬头,望见天上疏疏几颗多愁善感的星星,小区里小卖店的那个老大爷抽着烟在很晚很晚很静很静的夜里闪着微弱而鲜明的光亮,这些生动的情景足以让我发呆半个多小时。在没有他的日子里,我就是这样度过的。
我坐在电脑前梦游一般,不由自主打了几个字:落花时节又逢君。我蓦地定睛一看,迅速删去,贼头贼脑窥视旁人有没有看到,不巧目光撞上老板,被数落~通后,我懒得吵嘴,和她们无味地玩舌头简直是浪费细胞无知到家。
晚饭没有吃,喝了两杯水充饥,卫生间在楼下,跑得腿都软了。最后,不大的办公室只剩我一人,加班到九点,才算抢出两天的活。疲劳困顿折磨得我欲死不能,我盯着窗外的月亮,皎洁的光透过窗缦温馨地照进来,银水一般,使人陷入一种迷失的感伤。
出来,环顾四周,草木皆兵,稀稀拉拉的出租车在我面前按着喇叭驶过,我第一时间想起南筱风,然后轻叹一声,决定自己走回去。
明月清风,天空地静,黄鸟翩翩,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我一道上目不斜视直视地上,兴许能捡到钱呢!曾经沧海难为水,累死累活我是谁?除却巫山不见云,生活天天为钱寻。这是以前南筱风在学校里有事没事都挂在嘴边的一首诗。现在想来深有体会。
我苦中作乐哼着小调,从心理上消除路的漫长和恐惧。
快到家的时候,大事不妙!我撞到了一个胸膛,心想:这下完了!真遇上坏蛋了!偏偏就在要到家的时候给遇上了!苍天无情!我后退两步,惶惶抬头:“呀!该死!吓死我了!怎么是你!你没走?”
“我又来了。”南筱风笑吟吟地说。“更深夜阑兮,是汝来期。”他弹了一下我的脑袋,变态地莞尔,躬下身目光与我达成平行,淘气地看着我,“再这么晚就给我打电话。”
“打住,不敢劳驾。”我不屑道。
“好,你说的,别再给我打电话。”
“不会的,以前抱歉了。”我拂袖而去,他一把拉住我,我回过头遇见他凝视的双眸充满着杀伤力,既而用力避开这种眼神,甩开道:“要怎样!”
“干吗认真?”
“我不同你,马马虎虎,对待感情也可以马马虎虎!”我厉声道。
“还不原谅我?”
“我就是要你内疚,内疚一辈子!”
他挺拔的眉梢飘过一丝忧郁,涣散的眼神荡漾着伤心,喃喃道:“易水寒易水寒。你真是让人心寒。”
我佯装气呼呼,大踏步走进楼道里。感应灯几天前就坏了始终没人修,我使劲跺脚仍没有反应,南筱风走过来,拉着我的手,他跟中闪烁着光芒,照亮了我残缺的心。我必须承认,我一直都没有放弃他。我傻吗?我靠在楼梯扶手边,莫名地轻笑,是给予自己的,我笑我的悲哀。
“我们像从前一样好不好?”他贴近过来,轻轻地抱着我,我的理智没有灭亡,自己不能再像个笨蛋溺于这痛心的窒息的感觉里,可却仍然彷徨在这种飘渺的铭心的安慰中。我脱开他,退到墙隅,他的话是那样的闪烁其词飘忽不定,我仅存的一点自尊还保留在自己清醒的意识里。纵然我承认我在面对他的时候是那么的心口不一。
我淡定地说:“南筱风,对不起,我给不了你钱也给不了你车。”
他怫然作色:“你可不可以不要总提这个揭我伤口?”
“但是当初你就是因为这个离开我的!”我扑到他的怀里失声痛哭。他抚摸着我的头,有着柳永《浪淘沙漫》里的“碲雨尤云,有万般千种相怜惜”的神情叹息道:“可怜的小家伙,总是这么的不省心。”
我终于可耻地不争气地败下阵来。
我想我们又重新开始了。
我坐在公交车上,一路晃晃悠悠,停停站站,玻璃外面的人山人海高楼大厦熠熠灯光起伏在我混乱的视线里。车行驶在一个暗暗的桥洞里,猛然,我透过车窗玻璃清晰看到自己的面孔,憔悴的让我惶恐。洞壁像是一直在前进,而我们的车子似乎往回行驶,这种错觉却给我带来了无限的恍惚。直到出了桥洞,我才看见明朗的天。
我还铭记他的生日,我不知道给自己的生日忘了多少回但是却记得他的。我控制不住不给他过生日,我也确信再次回来的他,不是随口说说,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身影。我依然怀着初恋的心态要给只穿361°的南筱风362°的惊喜。
日落时的云,滴了几滴雨,是那样的轻盈,滴在我的头发上,睫毛上,衣服上,我一路轻快地取完蛋糕奔向他家,就差没唱出采蘑菇的小姑娘。
我到电梯口的时候,猛然撞见了南筱风和那个女人。我突然感觉自己心碎的一塌糊涂,蛋糕毫不犹豫地从我手里“叭”地一声,很响的一声,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掉在地上。那个女的,满不在乎地瞥了我一眼,我不知为什么目光脆弱地转向南筱风,而他明显有些不知所措,眼神是我再熟悉不过的慌乱,我居然像傻子似的说了这么一句话:“哦,打扰,太可笑了,哦,我是说我,太可笑了!”然后疯子一样地跑掉,眼眶里的那些废物澎湃而出,烫疼了我受过伤的脸。我特后悔刚才不是说诸如南筱风你混蛋不是人之类或者给女的一巴掌,或者推翻旧制度似地给女的一拳,或是一脚等等,我现在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愚蠢那么的生气那么的委屈那么的悲痛。
防雨的外套簌簌作响,风很大,所向披靡,吹散了我若愈即合的心。夕阳不在,夜幕深沉。
“易水寒!”仿佛南筱风又随风追来。
我又一次回头……
[责任编辑宋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