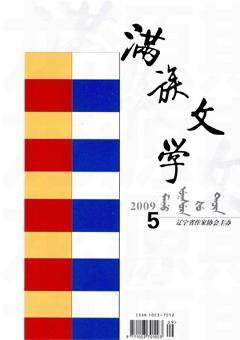猴戏
[满族]任国良
当,当,当,锣声响了。
队长拿着从戏班子借来的铜锣在堡子的小街上边走边敲着。铜锣已经很旧了,中间部位被敲打得锃明瓦亮,黄得好像涂了油彩,两边却有些发乌。声音是异常地响,颤微微的,绵绵不绝。细听听,锣声里似乎能听到有词,有句。
这是一个秋日的上午。粮食已经归仓,劳动了一年的社员们都懒在家里的炕上不愿起来。听到锣声,有人便挪到院子里,问一脸喜色的队长:“干啥呢,又有什么政治文件要学?”队长很得意地说:“不知道的,以为你识多少大字呢,快把老婆孩子叫着,到场院去看猴戏。”那人一脸松垮垮的肉便立刻泛起亮光,扯上一嗓子,一家人便往小队部跑去。只一刻,场院上人就满了,黑压压地落了一地。队长骂道:“看热闹比什么都积极,一到正经事儿就稀汤寡水的了。”
李木匠踹了一脚正帮他把着木料的老婆:“去,给我占个好地方,猴戏可是挺稀奇的,这个呆儿得卖。”他老婆说:“就这点儿,干完再说。”木匠火了:“你少磨蹭,占好位置,我这就去。”他老婆用手捌饬了两下头发,拿了两个小板凳走了。木匠也歇了手,洗了把脸,光着膀子,出了门。
当当当,三声锣响。耍猴的老人冲着一百多号人拜了拜,底气很足地吆喝:“各位老乡,今日我在贵地摆场子,演好了,您给点掌声,演砸了,您也赏咱一口饭吃。这位问了,你是谁呀?告诉各位,在下姓侯,人送外号猴王。家中祖传二百年的手艺,走遍咱中国各州府县。您问了,您会什么呀?好,我先告诉您,我带了两个猴子。瞧,这位,头戴花翎的,是咱们县令。这位,个头稍矮却有一身好武艺,是咱们的捕头。我是谁?对外称咱是猴王,对内,我就是这二位的儿子。”
老人话说干脆,吐口唾沫是个钉。大伙都在想,说话那么派头,比生产队长有水平。比大队长还有派。只一个开场白,就把场子震住了。“各位,咱们都是百姓平民,古语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天您在这捧场,我们爷们儿是主角。所以这里就听我的。”老人说着,操起一根两米长的竹竿,他拿住一头,另一头敲着地:“各位,看戏开场子。您体格好的,年轻的,个头高的往后站,您是小朋友,您是上了岁数的,您是女同志,您往前坐。咱家吃饭都先让老幼,到这里,您就别占了好地方挡了一面子。”那些抱着胳膊站在前排的爷们,四下里瞅瞅,就退到后边去了。老人又是一拜:“谢谢您了,咱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到了贵地,咱才叫见了世面,您这里人水平高,素质高,风格高,各位,我老汉还有一言,您把这正前方的地方给让出来,请咱们生产队的队长过去坐。哎,这个小伙有前途,他把椅子都搬来了。队长旁边,咱们请民兵连长、妇女队长、会计、出纳、生产组长都过来坐,请队长夫人坐过来。人常说,羊群走路靠头羊,穷苦人跟着共产党。咱们队产值怎样,家家户户能否吃饱饭,隔三差五能否吃顿细粮,过年能否吃顿饺子,全靠这些干部。来,您这边请。”老人说着,竹竿开路,一手扶着队长把他请到了正面的椅子上。队长才三十多岁,闹了个关公脸。也不让,坐上了。队长笑着喊:“庙小和尚全,都坐过来吧。”老人笑着点点头,于是生产队里带长的,带衔的,挂边的,就都坐到了正面。数数二三十个。会计捅了捅队长:“嫂子呢,叫嫂子过来。”队长小声说:“别弄那些事儿,一个老娘们,在哪不能将就卖卖呆儿。”会计说:“那不行。”会计站起来冲着人群喊:“队长夫人,过来,过来。”队长媳妇臊得恨不得钻到地缝里。有人喊:“快去吧,你看西哈努克出国都带夫人,那是文明。”几个老娘们生拉硬扯地把队长媳妇扯过来,会计让了位,队长媳妇坐下了。会计站着,身后的民兵连长把坐位让给了会计,一个让一个,最后团支部的劳动委员站在最后边。
队长想起了什么,左瞅右看:“哎,李木匠呢,你过来。”
李木匠才从北大荒搬回来,四十多岁,一手好木匠活。现在也允许干手艺活,挣个工夫钱。手头就很宽裕,买了全大队第一台十二寸电视。一到晚上,家里像开会似的,看电视的人挤得里三层外三层。队长去了。人家就把最好的位置让给他。礼尚往来嘛。这个场合,可不能冷落了这个先富起来的人。本来李木匠坐得四平八稳的,这下可好,硬是给挤得没了地方,气得李木匠那老脸比驴脸还长,正一个人呵斥带喘地生闷气呢。
队长喊了两声,李木匠才从人群里站起来:“咱不是干部,别小鱼串在大串上,珂碜。”说完又坐下了。人群静下来,老人略一沉吟,把锣交给捕头。捕头一手拿锣,一手拿锤,脖子上系着绳子,绳子头在老者的手中,绕着场子打起锣来。捕头步子走得顺溜,通红的小屁股撅着,节奏却一点不赖。走了三圈,下去了。
老人喊:“有请县太爷。”于是捕头放了手中的锣,一手抓起一块小木牌,一个写着“回避”,一个写着“肃静。”捕头在前,县太爷在后,到底看出来捕头稚嫩,小脑袋左顾右盼。县太爷则沉稳得多,目不斜视,四方步迈得颤微微的,走了三圈。老人一抖绳子,捕头放了木牌,搬来一张小椅子。老人再一抖绳子,县太爷心领神会,一屁股坐了上去,它似乎嫌日头有些热,眯起了眼睛,翘起了二郎腿。
老人把县太爷脖子上的绳子绑到了一把椅子上,手里牵了捕头。
老人说道:“各位看官,这位捕头是谁?师从何方?我告诉您。中国有三山五岳,其中北岳嵩山少林寺是天下武术的大集成地。这位捕头一岁上山学艺,三岁学成下山。它会什么功夫?嘿嘿,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十八般武艺那是样样精通。现在由捕头给各位表演猴拳猴棍。”捕头就在场子中间打起拳来,看不出套路,只是随着老者手里的绳子抖动,一会儿翻跟头,一会儿做打人状,一会儿拿起棍子上下翻飞,那样子,似乎入了无人之境。这捕头功夫一般,但一点儿不怯场,不心虚,长了张大脸,脸不红心不跳的,看得出来,也是见过大世面的。咱们这辽东山里,交通闭塞,很少有什么演出,更别说跑江湖的了。哪见过这场面。大人一个个睁大眼睛,抻长了脖子,不时开心地大笑。孩子们则一齐向前探着身子,小手拍着,哈哈直笑。
人群里只有李木匠绷着脸。他的个子不高,尽管北风下来了,略有些凉,仍光了膀子。常干木匠活,胳膊上的肌肉块一鼓楞一鼓楞的。他的眼神根本没在猴戏上。他眯着眼看了一会儿在坐的生产队的领导们,几乎是每一张脸依次看过去。他往地上吐了一口痰。然后他瞅着外围的观众。大家都在目不转睛地看着猴戏,没有人在意他。他的眼里有了怒火,喘气粗了。他老婆一直站在他身边,不安地扯了一下他:“他爹,咱回吧。”木匠一甩胳膊:“你他妈的傻啊,不看白不看。”女人噤了声。站在那里,一点声音也没有。
一个孩子从兜里拿出了一个粘火勺,粘高粱米面的,沾得手上左一块右一块。孩子可能是饿了,也可能有些显摆的意思。谁都没在意,可是捕头看到了。捕头立刻放下棍子,冲孩子走来。老人一看,一抖绳子,可是捕头根本不听,硬生生地把绳子抻得直直的,脖子硬硬地站到孩子面前,伸出了两
只毛茸茸的小手。老人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大伙笑话了,捕头可能是饿了。小朋友,你能把这干粮给咱们的捕头吗?”孩子可能没想到,很快就高兴地把粘火勺递过去。捕头一把抓到手里,它的嘴有些小,就把粘火勺掰成小块,可是一掰,弄得两只小手都是。它想把沾在手上的弄掉,不曾想越抹越多。捕头有些恼火,上蹦下跳的。人们看着它人事不懂的小样,笑得前仰后合。孩子们则一边笑,一边学着小猴子的样子。这是一个意外,老人也笑了,他说:“咱们捕头没吃过你们这种粘食,让大伙见笑了。”他扯过捕头,帮它弄掉那些沾在手上的干粮。
老人一抖绳子,捕头下场了。县太爷很知趣地从椅子跳下来,人们都瞪大了眼睛,都觉得这县太爷的功夫一定更加了得。老人一抖手中的绳子,开口说道:“各位,这个县太爷是个好官,脾气好,心肠好,但是却没有什么能耐,一辈子只学会了一样——作揖。各位,咱们县太爷给您作揖了。”说罢,一抖绳子,县太爷双手抱拳,冲着大伙作起揖来。老人朗声说道:“谢谢,做揖也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水平。”人们高兴地拍起了巴掌。
老人牵着县太爷来到队长面前,双手一抱拳:“咱们队长年轻有为,前程似锦。我带县太爷来拜父母官。别看这个县太爷是个猴子,可是膝下有黄金。每到一处,它只拜一人。来,给咱们的队长大人磕头。”县太爷来到队长面前,双手伏地。冲着队长就磕头。队长一捅身边的会计,会计把准备好的十元钱递给了老人。老人大声说:“钱不在多少,量力而行。生产队赏钱十元,谢了。”县太爷起身,大伙又拍起了巴掌。老人说:“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伙捧场。”说完,弯腰开始收拾家什。
“停,我还没看够呢!”李木匠大声喊。队长已经站起来了,他奇怪地问:“木匠,你还有什么事儿?”李木匠说:“我这个人就这脾气,来,我出二十元,让这县太爷给我也磕个头。”队长一听,乐了:“好哇,老人家,你就让这县太爷给我们生产队的有钱人磕个头。”木匠老婆火了:“你逞什么能?二十块钱,买个面子,回家我给你磕,钱给我。我看你是钱多了花不出去,让钱给烧糊涂了。”木匠涨红了脸,大声说:“钱是我挣的,我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来,磕头,赏钱。”人群静下来,有个半大小子喊:“李叔,我给你磕头,钱给我。”李木匠没搭言。队长对老人说:“给他磕,这钱挣得容易。”人们把目光都集中到了老人身上。老人站直了身子,瞅了瞅木匠,又瞅了瞅大伙,他大声说:“人有规矩,猴有尊严。咱们县太爷无论走到哪里,一场猴戏只拜一人。咱们虽是跑江湖卖艺的,但是也有咱的原则,二十元钱不少,比我忙活半天挣得还多。但是我们不会为了这笔钱坏了规矩。”
李木匠冲到场子里,有些不屑地说:“不就是磕一个头吗?嫌二十元钱少呀!”老人站在那里纹丝没动:“您可能是有钱,但是给多少钱这县太爷也是不磕的。就像在咱们生产队,咱只拜队长,别人不拜。您拿多少钱也不好使。”李木匠觉得受到了污辱,他大声说:“我拿二十元钱,谁磕头钱给谁,大伙能抢着给我磕。我就不信,一个猴子比人还有骨气?”
正僵持着,民兵连长喊:“大队长来了。”
人群回头,大队长领着几个人进了院子。
大队长五十多岁了,个头不高,挺瘦。队长迎上去:“领导来了,欢迎,欢迎。”大队长笑着骂道:“你小子不对呀,看猴戏也不通知一声。”队长有些不安:“瞧您说的,两个小猴子有什么可看的?您走南闯北的,什么好玩的没见过?我们生产队也是穷吃胀馕,瘦驴拉硬屎。”大队长骂道:“咱们一个穷大队,走不出沟膛子,漂不出大泡子,见过什么世面?来来来,咱也借把光,好好享受享受。耍猴的,有什么拿手的给咱们再来一下。”队长回头瞅瞅老人,老人刚要开口,李木匠不怀好意地喊上了:“县太爷磕头最好看。”所有人一愣,目光又都投向了老人。整个场院一点声音都没有。
“是吗?那好,就表演这一出。”大队长坐在椅子上,兴致勃勃地冲着队长说。
队长瞅了一眼老人。老人的脸依然平静。队长扯过老人,两人走进小队部,大队长有些不满:“不就是让猴子给磕个头吗?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弄得还挺严肃的。”李木匠感觉很好,喘气也顺溜了,他笑着说:“净能整事儿,一个猴子,磕个头有什么难的?惹火了把猴子杀了,也让它跪在你面前。”大队长瞅瞅李木匠:“你就是李木匠?你脑子挺活呀!我可告诉你,别犯法,碰到法律老子就把你扣了,蹲监狱去。”李木匠赔着笑说:“您放心,打死我也不敢犯法呀。很多事儿还得您帮忙,改日我请您喝酒。”大队长说:“知道就好。”
老人和队长从屋里走出来。老人面色铁青,到了场子里,冲着又围上来的人群一抱拳,瞅了瞅李木匠,转过身对大队长说:“闯江湖的有闯江湖的讲究。咱这猴县太爷一个地方只拜一个领导,这是多少年的规矩。今天就是打死它,它也不会再给大队长磕头。怎么办?我在世上走了多少年了,这点儿事儿难不倒我。先问一句,大队长,你还坚持要拜么?”李木匠插言道:“当然要拜,大队长是咱十里八村最大的官,不拜他拜谁?不拜就没意思了,拜才有戏看嘛!对不对?”后来的几位不知细节,和李木匠一起点头称是。老人把县太爷的帽子取下来,戴在自己的头上,有点小,用线绳固定了。老人一抱拳:“各位,咱中国自古就是官说的算。官是什么?就是一顶帽子嘛!从皇上到县官,多大官戴什么帽子,都是有说道的。今天,我带了县太爷的帽子,我就是那个县太爷。尽管有些为难,但是大队长是咱们的父母官,是我们卖艺的衣食父母,还希望您能多支持,让我在贵地多演几场。我谢谢您。来,咱们闲话少说,书归正传。来,猴县太爷在此,回避,肃静,看看咱这猴县太爷的表演。”
老人说着,冲着大队长双膝着地,他那花白的头发磕在泥土上,像一个放在那里的祭品。一个,两个,三个。个个落地有声,头发上沾满了秋天干燥的尘土。老人双手伏地,慢慢站起来,仿佛被风刮倒在地的树,又直起腰来。
人们都傻了。小队场院里静悄悄的,小队长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大队长没想到,之后就乐了:“你这个卖艺的挺懂规矩,你说的话我也听懂了。咱们还有十个生产队,你挨个儿演吧。谁他妈要是找毛病,我劁了他。”队长忙上前把老人扶起来,帮他拍拍身上的尘土。
一群人的目光又不约而同集中到李木匠身上。李木匠的脸色像要掉下来,踹了一脚他老婆坐的小板凳:“你他妈的死人啊,快回家做饭。家里的活都干不过来了,你不知道哇。”
人群很快散去。
老人装好木头箱子,扛在肩上,向村外走去。两个小猴子什么也不知道,依旧乱蹦乱跳,似乎陌生的旅途让它俩很兴奋。小队长一直给送到村口,老人紧握着小队长的手,用力摇了摇,转身消失在落叶的金黄中。
老人那风尘仆仆的背影,让人想起一个取经的人。
[责任编辑宋长江]